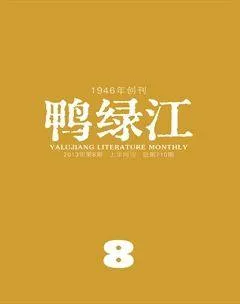李皓组诗(附:创作谈)
李 皓,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70年生于大连普兰店,1989年入伍,1999年进入大连晚报社,2010年任大连《海燕》文学月刊社主编。1987年开始写诗,曾获“蓓蕾杯”全国中学生诗歌大奖赛一等奖、诗刊社“雷锋杯”全国新诗大赛三等奖、“雷锋——道德的丰碑”全国诗歌大赛二等奖等奖项。曾在《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诗神》等报刊发表散文、诗歌作品,多篇作品入选多种年选。
回父母家吃饭
我的父母住在乡下,如果开车
回一趟父母家,需要个把小时的
车程。个把小时,父亲总共
来过三遍电话
第一遍电话打进来的时候,车子
刚经过开发区。我们一家三口正在
争论日新月异的被新区合并了的
开发区还叫不叫开发区,父亲说
你们开的什么车,真慢!
第二遍电话打进来的时候,我正在
打量着车窗外的玉米、大豆、高粱
还有翻滚着金黄色稻浪的水稻
女儿不屑一顾我对庄稼的认知
父亲在电话那头说,哦!快了
父亲打来第三遍电话的时候
我望见由远及近的收费站一阵窃喜
这个节日高速公路免费通行
让随着油表一起下沉的心,有些许
扭曲的安慰。爸,马上到家
在小镇电业家属楼楼下停车的时候
爸爸准时出现在一门洞的出口
像提前有预感似的。爸爸嘟哝着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妈早把
饭菜准备好了,有的都凉了
其实饭菜根本没凉,那一桌饭菜
把母亲忙得够呛。父亲对于快与慢
凉与热的定义,总是让人匪夷所思
但我始终坚信他有他的道理
就像一群大雁从我们头上飞过
根本不需要,任何借口和理由
母亲很享受我们的风卷残云
个把小时,我们就把父母家搞得
杯盘狼藉。一个个抹着油腻的嘴巴
我说妈,今天的饭菜咸淡正好
母亲说,好吃,你们就再多吃点儿
个把小时,我们吃得很快
没怎么喝酒,只唠了点儿家常
然后拍拍屁股就准备走人,驱车
个把小时,回到没有父亲母亲的
城里,没有庄稼撩人的城里
父亲母亲没有计较这个把小时
儿子足足走了大半个年头
他们知道,儿子很忙碌饭局很多
以至于大半个年头没回乡下
回来,也就待上个把小时
下楼时我们执意不让父母下楼
父母在门里,我们在门外
父亲说回去的路上慢点儿开车
我说爸,你别担心也就个把小时
转过身去我就觉得芒刺在背
高速公路上的车都是风驰电掣
但我清醒地知道,自己尚不及一根
干枯的稻草更有力量。我咀嚼着
残留在嘴边的饭粒,我的泪水
都已掉进酒杯
父母健在,明镜高堂
个把小时回父母家吃一顿饭
吃多吃少、吃快吃慢都不重要
只是守候与驻留的时间要慢下来
慢得我们从不曾认为自己的父母
正在慢慢变老
创可贴
必须有伤口,一个不大不小的伤口
一个创可贴恰好覆盖的伤口
这样就有了借口,一个恰如其分的借口
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
买药,买几贴谓之创可贴的膏药
为你刮骨疗伤,解去心头之痛
我丝毫不想掩饰对你的钦慕
打认识之日起,我就把你视为己有
据说也有人宣示过对你的主权
但我不在乎,我有我的霸道
是我的就是我的,我是个男人
对于心爱的女人,我是天然的保护伞
即使有秋夜的冷雨,将伤口浸泡得
四周泛白,创可贴欲盖弥彰
好吧爱人,对于你的伤口
我永远都是一味守候千年的药
女儿的电话
女儿打来电话,报了一声平安
我的心,才在平静中安顿下来
女儿拎着的两个包裹像两枚石子
一枚击中秋水,一枚击中了我的心
千重浪花在为父的胸中掀起波澜
每一朵都叫惦念,每一朵都叫牵挂
能让秋水复归于平静的,只需要
一个电话,大声报一个平安
亲情的涟漪在秋风中荡漾开去
谁也无法阻止儿女一天天长大
我看见窗前的银杏叶在悄悄泛黄
我想象丰收的田野颗粒归仓
我看见拎着包裹的女儿,平静地
走向轻轨车站潮水般的人海
石子的回声,在轻轨经过的地方
把叮咛和嘱托铺张得越来越远
这个秋天,我的心开始在一棵树
会说话的枝头上抖动,或者等待
烧水
一根木柴噙住了火苗
火苗从一根木柴爬上另一根木柴
两根木柴就开始用火苗
相互取暖
只有一根木柴进入另一根
木柴的时候,炉中的火
才会烧得更旺。焚毁乃至融化
才是生活的高潮
壶盖发出的惬意的声响
一定是烧热的水在呼喊
那些不曾被烧过的水
冷静中蕴含着无法预想的狂热
附:
创作谈
——诗歌与命运
我是一个用诗歌这种体裁写作的人,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人。我对诗人这个称呼有着近乎偏执的理解,绝不是发表了一些诗歌作品或者出版了几本诗集,就可以称其为诗人。
窃以为,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就应该是那种像诗一样生活着的人:他敏感、激情、豪放,不与一切世俗为伍;他蔑视金钱、权力,重情重义,仗义执言,不向权贵低头,不为五斗米折腰;他纯净如一汪秋水,纯粹如一缕清风;他表面平静如水,内心波澜壮阔;他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他平凡如草,但仙风道骨,他从平常事物中间找出闪光的语辞,向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我可能这辈子只能作为一个写诗的人存在于芸芸众生,对于“诗人”的桂冠,我只能永远心存敬畏。好在,我一直在路上;对于诗歌,我从未远离。
如果我不爱上诗歌写作,或许我人生的旅途会平顺许多。但是,人生的诡谲,叫作鬼使神差也好,叫作阴差阳错也好,使得我的命运发生了很大改变。很多东西个中滋味,实在是无法言说。
1988年春,我的处女作《男生宿舍》在“蓓蕾杯”全国中学生诗歌大奖赛中获得一等奖。1989年3月,我报名参军。接兵团副团长李艳国得知我的情况后,爽快地签了字:考虑此人的才能,予以接收,决不退兵!这段签字至今还保存在我的档案里。1989年底,我被分配到沈空机关。
沈空机关是个人才济济的地方,我耳熟能详的大概就是政治部创作组著名军旅诗人李松涛了,又是通过姜凤清老师的推荐介绍,我成了李松涛的弟子。认识了松涛老师,可以说就认识了半个中国诗坛。
1991年9月,我考入位于江苏徐州的空军勤务学院航空油料系。然而,由于一位诗友创办的诗社出了一点麻烦,我牵扯其中,当一名空军军官的梦想,随着那阵冷风而消散了。我只能无言以对。爱和爱好,同样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1994年我进入普兰店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做秘书工作,其间,我娶妻、生女,生活谈不上清苦,但绝不富有。精神生活倒是宽绰得多,写作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最终能在大连晚报社落脚,也与诗歌创作有关。倏忽间,我在晚报工作了十个年头。十年,我写了大概不到十首诗。我时常在无人的夜里怀念起诗意的军旅,就无法不想起李松涛,我一度那么执著地想模仿他的人生,但是啊,人生是不可以复制的,我只能听从命运的召唤:我学得了他的语言,却学不到他的深邃;我学得了他的灵性,却学不到他的睿智;我学得了他的忧患,却学不到他的风骨——四十岁的李松涛已经声名远播,而四十岁的我才刚刚开始。
或许诗歌带给人的除了心灵的抚慰之外,还能够改变人的性格。我一直在琢磨自己性格中的率性、天真、不圆滑、不设防、喜怒形于色等等,是不是诗歌带给我的,还是我天生就有着诗人一样的悲剧性格?它与诗人的灵性是相克相生的吗?
2010年12月,我被任命为大连《海燕》文学月刊主编。我重又端起写诗的笔,不为别的,只为了记录下命运那无法捉摸的点点滴滴,仅此而已。
附:李皓诗歌评论
“我在”诗情与生命意志的两全
芦苇岸
在诗人的写作动机中,往往难有类似定律一样的确定性,但作为艺术门类之一域,诗歌的作用或许真如奥克塔维奥·帕斯所言的为人类提供了“相互辨认”的可能,这种“隐蔽的整体的形象”在很多场景下确实让诗人着迷。比如我要论述的李皓的诗歌。李皓显然在不停地被诗意推动着前行,哪怕亦步亦趋。这种无悔的执著姿态,具有旗帜般的隐喻功能——被芸芸众生辨认,亦有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的冷静与激情。作为一个浸淫诗歌数十年的北方汉子,这种“我在”的诗意情怀甚至带有内视的色彩。通读他的诗歌,能强烈地感触他那打开自我的坚定态度,以及对生命意志的持衡之心。
李皓的诗歌创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学时期,成年后,丰厚的阅历和生活的宽度铸就了他更为灵动、细腻、多情的诗心,他的文学之路越发沉稳、深远。细读他的作品,对照他的生活轨迹,不难发现他是一个内心力道异常坚毅的人,他的诗歌道出了他对生活的敬畏,对世道人心的问诊,对山川大地的膜拜,对自然物理的亲近,对亲情大爱的恒常颂赞。
一、沉静的生活疼痛与故乡情结的诗意融会
常年辗转各地使得李皓背负的心灵痛楚日日深重,解读人生的异数更通透,加之诗人本身敏锐细微的洞察力,对日常生活细节赋予哲学与美学的反复思辨,成就了他诗作最明显的个性标签,尤其比照阅读了几组他不同时期的诗,更是惊喜他传递的声音的纯粹、丰盈。
对于诗人而言,经历繁杂会改写诗歌悲喜的格局,事实是不少人沉溺生活的洪流中,往往一蹶不振,沉疴不起,无法完成心灵的自救,但也有人踏平坎坷成大道,视其为孕育诗歌的肥沃土壤,这种游刃有余的人气场超强,能在光怪陆离中独守一份安宁,只留清气满乾坤。从这个意义层面考量,李皓是过硬的,他的诗心成全了他的坚韧。游走在城市各地,他的诗隐透着对生活沉静的痛,又因为他擅长以细腻度量生活,所以能自觉放下身架,褪去清高的外衣,以谦恭的视觉投影和心智过滤对待所目击的一切。但又区别于普通的写实主义,不是零星地再现生活图景,他擅长以“插科打诨”的旁观者方式,理性探视生活和人性的不同面,配之以特有的性灵触觉揭示事物(现象)的内在本质,甚至以互为悖谬或矛盾的心态反转将内心的沉淀激活,进而勾连人生百味。这种由表及里的叙写思维所形成的巨大反差能引发阅读共鸣,并促使读者进入冷静的思考。
在《我得坐车去一趟普兰店》里,多重叙述性意象构成生活里各种矛盾心情的冲突。“在东北师大读研时,我是辽宁人/在鞍山沈阳当兵时,我是大连人/在大连做记者时,我是普兰店人/在普兰店工作时我是磨盘乡人。”全诗在不间断的矛盾转换中透出芜杂人生的诗性真实,产生了一种冷静的硬度,似乎在作者的内心,再光鲜的身份后也总拖着卑微的影子。此诗让我不由想起雷平阳的那首悲悯的《亲人》,率真、务实,李皓也一样,在极力让诗歌剔除杂质,直接道出心迹,体现的是作者的谦卑与担当,当然更是对“诗人”身份的再确认,以及对自我灵魂的清晰辨认与体察。
而就诗的语言来说,他将赤裸裸的犀利的批判巧妙化为冷幽默式的自嘲。正如杨克所言,“一个诗人尽可以以丑角的面孔出现,但这种幽默滑稽的方式所传达的是平民的智慧和力量,而不应只展现人格的猥琐”。这一点李皓做到了,他对生活形态的书写也明显有别于传统主流意识形态,透过许多自我嘲弄,反射出现实生活的阴郁,和勾画出一部分人人格的卑劣。那些自以为是上等人的下等人,打肿脸充当起来的“假胖子”,整日钻营溜须拍马的谄媚嘴脸才是他真正想唾弃,不愿同流合污的原因。所以在他的诗中,反语和调侃形成的巨大思维联想是一大亮点。“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郭沫若语),李皓勤勉为诗,一切尽在五味杂陈的痛中。
二、人性真实与日常诗化的提纯
在消费时代的当下,物质文化对人文精神的冲击不可小觑。李皓摈弃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圣人”姿态,在描摹日常生活的诗歌中努力构建“包容开放,灵动大气”的诗风,将批判、理解与融入合为一体,旨在传达良知,启示真理。而要将鲜活的人性凿刻在日常生活的年轮里谈何容易?李皓在锻造语言内在的气度和智慧上花了不少力气。
“父母健在,明镜高堂/个把小时回父母家吃一顿饭/吃多吃少,吃快吃慢都不重要/只是守候与驻留的时间要慢下来/慢得我们从不曾认为自己的父母/正在慢慢变老。”在《回父母家吃饭》一诗中,父亲的三次催促传递了日渐年迈的双亲渴望子女回家团圆的朴素愿望。“母亲很享受我们的风卷残云……”他的父母从不会计较半年的守候、几天的准备、一整天的满心期待换来的只是半小时的天伦。为人父母给予儿女的牵挂总是这么细腻绵长,这份人性的真实借几个时间词的对比着实让人备感温暖。而人性的繁复犹如钻石的多个切面。
在描写男女情感时,李皓又成功转身化为一张炽热而温柔的“创可贴”。在《创可贴》中,他更热衷独辟蹊径,通过捕捉事物表面的差异来揭示其本质的一致。“我丝毫不想掩饰对你的倾慕/打认识之日起,我就把你视为己有/据说也有人宣誓过对你的主权/但我不在乎,我有我的霸道/……/好吧爱人,对于你的伤口/我永远是一味守候千年的药。”这种爱与哲思通融的打开是无限的,这个“药”的意象,堪比舒婷笔下的“木棉”,十分经典。
一张不起眼儿的创可贴却能在情伤时掩饰虚弱和难堪。这样的类比取象令人耳目一新,在描绘爱情的诗歌中我们习惯了花好月圆、花前月下,寄寓相思的红豆与鸟雀。他却将一张创可贴和一个男人对女人炽热执著的爱黏连在一块儿。这陌生化的搭配让诗歌豁然开朗,诗意沛然。亲情或是爱情,人性的真实投射到生活的激流里就是一个个光怪陆离的斑驳的影子,时而模糊,时而真切。
读李皓的这部分诗歌,脑海里总浮现出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神韵。“生命中会有多少变故,搬家/何尝不是一场别离。当平日疏忽得/几乎认为不存在的大包小裹/重新塞满又一个空间,那放不下的/岂止是一只饭碗,两双筷子?”(《搬家》)日常琐事的碎片一旦被诗歌照亮,就会生成无限的感动,也会为生活多了这样的人文深情而备感美好。写出名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的普希金说过要“用诗歌唤起人们善良的感情”,李皓觉得这份情怀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是多么宝贵,因诗而见李皓也有着别林斯基评价普希金的“天性”——他的内心有着许多赤子似的和善、温良和柔顺的成分,感情中永远有一些特别高贵的、温和的、柔情的、馥郁的、优雅的东西。
“我看见拎着包裹的女儿,平静地/走向轻轨车站潮水般的人海//石子的回声,在轻轨经过的地方/把叮咛和嘱托铺张得越来越远//这个秋天,我的心开始在一棵树/会说话的枝头上抖动,或者等待。”(《女儿的电话》)平白舒缓的叙述,娓娓道来,亲切动人,“我的心开始在一棵树”这样的冲动,已经随着阅读的深入移植到了每一个父亲的灵魂深处。这份“等待”是李皓提纯日常诗意的一个典型案例,占了他诗歌的很大比重,不赘言。
三、生命幽微的异境呈现与醇厚的心灵映照
大城市的喧嚣并未冲淡李皓对诗歌的热情,反倒促使他理性思量,砥砺生命幽微的意境,这期间,他写下大量批判现实主义的诗篇。更值得欣喜的是,他在冷静观察社会万象后能清醒地正视社会沿革的产物——对欲望的痴迷。所以,他的文字一以贯之地将丑陋的人性幻化成波澜不惊的调侃式幽默,剑指人心的黑色风暴,达到惊人的效果。
有的时候,坚硬的文字也有柔软一面。出于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同情,关注底层自然成为他诗歌内容的另一组成部分。《落叶》中的作者将卑微的小人物意象化为凋零的枯叶。“人生一世,你的舞蹈,不比一枚落叶更加轻盈/把喘息留在枝头/把叹息伸进泥土……”在生活这个沉重的命题前,人只能是一张落叶,无可避免地经历萌芽、繁茂、枯萎直至凋零的自然循环。小人物注定有小人物的卑微。即便落叶终需归根也不必沮丧,迎着花开的季节,努力绽放,自由地吮吸生活给予我们的一切美好,成就自己斑斓的春天,也不枉白白走一遭!在看似萧瑟的文字里却又包含对生命的竭诚的赞美,大有枯木逢春的惊喜与感动!
“其实这个秋天,早已/深入我的内心,我的每一寸/肌肤。你却视而不见//含泪的红,是我中年的伤/这一季/鸟儿已飞过。”(《苹果独语》)但凡文字折射出的镜像,均是因为有一双善于发现并且有思辨性的眼睛。李皓在生命与文字中潜心打造精神殿堂,在生活与心灵的激荡中探索人性的微妙;又凭借对生活细腻虔诚的关注,在一个个诗意的镜头里任由思维的浪潮肆虐冲撞,然后将一切激情凝聚成富有张力的文字,呈现出或热情、或谦卑、或醇酽、或知性的诗意景观。超拔的精神正行走与在潜心修为的诗情表明,李皓是一个与时代脉络一起搏动的诗人,并因此而找到了自己的另一个更为真实的身份!
芦苇岸,1989年开始公开发表作品,迄今已在《人民文学》《诗刊》《诗林》等数十家文学刊物发表诗歌、小说、散文、评论近百万字。1999年12月出版诗集《蓝色氛围》。有作品入选《星星诗刊甲申风暴大展》《70后诗歌档案》《浙江诗典》等选本,多次获奖。
责任编辑 林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