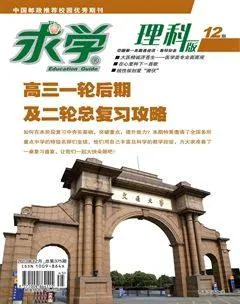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杜甫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陆游诗云“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都讲了在写作之外应下的工夫,很多考生都将其奉为圭臬。但不少考生花了精力,素材的积累却不尽如人意,写作时觉得无“料”可写,陷入一种低效状态。
如何有效突破素材积累的低效甚至无用的怪圈,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己教学经验,献上一得之见,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创新眼光,积累“材料”
这里所讲的“材料”,就是我们绝大多数同学正在积攒的素材:课本素材、时事素材、人物素材、自然素材……翻开厚厚的笔记本,又似乎感觉没有什么值得用的,一谈到苦难就是司马迁遭受腐刑,或者来一段“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很多素材被一窝蜂式积累,一窝蜂式滥用,其结果便是“世上本来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没了路。”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创新,用新的眼光观察、思考、延伸、拓展,新眼光发现、新角度切入、新高度概括,让自己的素材脱颖而出。
提到马云,大多数人想到的就是他高考失败、力排众议创立阿里巴巴等,这些都是老掉牙的故事了,着实难以引起阅卷老师的新鲜感。其实马云已经宣布退休,他的急流勇退才是最值得考生关注的。
二十年以前也好,十年以前也好,我从没想过,我连自己都不一定相信自己,我特别感谢我的同事信任了我,当CEO很难,但是当CEO的员工更难。我从没想过在中国,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缺乏信任的时代,你居然会从一个你都没有听见过名字,这样的人身上,付钱给他,买一个你可能从来没见过的东西,经过上千上百公里,通过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到了你手上。今天的中国,拥有信任,拥有相信,每天2400万笔淘宝的交易,意味着在中国有2400万个信任在流转着。……明天开始,我将有我自己新的生活,我是幸运的,在我48岁,我就可以离开我的工作,在座的每个人你们也会48岁。之前工作是我的生活,明天开始,生活将是我的工作。
这段卸任演讲中有一个特别好的话题:“信任”或者“相信”,而马云说“在我48岁,我就可以离开我的工作”可以说他幸运、可以说他勇气、也可以说他智慧、也可以说他豁达等等,都是非常新鲜且具有价值的材料。
“别哭,孩子,那是你们人生最美的一课。你们的老师,她失去了双腿,却给自己插上了翅膀;她大你们不多,却让我们学会了许多。都说人生没有彩排,可即便再面对那一刻,这也是她不变的选择。”
这是最美教师张丽莉“感动中国”的颁奖词,考生如果只停留于这个阶段,那么文章也难以升华。如果由最美教师延伸开去,谈到“最美妈妈”吴菊萍、“最美司机”吴斌、“最美婆婆”陈贤妹、“最美护士”等一系列“最美”现象,并探寻“最美”现象背后反映的社会文明环境土壤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人们的熏染,文章必定更铿锵有力。
二、深入阅读,积累结构
这里所说的结构,就像是一个“容器”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考场作文不可能把欲诉之怀全然写下来,而一个好的结构就是一个合适的“容器”,能够把生活这条大河中的水舀起一瓢来,让它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之内展示其丰富的姿态。
在议论文的写作中,常见的并列式、对照式、层进式、时评式等,考生们都已经耳熟能详,这里不再赘言。下面着重谈一谈记叙类文章(散文、小说)的结构问题。
瑞典作家斯特林堡的小说《半张纸》选择一张记录电话的小纸片作为“容器”,让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全都以电话号码的姿态凝固下来。看上去只是一个个号码,简单而不复杂,但人生变迁的喜乐悲愁,却被它们穿结在一起。每个号码背后都是一段故事、一番心情,但又被这个“容器”限制着,决不漫溢。在我们的写作中,是否也可以借鉴这么一个容器呢?可以用一个日记本追忆自己的高中生活,或者是一个相册几张照片回忆自己生活中的某个片段,折射家庭或时代的某些变迁。
俄国作家蒲宁的《安东诺夫卡苹果》,整篇小说用回忆的口吻,将我们徐徐带入那个已经逝去的田园梦境中。在对昔日美好的深情缅怀中,抒发对过去生活的留恋,对世事变迁的惆怅和感伤。写农村,写田园,浦宁给我们作了最好的示范,可以写乡村的景、乡村的人们以及乡村的生活方式,更有乡村在时代洪流下的变迁,在今昔对比中,作者情感表达自然而流畅。考生若涉足这一题材,浦宁的这个行文思路是效果极好的。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陈忠实曾经写过一篇《我的秦腔记忆》,完美地将一方水土、一方百姓、一方文化融合在一起,给后学者以无尽的启迪。陈老写的是秦腔,你可以写豫剧、黄梅戏、傩戏、年画、地方风俗等一切非物质文化的东西,皆可借鉴这一构思。
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的著名作家骆文的散文《怀表,很老很老了》,第一层写修表的经过,为下文介绍表的来历作铺垫;第二层写表的来历,凸显父亲的精神;第三层写表的传承,突出作者对父亲精神的感悟。由表及人,层次分明;环环相扣,严密紧凑。将后辈对前辈精神的理解、传承落脚在一块怀表上,文章也因子辈父辈之间精神的传承而有了一种时间上纵深感。一辆自行车,可能很老了;一张老张片,可能泛黄了;一台缝纫机,可能落上灰尘了;一支钢笔,快要被淘汰了;一本线装古书,可能快要散落了……一个个小物件就可能承载着一个家族几代人之间的亲情故事、家族传统、希望、梦想和光荣,这样的结构无疑是极具表现力的,拥有直指人心的感染力。
对结构的诉求要求我们在平时的阅读中不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而要在阅读中下工夫,多从写作者的角度理清作者写作思路,结构特点,技巧方法等,在读的过程中实现写的提升。俗语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大概也有这个意思吧。
三、提升认识,积累“思想”
上面讲到了对素材和结构的积累,对于一般考生而言可能就已经足够了,但如果想要在高考作文中拿到高分,思想的积累则是不可或缺的。这里所说的思想,包括对某事某物的观点、认识、见解、看法等等。不少考生可能认为:我难道没有自己的思想吗?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大脑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但现实却是,在高考阅卷中,能让阅卷老师眼前一亮、心中一动的优秀文章实在是凤毛麟角。大多数文章都处于立意雷同甚至肤浅、幼稚的尴尬境地。
比如一篇写回忆自己童年生活的文章,大多数文章都会写出“每当我想起童年,便能记起……”这句话,或者“回首往事,既喜且忧……”“不知有多少次我在梦中又把自己变成了可爱的小男孩,同儿时的伙伴在老地方玩耍……”错了吗,没有。好吗?很难说。可以肯定地说,虽然童年不同样,但很多人的选材会“撞车”。但若是你曾经读过日本作家志贺直哉的小说《清兵卫与葫芦》和美国诗人狄金森的短诗《篱笆那边》,你的童年题材肯定会有所不同。
《清兵卫与葫芦》中老师与父母粗暴地扼杀孩子的兴趣以及不可限量的潜力让人扼腕悲叹,而清兵卫在父母师长的压迫下不敢吭声,没有捍卫他的兴趣,又让人特别惋惜。父亲呵斥了清兵卫一句,他就不敢作声了,教员没收了葫芦、父亲砸碎了葫芦,彻底地破灭了他的葫芦梦,一个鉴赏葫芦的小高手就此被扼杀,而文章结尾处说父亲又开始嘀咕“他喜欢绘画”了,文章的悲剧意味更深了。
学习了《清兵卫与葫芦》,我们笔下的童年也必能写出全新的体验。哪个孩子没有因为要学习而被父母逼着放弃一些兴趣爱好?或者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写自己小时候特别喜欢绘画,但因为学习而被迫放下了,到了高中,自己因为文化课不够好的原因,又不得已捡起画画这个爱好以参加艺术考试,心中无限感慨……这样的构思岂不是远远超出那些与小伙伴们在一起玩的构思?当然,如果你认真读了鲁迅的《故乡》,写自己儿时的小伙伴以及故乡之人乃至整个故乡的变迁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相对于《清兵卫与葫芦》的悲伤,《篱笆那边》稍显积极明朗。
篱笆那边/有草莓一颗/我知道,如果我愿/我可以爬过/草莓,真甜!可是,脏了围裙/上帝一定要骂我!/哦,亲爱的,我猜,如果他也是个孩子/他也会爬过去,如果,他能爬过!
诗作的立意是深刻的:真甜的“草莓”,正是孩子所追求的世间美好事物的象征;骂人的“上帝”,是权威的代表、正统思想的化身,他禁锢别人的思想行为,但面对美好,他是否也会有“爬过去”的冲动呢?童心童趣童真跃然纸上。
再如面对当下社会环境,人们都有一些不满与抱怨,但真正分析问题时却又难以深入,青年作家徐则臣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没魂走不远》,则将“经济、生态、文化”联系起来,剖析在经济发展、生态得到重视后,无形却又对社会发展的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却被人忽视的问题。读罢此文,或者考生们就可以得出国人外出旅游形象不佳的背后,是因为钱包膨胀的速度超过了头脑丰富充实的速度,各种不和谐现象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如此一来文章的纵深感和立意程度无疑都拔高了不少。
由于实实在在的高考压力,不少考生与外界的直接接触不多,不足以让他们对生活、对现实形成比较丰富、独特、深刻、个性化的见解。那么此时,善借“外力”就显得极为重要。那些作家、诗人、哲人甚至是身边的同学,他们与众不同、超出常人的独特认识、感悟、心得、故事等等都可以当作自己的间接体验、直接认识,勇敢地拿来,为我所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