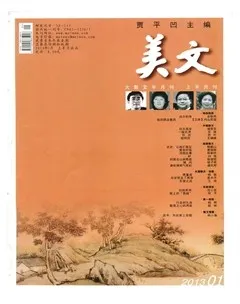一夜北漂
东珠
1978年12月28日生于吉林省敦化市黄泥河镇五人班村,现为吉林省作协会员。现任吉林市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财富江城》栏目组编导。
我终于摆脱了狗的日子,过上了猫的生活。虽然,还没有脱离禽兽的户籍,但是作为猫,要比狗优雅得多。我的身上,猫的特征也越来越多——悄无声息地走路,左顾右盼,不胡乱叫春。猫走路,前腿向前伸得很长,后腿向后拖得很远,尾巴傲慢的绕过地,冲天翘。这样南辕北辙,用尾巴梢问天,主要是为了一旦遇到险情,猫可以进退自如,不至于把前后腿都搭进去。但是,猫的本性,是敢于奢望一条鱼,向着腥味做梦。
我的梦,正在为我张罗一桌好饭。我总是在梦里自助游,它的费用很低。小姨给我炖了一锅鱼,用的是木头锅盖。她纤弱的身躯掀锅盖时,一只脚向后飞伸,一只脚向下点地,这边锅盖拽着右手,那边空气拽着左手。空气拽不过锅盖,她差点栽到锅里。但她品尝鱼汤的样子,还是那样神道——嘴离着勺子老远,唇一吸,那汤就会千丝万缕与未曾露面的舌头相会。这空运的武艺,我学一次被烫一次。我只会用筷子陆运。小姨家今天没有筷子,她支使我去院外,折了两段老绿的蒿秆,乔装打扮成筷子。做这事,我业务熟练,因为小时候常干这寻找替身的勾当。没有电熨斗,我就用热水装茶缸里熨衣服,水热得蹬鼻子上脸,衣服也不会服服帖帖。我还曾暗派红心萝卜汁顶替染色剂,到元宵的馅里去当差,结果是——萝卜像出土的罗衣,见风就失色,白花花的开追悼会。两段蒿秆架起了美味通往肠胃的桥梁。吃得很过瘾,鼻子尖、发梢都滴着香水。这个梦很负责任,售后服务也不错。因为我醒后,并没有因为过度的梦游而双手发麻。那一锅的精神食粮,也丝毫没有在梦醒后,露出短命、忽悠人的狐狸尾巴。我真的吃饱了!
千万不要以为,我多么钟情现在的工作——卖手机。那只是我的一张简易饭票,有下嫁和屈尊的隐患。在工作上,其实我时刻准备着移情别恋,做一个逃跑新娘。我的目标,不是卖一部手机吃十块钱的回扣,而是要吃一辈子文化大餐。粗粮要细做,婆婆丁要缀上诗经的根,就算是挖一棵川贝母,也要到《本草纲目》里过过目。可怜我这写意的村姑,被淹没在这写实的破烂市场里。我认为,那手机,通上电是电器,拔了电就是破烂儿。我对待工作,就像对待爱情一样。对于我不爱的,下死手遗弃;对于我爱的,梦里梦外勾连。这与钱多钱少没关系。朝阳大厦手机市场,外墙壁上贴着一张纸片,方方正正地写着:影视公司招聘,到北京工作。要求文笔好,相貌佳。有意者请到四楼面试。这里面,我独不喜欢“相貌佳”这三个字,它让我很伤自尊。就算我是古典美人,在这大雪滔天的城市里,谁会给我背后安一座故乡的扒山岭?再引一条故乡的黄泥河?让我的村姑美貌昨日重现?但我还是去应聘了,因为我自认为,我非常符合其中重量级的一条:文笔好。外面风悄雪寂,我的心却直打鼓。自上学时起,我一见到“文笔”两个字,就像见了失散多年的亲娘一样。不知怎的,我总认为,在我的血缘库里,还有一个备用的亲娘。而我现在的,是后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特别渴望得一种病——梦游症。因为得了这种病,可以帮我去导演一场相见亲娘的悲情大戏。再说文笔,上学的时候,我才思成片,一直霸占着校园才女的雅号。哪知今日,落得个柴女都不如!但是,天这样冷,我那颗怀才不遇的心,居然没有被冻死!它一经这张招聘纸片的煽风,还未点火,心就先着了。
我偷偷摸摸地去面试。等待我的是一个缸,还有一只筐。男的是缸,女的是筐,都是粗线条的。男的说来应聘啊?我说是。女的说填表吧,明晚出发。我说好。连“三句半”还没有凑上,就聘上了?我的心火灭了一大半。这样的招聘我去是不去?万一我掉进了缸窑怎么办?成天让我编筐担土又怎么办?我低头暗瞅着屋里60后的破椅腿犹豫不决,这现场过于贫穷,我怕日后富不起来。俺娘又来了!俺娘总是在节骨眼上使劲剜我一下,让我浑身刺痛向前冲!俺娘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俺娘还说,不能势利眼,见着金子就笑,见着破铜烂铁就绕。这一鼓舞,让我居然拿出了爷们的义气,打算豪赌一场。俺娘用她的语录,把我送进人生的第一个赌场,然后她退步抽身走了。不管我离她多远,她都能遥控我!她在我身上种下的毒,一遇大事,就发作。
我把表格填完,简单谈了工钱,他们连照片都没要。我一笔一画地填,我想用苏绣的精致,弥补一下他们那麻袋片子一样粗糙的工作态度。一男一女都很老,有气无神。精有没有,我不知道。这只是假象!因为一落地北京,他们就迅速年轻起来。春药是染发膏,女的给男的染头。男女都脱了外衣,露出了劣质的内衣。我说过,我现在是猫,经过了一夜火车的颠簸,我是一只北京的猫了。换了水土的孩子能长大个,换了水土的猫,鼻子更灵敏。我又闻到了腥味!火车是在前一天的夜里出发、早上才到达北京的。这样,我就没有理由直接钻进被窝睡觉。因为在作息上,我一直比较尊重太阳、月亮还有星星的劳动成果。天空也有祖训:太阳出来要起床,月亮出来要睡觉。但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手里没活儿,心也发空。我就用这段时间来研究被窝儿的事!房子不大,只有一个大通铺。这大通铺,多像火炕的假唱!我从左数到右,三床被褥。我又从右数到左,还是三床被褥。这三床被褥,它们的关系过于亲密,我睡在哪里呢?我想我不能打草惊蛇,我要用旁敲侧击的语气套出他们的真实想法。也叫欲擒故纵。我说这床单挺干净呀,这屋子挺好,还向阳……还好,女的上钩了——那好,丫头你先挑,剩下的是我们两个的。这么大的权力交给我,着实让我吓了一跳!因为无论我怎样使用权力,我还得与他们同睡!这样的大通铺,别说是粘连在一起,就算它们独立成章,我也是接受不了。床与床之间,假如拉个布帘,那也是糊弄鬼呢!我很镇静,我说了声“谢谢”后继续寻找我的藏春之地!我觉得我是春天,我脱了衣服就是春光乍现。内衣有什么用呢?这样的无能之徒,只会出卖我胴体的轮廓和曲线。我用眼睛侦查了各个角落,除了厕所之外,再也没有别的私人空间了。女的还在为男的染头发,一边染一边说着各自的家事。家事里,我听到了两条重要的信息:一是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家庭。二是他们离了各自的家庭就长期同居在一起。他们不是鸳鸯蝴蝶派,而是野鸭胡来派。他们的对话是这样的——男的问女的:“你来这里,你老公很愿意?”女的是这样回答的:“他有什么愿意不愿意的,我是出来挣钱的。”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台词,原比剧本要精炼得多!还有,俺娘从小就教俺,听话要听音。这弦外之音,我是听明白了,假如我睡在这里,我还得兼两份职——晚上,我做电灯泡,发挥我的光和热。白天我也做一只鸭,是正在被驯化的野鸭,大脚板子呱唧呱唧地踩在北京的大地上,为他们鼓与呼。至于我的文笔,毫无疑问,已经沦落到艺妓的地步了。假如我是男生,我豁出去了!为那朝思暮想的“文笔”做一回下人,也无所谓,因为英雄不问出处。可是,我是女生。我骨子里一直在为贞洁效忠。现在“贞洁”这两个字,在我的心中,它的范围更广了,交友的贞洁,职业的贞洁。我这天生的处女情结,宁要花灿,不要花烂。我是带着俺的老家敦化市五人班村一村的风气,来到这里的。北京的风,虽然很大,也不能把它们吹散!正气是吹不散的,只有邪气天生理亏,四处躲藏。我不能住这!我没有再等俺娘的语录,就自作主张、速战速决了!男人的头发弄好了,一色的向后背,等待黑色长相依。经过女人的手,一顿搓摩,那残存在脑袋上的发丝,显得居住环境更宽松了。但这傻大憨粗的背头,一点也不艺术。我断定他们做不出文化大餐,咸菜也不会。因为我到现在连一粒咸盐豆也没有吃上。
中午,大人物出现了。听说是这家影视公司的老总。老总并不上楼,就在楼下等着我们。后来我才知道,是专门等我。那一男一女说老总要带我去公司实习一下。我想,假如还有比大通铺更体面、更安全的公司在等我,也许还有转机。我就这样上了车,一抬腿的事。北京确实很大,楼群像密集的火柴盒,桥像俺爹的长烟袋,花坛像烟袋锅。那么我是什么呢?是烟灰?我地理学得不好,不知道我现在正在哪个纬度上实习,又将实习什么?他开始查户口,还是老配方——家里有几口人、老家在哪里、在北京还认识什么人。我一五一十地回答着,家里有七口人、老家在敦化,在北京没有别的认识人。他对我的回答很满意,我能感觉到,他的眼睛在大墨镜下使劲笑了一下。太忘情了,那笑容,镜片没有兜住,漾出来了。这泛滥的眼波,我总担心要翻船。加了油门,接着绕!我在琢磨他为什么笑?我开始做老牛吃草倒嚼的事,把说出去的话,再倒腾回来——家里七口人,老家在敦化,说明天高老子远、孩子多不缺我一个。在北京没有别的认识人,说明可以任人宰割、没有什么急救措施。我碰上对手了,他也会琢磨弦外之音!但我诉说的是我的家族正史,他硬是当野史处理了。太可怕了!他很胖,穿着墨绿色的布衫,只有领子,没有扣子,直接套头上。但是他的裤子有扣子,前开门。我之所以能看到这些,是因为我在所谓的大人物面前,总是自卑得抬不起头。所以我的视线只能聚集在他的脖子以下。然后顺便看看肚子、腰、腿、脚,以此推断他那颗脑袋,是豪华版还是流浪版。还是接着绕!我说咱们这是要去哪?他听见我说话,便啊啊啊啊的上下左右全部啊了个遍。最后,他掏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一会,我们就到了另一个男人面前。老总介绍说这是电影明星。我上下打量着眼前这颗星,金丝猴的眼睛,长着一身的腊肉,血脉不畅通,是被什么盐渍的?他叫我进屋里坐,从床上到车上,这回我总算是坐到了貌似贤良的办公椅上。他叫我小姐,我没有应声。我想他究竟是从几亿光年里跑来的呢?又在哪个星球演过戏呢?还是查户口,还是老配方。不同的是,他还问了我的年龄、有没有男朋友。然后就大笑着说,王总好福气啊,能找到这样的员工。我听完,脸又红了。我的脸,特能出卖我。也是我太脆弱,我都是北京的猫了,一听到男女之事,还是脸红。脸一红,那明星又大笑说,小姐好腼腆。我觉得他把“福气”和“腼腆”这四个字都糟蹋了!我想他演戏是不是也这样?那一刻,我的屁股坐在北京的椅子上,我的腿已经决意撤退了。
茶我没敢喝。出了明星的屋,太阳就要落山了。我滴食未进。弄明了老总姓王,也弄明白了我今天的实习要领,功夫在诗外。太阳就要落山了,我落哪?我想现在那一男一女,是不是正在床上办公?王总让我上车,这一脚我是极不情愿上抬的。但是,偌大的北京让我望而却步。我不上这个车,我上哪个车?上了这个车,我又怎么办?我假装低头系鞋带,然后在自己的脑袋里打架。两只都系完了,还没有想出办法,这时后面有人鸣笛了。交通,只在乎车是不是有道走,却不在乎人是不是有道走。那里一叫唤,我无路了。上了车,他又是绕!我很饿,车上一粒吃的也没有。我心发慌,这回我体会到了俺娘说的——饿急了,像筛糠一样直打晃!我把手捂在胸口,我要让它停止筛糠,别干扰我。我闭上眼睛,在大脑里搜肠刮肚地寻找可以搭救我的人。最后,我在他的姓氏上停了下来。下面,就由我导演吧。我攒出浑身的力气,把笑攒到脸上显眼的位置。我说,原来您叫王超啊!我刚才听明星说的,世界真小啊,我哥哥认识你,他总跟我提起你,我太幸运了,到哪都能碰到熟人……我又从丹田处积攒了一些力气,运到脸上,欢快地笑了几声。这一笑,把他笑毛了,他的方向盘突然死机了。然后他又低头鼓捣,这和我系鞋带是一样的。我的后背沁出了冷汗。我想这招好使,继续!可喜的是他说话了,他问我你哥在哪工作?我说我哥在化工部门工作,经常与你们打交道,我哥还说与你喝过酒呢。我哥还说,那小子不错!我又笑了一下,云淡风轻。他狐疑地回忆着,摸着啤酒肚排查。我怕他摸不着真人又要为难我,就赶紧递上话说,王总您把我拉回住的地方吧,我回去好趁早写写今天的实习感想。他还在摸,好像非要摸出一个“带着我继续绕”的理由。但我已经不怕了,他内心的壁垒让我用一个哥哥给击垮了,余下的破墙头,我一脚就能踹倒了。真想踹他。
我赢了!接下来,他以发疯的速度,把我拉回了出租屋。看也没看我一眼,让那车冲着我放了个大屁就走了。我讨厌这味道,捂着鼻子上楼了。那一男一女正在做饭。这一对野鸭在这里,俨然一对家鸭。虽生不出一只蛋,但做窝的热情异常高涨。吃饭了没有?女的看着锅里的菜,也不知道她是在问锅还是在问我。能不吃吗?王总能不请她吃吗?男的也没有看我。我想,今晚这里是没有我吃的饭了。我的肠胃,已是一整天一整夜没有吃东西了。来的时候,只在刚上火车时吃了一根香蕉。我只能说吃过了!没吃过,多不正常啊。我说我下楼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七拐八扭,找到了一个电话亭。北京的大妈们都在电话亭附近坐着,说话时每一个尾音都向天翘着。我确实是有一个哥哥,也确实在化工部门工作。但是,我们已经很久没有通电话了。那个哥哥是我的远亲,我连爹娘都不想长期打扰,更何况远亲呢?我很独性!凡事不愿求人。上中专时,我因为生了一场大病,生活费透支了,我就用仅剩的五十块钱一分一毛地硬挨到了放寒假。五十元,我度过了三十天,只有白开水是管饱的。我的生存体验都是挑战极限的!那我也张不开嘴管家里再要钱花。生病不是理由,为什么生病,才值得追究。我这种自虐性质的毅力,今天借不上力了。因为我不知道今天晚上住在哪里?我被一张纸片骗到这里,哪张纸片可以把我捎回去呢?我给哥哥打电话,我要有一个备案。假如我真的无处可住,哥哥或许能帮我。抓起电话,眼泪就都跑出来了。冲到了周围的大妈。大概这个地方,曾经上演了无数场的“外来妹电话亭忏悔记”,大妈们太了解剧情了!她们很快就把我包围了——闺女快回家吧,这里竟是骗子。你家在哪?快点回家吧!我听到“闺女”这两个字,眼泪就开始泄洪。这“闺女”的叫法,只有我奶奶活着的时候,才会摸着我的头说,这“闺女”长得真俊!我没想到在这犄角旮旯里,那声亲切的“闺女”还会还阳。我止住哭,开始给我哥哥打电话。哥哥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仿佛他就在我身边。但是我说不清楚地址,大妈们也说不清。她们都是来北京给儿女们看孩子的,学会了北京话的尾音儿,却没有学会看地图。因为只要是不逃跑,就用不着地图。我亲自导演的这场安全大营救,到后来,我只有演戏的份了。我按照哥哥的指示,上楼收拾行礼。我的行礼很小,在别人看来,那只是一些换洗的内裤和袜子。这行礼好像也知道我今天必须得离开,因为行礼没有打开,我抓起就可以走人。我对那一男一女说,我有一个亲属也在北京,我要去那里住一晚上,明天一早再回来。因为他们在面试我的时候,从来没有问过我在北京是否有亲属,所以我可以保证,我的这个谎言在一个小时之内不会被揭穿。那一男一女已吃得满嘴流油,嘴唇腻而肥厚。我想到了猪,一下子就吐出来了。胃空着更经不起这大油嘴的刺激。快走吧,看来是晕车了。那女的一边刷碗一边让我走。我说再等会,他们来接我。电话打进来了,借着大油嘴,弄明白了具体方位。女的撂下电话,说你把电话号给他们的?我说是,因为我弄不清这是哪。我说我走了,明早见。一切安排妥当,天已经黑透了。我已经没有力气走下这个楼了,先前我是生死未卜,不得不活蹦乱跳地强装有劲。现在不行了,我只想大睡一觉。
我住到了学校里。是哥哥的两个朋友把我送到了这里。哥哥在吉林,我的心也已经回到了吉林。那两个朋友问我吃过晚饭了吗?我说吃了。我只能说吃过了,天这样晚了,我觉得他们问过我的饥饱,我就很满足了。校园真安静,这是放假的时候,一个学生也没有。这里的床单很干净,打心眼里干净,像月光一样。素白的月光,与洁白的墙壁联手为我隔离出了一个可以做美梦的空间。这空间,是柔和的渐变色,很艺术。明天,我就要回去了。这北漂的一夜,因为前面铺陈得过于惊险,所以现在异常静谧。今夜,谁能与我共眠?多想再梦见我的小姨,再给我做一顿木头锅盖的鱼宴,再折两段蒿秆……小姨已经去世了,在二十三岁。就是我现在的年龄。她天生有病,不能生孩子,就被俺娘乱点鸳鸯谱点给了一个她不爱的男人。一个草本,一个木本,不求开花结果,只求相安无事。她长得像梨花一样美,而我是她身上飘零的一缕香。前世的香缘、后世的知己。我知道她心里的苦楚,她也知道我心里的不甘与挣扎。我与她,是在阴阳接力。我遥望着温润的月光,我想我有必要再次总结、规划一下我的人生:土地养活了我,同时也囚禁了我。命运试图软禁我,有吃有喝有规律,可以果腹度日嫁人生孩子。但我活着,不只是为了吃喝嫁人生孩子——这一套传统女人的佩饰,我不能尽兴。我的心,又野又大又执着。我要用越狱的方式,越过高墙,冒险求生,光明正大地追求我想要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