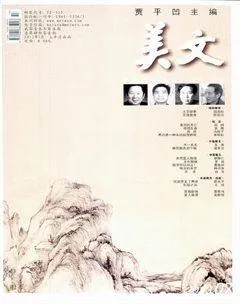乡村散板
粮仓
一年一年,大地上生长着谷物。一年一年,农夫们——其中就有我的乡亲,手持镰刀把这些谷物收割回家,把稻谷和谷秸分开,在打谷场上,将稻谷堆成了一座座小金字塔,稻秸则码成垛,城墙似的垛。
一代一代人就靠这稻谷活下来了;每天,村庄上空都飘起缕缕炊烟,这就是生命的旗帜,这就是人间烟火。
我生长在一个简朴的村庄。那年月,还是集体所有制年代,打下的稻谷都归生产小队所有,然后按人口、按劳动工分分配。在分配之前,先要把粮食挑进队里的粮仓储藏。
粮仓位于村落中心地带,是一座要走一段窄巷才能拐进去的幽深的小屋;进门左侧是三间小仓,往右转,是两排相对的小仓,一起大约有十数间小仓。当粮食储藏进去,每一间小仓的门板都一格一格上上去了。每当看到那些紧闭的仓门板,我们就在想象,这里都是一粒粒金黄的粮食,都是我们的口粮啊!当然,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仓里的粮食只能偶尔窥见,平时整个粮仓都是紧密地封锁着的。
但是,到了年底,粮仓的大门便已敞开,而且每一间小仓的门板也都一块一块卸了下来,堆放在仓库一角。于是这里便成为孩子们的乐园。我们像小松鼠在树上攀缘跳跃一样,在每一间小仓房里到处乱钻乱窜,打闹个不停;粮仓真是天然的捉迷藏,躲猫猫、藏宝寻宝的好地方。
我们尽情地在这里玩耍,常常忘了肚子饿,忘了天色已黑,忘了外面正飘着零星的雨或雪花……只有一串串笑声在空空的粮仓里回荡。
粮仓已空。只有一扇扇洞开的小门,一任我们爬上爬下。我们根本不理会这些粮仓空了意味着什么,即使知道不仅这里已没有粮食,就是我们自家的米缸里粮食也不多,然而我们丝毫不知道发愁,我们只知道玩啊,乐啊,只有一串串笑声在空空的粮仓里回荡。
后来,我真的很奇怪,我们当时怎么会那么地感到欢乐?我们难道不会问一个“愚蠢”的问题:假如我们的粮仓里从此再也没有粮食储藏进来怎么办?假如大地上再也收不到谷物怎么办?
我们没有读过《圣经》,不知道上面曾经记过“耶稣”的一段讲述:“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可是人毕竟不是飞鸟,人是有可能饿死的,就在我们出生的几年前,村庄里就有许多人饿死……但是,这一点都不影响我们在这里尽情地捉迷藏;我们不担心下一顿会不会有饭吃。或许,这是大人考虑的事;或许,我们潜意识里都觉得,这么广大的田野,哪里找不到一点食物?
只要土地上还能长出绿色植物,只要春天还会来临,大地上照旧会郁郁葱葱,我们就是安全的,我们就会有食物。
现在想来,我们生来就怀有一种基本的信任。我们信任我们的大地,所以我们的笑声才会一串串在空空的粮仓里回荡。
现在,我们还会有这种基本的信任吗?在大自然,在大地日益被肆掠,被侵蚀的今天……
村路
那真的是我吗?我真不敢相信,门前的一条村路曾经凝聚着我童年那么多的欢乐。我仿佛从小就生长在村路上,我的灵魂从来就纠缠在这条村路上,游荡在这条村路上。
这也情有可原。我家的门前就是这条村路,或者说,村路正是经过我家的门前。正是在这条村路上,我两三岁就迈着蹒跚的脚步摸爬滚打。我曾经一个人待在门外——这似乎是妈妈第一次把我丢在外面,一阵剧烈的鞭炮声从村西边传来,吓得我惊慌失措,急忙叩响我家的院门,喊着:妈妈,妈妈……
但接下来,我就站得稳当些了。我在村路上结识了村里的许多小伙伴;我们在这里追逐,放飞纸折的飞机;在路边挖沟、植树——当然是比小草大不了多少的小树苗。似乎整天都离不开村路。
这条村路从西边的山中蜿蜒而来,向着东方的平原逶迤而去——走出我们村庄不远就是无尽的田野——这条村路似一条飘带,把大山联通向外面广阔海洋似的世界;正因如此,村路上每天人来人往。从山里出来的人肩挑手提,驴驮车推;往山里去的人也行色匆匆。这是每天都上演的风景。我们每天都能打量到来往的人,每当手扶拖拉机突突地开来,我们还欢呼雀跃,跟着撵,跟着跑;遭到呵斥,不服气,甚至在村路上挖个坑,上面盖上树叶,想要让开拖拉机的人吃点苦头。
又有娶亲的队伍经过,他们常常是趁着暮色;我们则循例要“砸新人”,给新媳妇的脸上抹上锅灰、泥土,乱扔土坷垃,甚至石块;不慎将人家砸破了皮的事也是有的,偶尔还会因此发生纠纷……
真不知道那时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劲头。那时候,村庄里的大人也没有如今这么忙,他们也有工夫——哪怕只是夜晚,三三两两聚在村路上闲话、纳凉,看我们玩游戏,胡闹腾。
在一个夏夜里,我还曾学《沙家浜》里的郭建光,带一支队伍出没在夜幕当中,乃至爬到村路边打谷场的围墙上奔跑、呐喊,结果不慎跌下,脚踝被玻璃碎片割破,血流如注……
这真的是我吗?我真的不敢相信。还有,当中学里的女生上学、放学从我家门前走过,我们也要前去骚扰人家,因为其中几个姑娘的长相是那么漂亮,我们不去喊她们,骂她们,不向她们丢石子,总觉得心里有什么放不下。有一次闹得厉害了,她们反过身来要打我们,还要找家长告状,妈妈走过来生气地把我拽回家。一转眼两三年就过去了,我已渐渐长大,竟然意识到自己真的喜欢上了其中的一位姑娘。有一次,她和伙伴们乘拖拉机回家,不知为什么,那拖拉机竟把他们颠簸下来了,正与追撵拖拉机的我的头撞在一起,我心里觉得那真是甜蜜的一撞。
这一切都快过去四十年了!我不敢相信,时光过得这么快。那条村路还在我家旧居的门前蜿蜒,只是走的人少多了,肯定也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
想起来,我也正是沿着这条村路走到外面的世界的,而且一生都将是一名游子,再也难得回一次老家。
想当初,我还没有上学哩,妈妈就教我认识了几个汉字;为了显示自己已经识字,我把板凳搬到村路上,在一个小本本上一笔一划地书写那几个刚认识的字,还引来一个后来参军入伍的邻家大哥哥前来探望……现在我不自觉地还要这样认为:我在门前村路上识得的这些汉字其实也是一条村路啊!
它们都是我生命的脐带!
邻村
我曾经写过一段散文诗式的文字,大意谓:邻村虽然与我所在的村子挨得近,但是,他们有什么样的风俗习惯,他们的人际关系如何,他们的“工分值”(生产队时社员按工分计值)是多少,对于我们都是一个未知数——所以,我们根本不能真正走进邻村。
这当然有些夸张,但邻村在心理上与我们总有些距离倒是一种明显的感觉。虽然邻村的确很近,甚至我们原本是一个村庄,只是为了便于管理,才分成两个自然村(生产队)的,但是,一经分开,那就是外村了。两个村庄隔一条村路,一个打谷场,但总觉得他们的房屋也都是背对着我们建的,门不朝向我们这边开。
很小的时候,我跟一个大孩子要通过邻村到远处去,可是邻村路口一户人家养了一条大狗,人一靠近,那狗就要从卧着的地上爬起来猛吠;我们硬是闯关,丢了几块土坷垃吓唬那狗,仍被它追上来了咬了裤管、脚跟,好在都不严重。这在本村是从来没有过的。邻村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如此。
稍大后,两个村庄的孩子各自为阵,互相“开仗”的事时有发生。这种“战斗”,也各有胜负,互相占不到便宜,所以“战火”倒未蔓延,经常是相安无事。到了上小学,两个村子的孩子同在一个课堂上课,还不时地发生“战事”。我与他们就打过一架,甚至把大队支书儿子的头打破了,惹得他妈妈在田埂上一顿乱骂,什么“山头上的水,人头上的血”云云,我都不知何意,后来才明白,是说人头上的血金贵,头被打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
再长大我们就不再干仗了,甚至互相有了往来。我有时到比我大的孩子家去借书,因为毕竟是邻村,还是去得少,所以对他们的村巷、屋舍、池塘、竹园、庭院什么的都觉得新鲜。在那里看邻村的人从井里提水,和邻村的孩子一起在池塘里游泳,一起到园子里摘桃,到树上捕蝉、捉天牛,常常乐而忘返。
两村相接处的邻村人家靠着打谷场有一片很大的菜园,菜园里不仅有碧绿的菜畦,还有一片小小的桃林。春天,我们村的孩子常常翻墙头到那菜园里偷桃,或把桃枝拽过墙来,在我们这边“叠罗汉”把桃摘下;如果被这家女主人发觉了,我们会呼地跳下墙,一阵风似地四散,空让她在那里叫骂……
但是,对于邻村,我们到底还是所知甚少,他们的作息习惯,他们各个人家的人口情况,他们的亲戚及其如何来往等等,我们都不甚清楚,虽然田陌相连,檐宇相望。
我只知道邻村出落得好几位美女,这倒是胜过我们村的地方。这几位美女或自己考取了学校,有了工作,或顶替到了城里,或随军去了远方……偶见她们回来,一个个衣着光鲜,举止大方,就像是城市姑娘。我只与其中一两人有过几次书籍上的往还。
我们国家最小的行政单位大约就是村。村下面还有自然村,其实那已是一个个自然聚落;但每个聚落才像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家庭里,我们互相是熟络的;再稍稍扩大一些就有一些陌生感。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一个人真正能接受的、觉得亲密无间的,恐怕就是一个村庄(自然村)那寥寥几十户人家。
何况县与县之间、国与国之间呢?那彼此的距离真不知道有多大。
当然,这是从小处看,从大处看呢,则是天下一家。
偷牛贼
诗人海子有一首诗写道:“雨夜偷牛的人/爬进了我的窗户/在我做梦的身子上/采摘葵花。”
这真是奇特的臆想,连“偷牛的人”都可以入诗,成为美的意象,令人惊叹。这是因为海子从小生长在农村,对于乡村生活的形形色色刻骨铭心。当然,这里的“偷牛的人”也可能有超出本义之外的象征意义。
我的家乡与海子的故乡相隔不远,海子诗集里写到的乡村情景我都非常熟悉。比如这“偷牛的人”,我小时也经常听人说起,当然,各地也都有偷牛的人,只是海子笔下的偷牛的人更让我感觉“亲切”。每读此诗,总能唤起我一点微末的记忆。
在手工劳作的农业社会,耕牛应该是不可缺少的生产资料,农民们自然都十分重视;“二十亩地一头牛”,不正是以往多少代农民共同的梦想么?历代官府也同样注意支持农民蓄养耕牛。西汉的龚遂任渤海太守时,因其地连年饥荒,民多为盗劫,他便“劝民务农桑……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成为佳话。同样,历代也将盗牛列为严厉禁止。
我生活的小村庄只有三十几户人家,一般只有三四头耕牛,负责翻耕百十多亩土地。因此,耕牛和犁田手都十分辛苦。
买一头牛颇不容易,先要联系数十里外的养牛专业户,一般买来的还是牛犊,要精心饲养长大,所以乡亲们都对耕牛极是呵护。但是,就是这样,仍有大胆的偷牛贼趁隙来偷,有的得手后,贩卖到别处,乡亲们还四处察访,将之追回,虽然常常颇费一番口舌。
我当然没有做过偷牛贼,也没有目睹过耕牛被盗的过程,只记得当耕牛被盗后,村里群情汹汹,欲得盗贼而食其肉剥其皮,同时还纷纷攘攘要去追。从乡亲们口里得知,偷牛贼大多是趁夜深人静时分潜入,为了不惊动村里的狗,他们一般预备下毒药或炸子——用猪肉裹着的,投入拴有耕牛的院子和牛栏,将狗毒死或炸死(响声不要很大),然后再去拔牛桩,剪牛绳。还听说,有的盗牛贼更残忍,他不是偷的活牛而是牛肉(因为牛毕竟走得慢,容易被赶上),所以干脆就当场将牛宰杀,大卸八块,直接运走销售。这种方式更是让乡亲们气愤不已。所以,一般抓住了偷牛贼,村里的壮男力就会一拥而上,将他捆住,吊起一番狠打,乃至不慎失手将人打残、打死也都有的,然后再去报官。
因此,一般人也不敢轻易去当偷牛贼,我们周围几个村落历史上也从未出过一个偷牛贼。但是这一纪录在某一年被打破了,而这不光彩的贼名竟然落在邻村一位我的本家身上,而且这位本家还做过生产队的队长,家境也不错,儿女成行,个个都长得比较精神,他的大儿子还考上了中专——那年头的中专在乡村里也不多见,还分配到外县政府机关工作;但就是这么一位平时在乡亲们心目中形象甚佳的年过五十的长者,有一天却听说他在某地偷人家的耕牛而被抓住了,遭到一顿毒打。人们都不敢相信,我也不愿相信。但是,村子里从此真的不见其踪影,后来据说被判了两年徒刑,他那一个个体面的儿女自是脸上落了一层霜。两年后这位长者被放回来,身体已垮,最初还能略略在村里走动,很快就卧床不起。出于礼节,母亲让我前去探望——其时我已上了大学。我走到他的床前,见他斜躺在床头,面容有些憔悴,头发更加花白,眼睛倒还清明,但中气已明显不足。我坐在他的床榻前,除了寒暄,只略略说了几句闲话,就告退了。回来的路上还觉得不可思议,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偷牛贼”三个字跟他联系起来,我多么希望他起来喊冤,可是没有。看来他真是一念之差,毁了一世清名,这是多么地可惜!
人性之不可捉摸,命运之难以掌握,往往类此,岂能不慎哉!
杀 狗
在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农村一直处于饥荒的边缘。虽说粮食还未十分短缺,加上瓜菜什么的,勉强能填饱肚子,但是,肉食除了过年过节有一点外,平时是断乎没有的。
而一般十来岁的少年,正处于长身体的年龄,寡淡的肚腹充满对油水荤菜的渴念也就可想而知,于是,头脑稍稍灵活一些的孩子便常常把脑筋动在捕食一些野物上,如掏麻雀,撵野兔,捉鱼虾鳖鳝,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往往集体行动,看似在一起玩闹,结果把这些“野味”捕来了,也不各自拿回家去,就借某个五保户的锅灶稍稍清理一下,便烧煮吃了,此之谓“打平伙”。
某一个青黄不接的季节,无鱼虾可捕,无野兔麻雀可捉,一群少年在我家隔壁的五保户大叔家里玩,大叔是抗美援朝伤残战士,既无妻子,也无儿女,平时正是能和我们玩得到一块。这天下午,大家玩得尽兴,却感觉有些饿了,正准备在哪里搞点食物垫垫饥,然而大叔家的米缸里只有浅浅的一层米,是无法满足大家的食欲的。怎么办?大叔正巧看见门前的小树林里有一两只黄狗在游荡,便一拍受过伤、弹片尚未能完全取出的大腿,说:“有了!就吃那只狗。”
这帮孩子吃过各种能找见的野物,但都没有吃过狗肉。虽说村子里的几条狗既说不清来历,也分不出来哪条是谁家的,但都是总在村子里转,跟家养的毫无二致,何况平时为看家护院,这些狗也是出了力的,正是因为它们的机警,人们才成功地撵跑了几起偷牛盗猪摸鸡的贼盗,所以,大家对这几条狗也还是有些感情的,现在情急之下,对它们动起了念头,自然有些不忍,但是,饥饿和饥饿带来的旺盛食欲很快驱除了这一点“不忍”。
有两三个大点的孩子拿着绳子,悄悄逼近了小树林,其他人都扒在五保户大叔家的门框边偷窥。只见那几个大孩子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到那两条黄狗——背上的毛是淡黄的,而腹部雪白——身边,突然,拿绳的少年一转身,刚才温和、甚至有几分讨好表情的脸顿时露出狰狞的面目,狠命地把绳子套向一条狗的颈脖,另外两个少年也似兔起鹘落,把身子向狗扑来,双手猛按下去。被套的狗被吓了一跳,后腿向上一竖,同时扭过脖颈,张开惊恐的眼睛,看向这几个少年。那另外一条狗更是机警地溜向一边,吠叫了几声,眨眼就扔下同伴,不知溜到哪里去了,只剩下它那不幸的同伴在拼命地挣扎——这种挣扎是猛烈的,但还谈不上是狂怒的,它那张开的嘴也没有要撕咬人的架势,它似乎还不以为人们真的是要结束它的生命。它差一点就挣脱了,事实上,它从少年的手里挣开,但刚跑了一两尺远,还是被死死按住了,它不能吠,只能呜呜地喘,加上嗷嗷地叫,终于被勒住了脖子,吊在两棵小树之间,双足垂地,仍挣扎不停。接下来,是要人抡着大棒把它敲死,这到底是一件狠心的活儿,有个少年敲了几下,没有把它敲晕,它嗷嗷地叫得更厉害了;又一个少年接过大棒,朝它狠敲,它的叫声才渐渐地小下去。这时候,已有许多村人前来围观,并没有一人出来干预。少年们见狗已老实多了,似乎已昏迷过去,就把它放到了地上,喊人拿刀剪来剥皮;没想到,在地上躺了一会儿,那狗却忽然一跃而起,向树林外逃去,少年们跟着去追,无奈那绳子还套在狗的脖子上,没跑多远,那狗又被逮回来了,吊在树上,又是一阵棒敲,这回它是彻底缴命了,它被打得鲜血淋漓,叫人不忍目视。围观的人先是感叹不已——他们说狗属土性,打昏了放在土里还会复活,果然!接着,就喜笑颜开,开始议论这狗好肥,可以剥几斤肉,皮毛可以卖多少钱或裁多大一块褥子;也有人开始凑近,问能不能分一点肉给他,或者他出一点钱也是可以的;一位慈母看大家都想分一杯羹,她想起自己的儿子也已好久没有打牙祭了,便上前对少年们说:“也给一块狗肉给我家‘狗儿’(小名)尝尝。”她的话惹来一阵轰然大笑。
惭愧的是,我也是围观的人中间的一个,按照见者有份的规则,我也分得了斤把多狗肉。我把狗肉拿回家,母亲把它洗净,就搁在地上的砧板上,然后拿砖头在地上支了个临时锅灶,我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她回答:“狗肉不上灶。”
呜呼,可怜的狗!
村 井
“童年时,他们没能把我从井边,从挂着水桶和扬水器的老水泵赶走。我爱那漆黑的井口,被框住了的天,那水草、真菌,湿青苔的气味。”
这是爱尔兰著名诗人希莫斯·希内的名作《个人的诗泉》中的开头一段,写得真好。写得好,是因为写出了许多人共同的感觉。不仅如此,希内还将这里的“井”赋予了象征的意义,所以这首诗的题目中文版有的译作“个人的诗泉”,有的就干脆译为“自我的赫莉孔山”。为什么要这么译呢?赫莉孔山是希腊神话中司诗女神缪斯的住处,那儿有一口井,是诗人的灵感之源,所以,在诗的结尾,希内写道:“去拨弄污泥,去窥测根子,去凝视泉水中的那喀索斯,他有双大眼睛,都有伤成年人的自尊,我写诗,是为了认识自己,使黑暗发出回音。”
确实,大地上的井总是能给人以灵感。因为灵感与井里的泉水何其相似,都是从地层深处滋涌出来的,都澄澈、纯净,都清凉、甘甜,都映现着蓝天日影,给人以美好的遐想,而且都给人以神秘感。
或许是与诗具有一份天然的不解之缘,我小时候也极喜欢来到井沿,把头俯到井筒里,凝视若隐若现的倒影和明暗交错的波光。我总在猜测这井泉是从何而来,它会不会有一天神秘地消失;我有时对着它轻轻地呐喊,它会发出重重叠叠的回声,愈加令人感奋;但有时我又莫名其妙地恐惧,一恐惧,头颅更加沉重乃至晕眩起来,我希望却又生怕井里会有什么冉冉上升,拽住我的手……
我上学的时候,每天要路过乡政府(那时是叫公社)。在它的厨房的一侧,有一间长着几丛茂草和茁壮的梧桐树的小院,小院里就有一口深井;平时是盖着盖子的。因为经常要在政府院落里玩耍,跟大师傅都混得有些熟悉,有时他也允许我们到井边好奇地探看。那情景正如希内在诗中所写:“烂了的木板盖住制砖墙里的那口井,我玩味过水桶顺绳子直坠时,发出的响亮的扑通声,井深得很,你看不到自己的影子……从蕨丛和高大的毛地黄间跳出身,一只老鼠啪一声掠过我的面影……”就是此时此刻,我似乎还能再次体会到井沿边惴惴战栗的感觉。
我们村子里的人都到池塘里挑饮用水,而不用村西北角的那一口井,那一口井已成废井,我一直疑惑不解。甚至在大旱年月,也宁愿去邻村的井口排队汲水也不愿把废井清洗一下加以利用。我很小的时候问过妈妈,这是为什么?妈妈支吾其词,语焉不详;稍大,妈妈告诉我,井里淹过人。
那是谁呢?是村里一位剃头匠的儿子。这个孩子生来有点“不凡”,不仅相貌清秀,眼睛很大,而且有一副好嗓音。还没有上学,就已跟着广播里播放的音乐学会了唱歌;上了学,他的音乐天赋更是获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赏,每次上音乐课,别人教了几遍都唱不会的歌儿,他两遍下来就能唱得非常清晰。但是,他的性格却有些孤僻,基本上独来独往,就是在家的时候,也喜欢支着腮,坐在桌子边呆呆地凝望面前的池塘。他也喜欢到井畔去,把头俯临井口,去看那一汪清泉。村里人都说他有些怪。终于更奇怪的事发生了,有一天,家人没有看到他的踪影,就到处找,却在井畔听到他的轻轻地回应。家人过去一看,他正双脚岔开,蹬在井壁上,双手也紧紧地扣着井壁的石头。慌忙把他救起,问他缘故,他答说他正从井畔跑过,不小心,一个健步就滑倒栽进了井里——其实,井上还有高达两三尺的水泥井沿,这真是莫名其妙的事,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事后,他似乎清醒了些,学习成绩也好,还喜欢上了画画,常常在纸上涂鸦。但是,他最终还是消失在了井里,这真是一件怪事。迷信的人只说可能风水不好;有人甚至说,很早以前就曾经在某个黎明看见有鬼魂攀附在井沿上,一晃就不见了……但这些说辞不过是安慰死者的家人,意思就是:一切出自天意,命该如此。
但从此这井就被废去不用。在此之前,人们还在井口汲水洗衣洗菜,现在已无人问津。听说可能还有人往里乱丢东西。
这让我感到非常的遗憾。所以,当我读到希内的这首诗:“去凝视泉水中的那喀索斯,他有双大眼睛。”简直就觉得这就是为我村那个死去的少年写的,他就是我们村的那喀索斯——希腊神话中爱上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死后变成水仙花的美男子。我特别想去他们家,拿这话去安慰他那上了年岁,已满头白发的双亲,但是,一怕勾起人家的伤心往事,二怕让人觉得我莫名其妙,所以我有几次都临时惴惴地退回来了。
或许村里人早就忘记了这个死去的孩子,可是我一直记住了,虽然我没有见过他。这也给我带来灵感,我写过几首以井为题的诗歌,其中一首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写的:
“大地围拥着我,泉流滴滴/在黑暗的深处枝叶怒放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