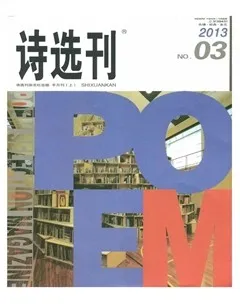直面虚无的修辞术
对于沉浸于内心生活的人来说,咖啡馆是一个情绪自由释放的避风塘。孙磊的《静穆》就选择在这样一个暧昧的表意空间展开。虽然没有刻意模仿咖啡馆舒缓流畅的背景音乐,但诗歌本身的节奏带有一种听觉上的沉静感。与耳感相应的,是咖啡馆内氤氲迷离的氛围。在视觉受限,触目可见沙发、杂志、烟等关涉个人情趣的私密空间里,适合个人情感的百转千回、恣意延展,既可唤醒内心深处隐秘的往事,也能突然导致情绪上“必然的颓唐”,甚至产生放纵自我的爱的“蛮劲”。但诗人马上意识到这一切显得多么奢侈,于是内心的激烈冲突由咖啡馆蔓延到外面的世界。与情绪的变化相应,咖啡馆内外区分出两个世界:上升的烟雾与下落的细雨,外面的炎热与屋内的清凉,构成结构上一种强烈的自反性张力,世界合唱的繁华与内心的独奏的萧索引发心弦的强烈波动。
如此的静穆就不是单向的。无论是画面还是旋律上的静穆都不能导向内心的平静,而是不断被内在情绪的紧张感所撕裂。静穆具有了某种形而上的意味,诗人一直在试图寻找,但却被各种各样的时代“杂音”所包围和分割。出于修辞上的考虑,这首诗并没有过多牵涉时代的喧嚣,也没有仅仅停留在对当下的解剖式开掘,而是让时代的噪音充当了精神幕布,在前台导入了不同的“文化资源”。不同时空“文化杂音”的强行进入,行文稍感突兀,阅读效果上却直接构成对静穆感的冲撞与挤压。即使诗人不以注释刻意标明,李白或者陆机,苏珊·桑塔格或者约翰·凯奇,这些并置于“静穆”周围的种种文化资源并不难于辨认。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来自不同文化场域和精神背景的,脱离具体历史语境的文化资源,已不再具有资源本身的承载力,由于当下现实语境的强大压力,它们只能铭刻在咖啡馆周围,呈现的是当下的文化变形记。
表面看,由“必然的颓唐”转向“处世若大梦”的理路是清晰的,但作为一个时代文化标本的李白,与孙磊诗歌的整体氛围有着内在的冲突。很难想象一个现代社会原子化的个人,在何种程度上与唐诗里的个人建构起深层次关联。在权力和市场的挤压之下,个人被强行整合进时代机器,精神处境虽然有了多重展开的可能,但“直彻心源”的生命意识早已被网络状的社会结构暗暗抽空。对于一个试图在更有效的层面和时代对话的知识分子来说,触手可及很难被确切表达得彻骨的清醒与沉痛。时代夹缝中的文化活力,被编织进各种政绩、表格、指标的时代图腾中,虚假的繁荣与内在的荒凉疯狂地滋长,与盛唐的精神气象相对应的生命意识并不存在。“长安市上酒家眠”的酒中仙在当下是不合时宜的,当酒被咖啡所取代,是更为清醒也更为隐痛,而不是“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的生命沉酣。古人在混沌hC/+YMx3v/BPKc+5+7GbItJeFPmIzsbo/GBYHqheFmE=中所展现的生命活力被冰冷与清醒的当下意识所击碎。
“风神超绝”、“离众绝致”的艺术魅影,在咖啡馆这个狭小私密的空间是被允许的。这种安全对于诗歌来说却是一种更为内在的危险。形式的探索与内在精神空间的隔绝,离众绝致有可能演变成咖啡馆打发闲适时光的调味剂,演变成精神下滑的另一种极端方式。在这样一个暧昧时空中,多大程度上能和传统展开有效对话交流都是未知数,更无法奢望重新转化和创生传统的可能。这并不是说引入传统是没有意义的。90年代以来,古典诗歌传统逐渐被诗人处理成进入当下的另一扇窗户。静穆感一度是古典美学的重要标志,它直接对应传统文人的准宗教体验的生命状态。静穆的美学意境建立在直彻心源的生命体验之上,采用的是禅宗离相无念的直觉思维。生命体验与艺术直觉融为一体,与整体直观的禅宗参证悟空过程互为参照。艺术灵感与生命体验的妙悟与迭度,实现了对日常生活的感性超越。这种超越是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亲证手段实现的,表面看是“雪中蕉正绿,火里莲亦长”的非逻辑性,实际是无理而妙的美学意境。
由于诗歌和历史关系的转变,具体到当下现实语境,这种审美方式是脱历史的。早在80年代“整体主义”的文化诗实验中,就出现过对于传统文化仪式上的向往。宋渠、宋炜的《家语》等诗,就以连绵悠长的语句,将诗歌导入一种恍惚混沌的境界,读者仿佛在梦境中感觉到文明的传承。诗人希望通过平静淡泊的意境,来化解现实中波澜激荡的心绪。把只可意会的审美感受发挥到极致的同时,艺术经验也渐渐远离了人间烟火。在凝神虚静中心领神会的禅悟,与当下现实语境的对接与融通是非常难的。面对严峻的现实,对于承担时代良知的诗人来说,清静自然、行卧自由的人生情趣显得非常奢侈。孙磊诗歌的资源并置,并没有导向这一审美感悟,而是经由网状的精神链接将传统空间置换,诡秘地展开了一条从过去空间通往当下的道路,同时也多少质疑了人们今天对传统的热切渴望。这是一种充满悖论的表述,诗歌构建了一个传统与当下互为阴影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一种虚无感与静穆的氛围相伴而生。
…………
在时代的喧哗与躁动中,静穆在很多时候意味着对静穆自身的否定。就连被阵阵不和谐的噪音所裹挟的咖啡馆的片刻宁静,都几乎是无法实现的。从街头到家中,从工地到工厂,从酒吧到网吧,只要深入体察,就会发现一种沉浸在时代喧嚣背后的不安和焦虑,这从普通民众时时显露出来的戾气中可见一斑。但对于诗歌艺术来说,试图以喧闹吼叫凸现自身价值仅仅是自欺欺人的艺术幻觉而已。对于时代夹缝中溢出的“不可推脱的恐惧”,诗歌的精神意义恰恰在于对恐惧的反驳和拒斥。在这一抗辩性结构中,静穆的姿态确实是一面能够照出生命本体的镜子。比如在大草原、沙漠、山谷上,万籁俱静的特定空间,人们往往会沉浸在静穆的感觉之中。诗人姜耕玉就为灵魂找到了这样一个对应的生存空间。诗人飘泊阿里,在高原群峰肃立的“白色的沉静”中,经由“拱卫绝顶升起的眩目之光”体验到了灵魂的超越和升华。类似《冈仁波齐·静穆》这样的诗歌,就是在表面价值观念多元,实际上精神迷乱与虚空的时代表象下,探索个人精神空间提升与超越的可能性。
孙磊选择了另外的诗歌方式。他的诗歌虽然有着内在的理想主义气质,但这种理想建基于对当下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精神虚无的洞察之上。在一路高歌猛进的现代化高速公路上,普通民众真实的生活境遇被各种形形色色的叙事不断删改和编纂,每一种叙事背后都是一种或宏大或微观的权力关系。只要稍微留意从各种叙事的缝隙流露出来的真实的侧影,就会发现当下生存境遇的严峻和精神的大面积溃败。比起精神的超脱和升华,孙磊更愿意直面那些直逼现实的精神困境,挽留住生活的尴尬和问题,而不肯轻飘飘地滑过去。如此而来的静穆或许就是诗人在《重申:建设性》中所说的“沉静”,是将“加速度定格或者放慢,让它在读者内心形成一个可以回旋的空间”,以更为理性和隐忍的方式进行艺术探险,从而“将活力变成良心、将自由转化成尊严的热情和魄力”。于是《静穆》中的咖啡馆只是提供了一个装饰性的场景,一个思考当下精神处境的契机。在这里真正的戏剧并没有上演,与记忆相关的“密语”也终究没有出现。诗人有意将这一场景与背后的多重精神幕布进行深层勾连,在沉静下来的情感模糊地带,才能发现真正的精神密码,因为精神变得过分清晰的时候,恰恰是精确的算计取代了复杂的情感。
让生活的镜头慢下来,让情绪沉淀下来,正是为了请出那个“绝对的虚无”。在“静穆”的出神状态下,“惭愧”的或许不应是作为见证者的诗人。在巨大的时代神话面前,如何把内心的剧烈冲突转化为诗歌的有效形式,是对每一个有良知的诗人的考验。我们面对的文化处境,是对于当下现实过渡膨胀的非真实书写,导致生命隐痛被猎奇和围观逐渐抽空,历史深度消散于消费时代的字里行间。这首诗中的“虚无”正是出现于层层时代叙事的围困之中,通过诗人修辞术的锤炼,将与“虚无”的种种对话转化为艺术的形式。这种静穆实际上是在时间、空间的多重秩序中引入了一种“不思”与“必思”的互动,以突然减速的方式处理时代的喧嚣和疯狂,在悖论中逐渐打开一条艰难但却更为有效的进入当下的诗歌通道。
或许,在一个无法安静的焦灼时代,对静穆与虚无的思索行为本身,就已经戳到了时代的痛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