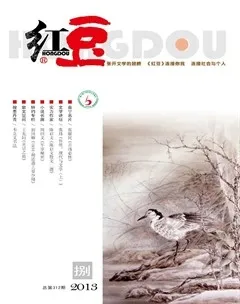从黑石关到砖砦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又叫“四清”,对于现在的青年人无疑是一个陌生字眼,然而它却是真实地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席卷神州大地、持续数年之久的一场政治风暴。运动期间中央最高领导亲自挂帅,数百万干部赶赴基层,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其目的是要在中国大地上彻底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在党内彻底杜绝滋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实际上却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与前奏。
1964年到1965年期间,我还是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先后两次参加“社教”,第一次属于“小四清”,地点是河南巩县的黑石关镇;第二次是“大四清”,地点是河南通许县的砖砦村。
作为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年轻人,充任“工作队员”下到农村,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也是新奇的。因为此前,除了寒暑假到外婆家的小村子住上几天,我的农村知识全都是在《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创业史》、《青松岭》、《艳阳天》这些小说、电影中获得的。两次社教的意外收获是让我获得一个零距离接触农村、认识农民的机会,并体验到我少见的乡土风光,甚至还学会一些农活。两次社教的恶果是,我被作为“一个小小的齿轮或螺丝钉”强制性安装到阶级斗争的庞大机器上随之运转,在我本来怯懦、善良的天性里注入过多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强化剂,并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认知模式与思维模式,直到若干年后还难以廓清。
日落时分,火车在黑石关站停靠下来,我背着行李走下火车,只见铁路两侧全是层层叠叠的黄色山峦(这之前我还从没有见过山)。回首望去,铁轨从山谷中蜿蜒伸向远方,在暮色苍茫中渐渐隐去。那在视野中消失的远方,便是我的来路,开封、河大、十二视庙街,都被隔在山的那边,天的那边。我的心突然苍凉起来,顿觉成了孤悬天外的游子。
差不多半个世纪前的那个初冬,是我第一次离家外出远门,那时我不足20岁,距离开封三百多里路。后来真正的远行,比如到南洋、到欧洲,也没有这次300里行程的外出那么伤情。
我被分配到“大北沟”村,与教古代文学的孙先方老师同住一个窑洞。那是一座破旧的老窑洞,上方已经开裂出几道缝隙,村民们说不打紧,这些裂缝已经存在几十年了。每到临睡前,我总还是有些担心,担心那些坚硬的黄土会突然掉下一块。孙先方老师那时三十来岁,高高的身量,瘦长的脸,长相有点像当时正在热映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里那位指导员。孙老师是位学者型的教师,正在协助李嘉言先生整理《全唐诗》,一有空闲,还要翻看带来的书,于政治斗争方面完全看不出有什么经验。
倒是同组的一位高年级同学张启瑞显得十分干练。他属于“调干生”,进校前已经参加革命工作多年,村子里几次召开动员大会,发动群众,都是由他主持。先是领唱《忆苦思甜歌》:“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山崖前,枯枝倒挂,电石灯发出幽幽的光线,启瑞同学披一件大衣,挥动着不断变换的手势,让我佩服极了。我想,当年刘少奇在安源,毛主席在延安一定也是这般风采!张同学能讲出一套一套的革命道理,而且富有煽动性。接着是喊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会场上渐渐充满阶级斗争的紧张气氛。
我虽然年龄小,但身份依然是“工作队员”,被村民视为政府派下的人,被尊敬地称作“老鲁哥”,不时向我反映生产队里的干部问题。我尽量对照文件精神动脑筋分析,却总也抓不住要领。一次要我到另一个村子向“片”上的领导汇报工作,“片长”是化学系的一位教师,双目炯炯有神,也披一件大衣,显得干练威严。我长这么大从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紧张得连话也说不囫囵。尽管“片长”一再安慰我不要紧张,我已经脸色苍白,几乎虚脱。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老师叫夏德明,是艺术系同学夏美莲的哥哥。多年后和夏德明老师谈起那次向他汇报工作的情景,他还笑得乐不可支。
豫西的巩县是一块风水宝地,北魏“石佛寺”的遗址在这里,唐朝大诗人杜甫的祖居在这里,宋代皇帝的陵寝在这里,清代唐百万的庄园在这里,民国的孝义兵工厂在这里,那时都无暇一顾。黑石关因为是公社所在地,所以来过多次。黑石关古称黑石渡,洛水渡口之一。关之两侧山峰对峙,一条窄窄的山路蜿蜒而下,地处险要,古时乃兵家必争之地。
那一天刮大风,我到公社邮局寄信。一天风沙漫天,黄昏时分风息了。返回的路上尘埃落定,一轮明月升起,我看到了一生再未看到过的奇景:皎洁的月光竟变成了淡绿色。虽是隆冬季节,月光却为远近的岗峦蒙上一层或深或浅的灰绿,山间的蜿蜒小路也被涂上晶莹的绿粉,山坡上晃动着暗绿色的人影,远处山村的窑洞已经到了掌灯时分,浑蒙的绿雾中闪现着点点幽光。这景象让我全然忘记了阶级斗争,沉浸到一个奇幻的神秘世界里。
黑石关的社教运动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给我留下太多记忆,只记得大雪天去到窑洞院的贫农孟大爷家,他家掺了红薯块的玉米糁粥香甜无比。还记得豫西山村姑娘们的质朴与热情。一天黄昏,黑妮、水仙几位大姑娘将我反关在生产队办公的屋子里,逼我唱歌。第二天我将此事汇报上去,领导为了防患未然,便把我调到另一条山沟里。
没过多久,巩县的这场“小四清”也就不了了之,工作队随即撤回学校。
接着,在通许县开展的为期近一年的“大四清”,形势就紧张多了,而我也在“严峻”的政治运动面前不断清除自己灵魂深处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逐渐“成熟”起来。
这一次,参加社教工作队的干部、教师、学生先是集中在通许县的一个大院里,“洗手”、“洗澡”,也就是钱钟书夫人杨绛先生所说的那类“洗澡”。在参加政治运动整治别人时,先将自己清洗一遍,先是自我检讨,接着是“背靠背揭发”,然后是大会批判。学生们大多比较单纯,容易过关。干部、教师就难多了,一个个要被泡上好几天,搓掉一层皮。听说一位女教师由于在办公室给一位男性干部缝过扣子,就再也洗不干净。
洗过“澡”后,人人轻装上阵,个个磨拳擦掌、斗志昂扬。我被分配在河南大学中文系自己的试点通许县四所楼公社的砖砦大队,带队领导是系总支副书记张书兰。我与陈信春老师、刘溶池老师、王梅英同学被派驻第五生产队。我与陈信春老师同住一间屋子。
陈信春老师出生于河南信阳地区一个贫寒农家,靠个人奋斗成为大学教师,并在民主德国洪堡大学东方语学系任教三年,此时刚刚回国不久。他表情严肃,说话严谨,逢事较真,处处透递出语言学家的教养,还多出几分德国学者理性主义的格调。一旦和他同住一室,又感到他其实是一个善良、正直、不乏幽默感的人。有一次当着我们大家的面,他掂起从家里带回的一只灰白色脸盆,砰地一声摔在地上,笑了笑说:没事,德国造,尼龙的!那时候,这种塑料脸盆在国内绝无仅有,让我们莫名惊诧、大开眼界。“文革”开始后,有人写大字报批陈老师“崇洋媚外”,这“德国造的尼龙脸盆”就成了罪证之一。记得那张大字报上我也是签了名的,在那个疯狂时代,我也曾鬼迷心窍地伤害过自己敬爱的老师。“文革”结束后,陈信春老师晋升教授,同时又升任抓科研、外事、出版等工作的副校长。作为教授,他始终热爱着自己的专业,写出了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作为副校长,他又是勤谨、认真、刚正、廉洁的。我举家迁往海南岛后,便和陈信春老师渐渐少了联系。不料,在海南竟又遇上了他的小女儿红波、儿子红雨。红波性情开朗,能歌善舞,河大历史系毕业,按辈分喊我师兄。红雨善饮,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多次一齐喝酒,他颇具乃父风范,能在自己喝得很清醒时把别人一一灌醉。
在砖砦的社教运动中,陈老师虽是农村出身,在他身上已经看不出有多少农民的味道,也没有感到他有多么出色的表现。
另一位老师刘溶池先生更年长一些,毕业于解放前的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硕士,诗人。搞运动似乎也非其所长,只是在揭批会上跟着大伙厉声嚷上几句,还不如学生干部王梅英敏锐干练。记得他很注意保养身体,早起的晨练从不间断。“文革”开始,刘老师一度成为批判对象,我曾揭发过他在社教时不肯下功夫与贫下中农搞“三同”,多吃了农户家的白面馍馍。现在看来,这都是些强词夺理的编排,那时却成了射向教授、学者们的一发发“炮弹”。
搞运动的能手是张书兰副书记。他本是从市里调进学校的专职政工干部,拥有政治头脑、斗争经验、工作方法,既能及时摸透上级的精神,又能认真联系下边的实际。他又很善于演讲,能够活学活用辩证法,时不时地会吐露出一些极富哲理的言谈。那时我对他的钦佩已达到崇拜的程度,回到住所后会赶忙把张书记的话语记到笔记本上。在张书记的英明领导下,砖砦大队的社教运动终于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查账摸底,背靠背揭发,大会造势,小会攻心,今天查出某生产队瞒产私分三百斤麦子,后天整出某队长私吞二十斤玉米,一些队长、会计被整得上吐下泻、苦不堪言。那时的砖砦村经过多年极左政策的折腾,上上下下都穷得很。我看到一位生产队长家的全部“存款”都小心翼翼地夹在一册小学课本里,五分的,一角的,两角的,最大的一张票子是五毛的。
在砖砦的社教运动中,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仿效者,全心全意投入到分配给自己的工作中,苦干加实干,在改造社会的同时也改造自身。
比如入村不久,我就帮一位贫农推磨,这是我只在小说里看到过,自己却从来没有干过的活计。刚吃下一肚子的红薯粉面条,肠胃正在泛酸,磨道里一连转了半个多时辰,十几斤麦子推下来肚子里已经翻江倒海,只觉得头昏脑胀,出了磨坊就呕吐一地。第二天得到领导表扬。村里的群众却有些不以为然,说那个贫农虽然“贫”,却不是个真正的“农”,以前是跟着个戏班跑江湖的,蓄意把工作队员当驴使唤。
运动的后期,为了实施“扎根串联”的需要,我搬进村里一户“赤贫”的家里。一位患有眼疾的五十多岁寡妇老大娘,带着四五个孩子,上面还有年迈体衰的公公、婆婆,家里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按照我们的阶级分析理论,这样的人家才是革命性最强、革命觉悟最高的。于是,我就住进他们家的柴房里,与他那十六岁的儿子一同睡在秸秆堆起的地铺上。不久就爬上一身的虱子。得闲时我就像鲁迅小说里刻画的阿Q那样,靠着墙,迎着阳光,扯开裤腰逮虱子,这在当时是很值得炫耀的事。据说,毛主席在延安时,当着外国记者的面也曾在裤腰里抓过虱子。
砖砦的社教运动尚未完全结束,“文化大革命”已经启动,我们重新回到学校。学校领导在大礼堂做“社教”工作总结报告,表扬了一批积极分子,其中就有我。记得当时颇为振奋,或许就在这振奋之际,我已经被诱导上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隆隆战车。
可悲的是那位从事政治运动的“行家里手”张书兰书记,自己在“文革”开始不久便成了政治运动整治的对象,受到严厉批斗、残酷折磨,一度“畏罪潜逃”、流亡他乡。“文革”结束后我每次回母校,打听起这位张书记的下落,竟无人能说得清楚。
“文革”中,我自己也经过一场血与火的洗礼。但从天性上讲,我不能说是一个勇猛的战士,有一件小事可以证明。
那时“四清”工作队队员每天的饭食是被派到农户家的,交钱和粮票,上门就餐。每家轮上三天、五天不等。被委派“管饭”的农户自然是政治可靠的贫下中农;能够被派上“管饭”,也是一种信任与荣光。有一天我被分派到村东头路北一家农户,男主人是个身条瘦长的汉子,女人手脚利索,早已经将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净整洁。饭桌已经摆到院子里,炒萝卜丝、溜南瓜片、玉米面糊糊、红薯面烙馍,外加一碟辣椒醋汁,夫妇俩恭恭敬敬地等着我的到来。他们家还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儿,穿了件粉红色小褂,长得清秀水灵,看到“工作队员”来自己家中吃饭,兴奋中显得有些慌张,套一句古代用语那就是“貌若惊鸿”。寒暄过后我已经落座,正要动筷子,生产队民兵排长突然跑来将我拉起来,说是搞错了,绝不能在这户人家吃饭,他家男人解放前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兵!我心中那根阶级斗争之弦顿时绷紧,赶忙起身撤离这户人家,连一声道别都没有。只瞥见躲在一旁的那个女孩儿,清澈的眼睛里已是泪光闪闪,满是卑怯、感伤、乞求而又无助、无望。
从黑石关到砖砦,那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多少红头文件,多少英明决策,多少会议演讲,多少豪言壮语已全然不再记得,至今留在我记忆中的,倒是黑石关那月色混濛的绿夜与砖砦村头那位女孩儿泪水晶莹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