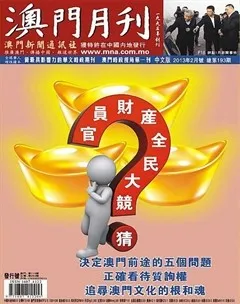反腐敗與權力制衡的制度設計
反腐敗應從權力制衡的制度設計入手。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共政治局的會議上談到“近年來我們黨內發生的嚴重違紀違法案件,性質非常惡劣,政治影響極壞,令人觸目驚心”。“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為什麼腐敗現象會越演越烈,以至有“亡黨亡國”之憂,而多年來反腐敗的努力,對遏制日益嚴重的腐敗收效甚微?究其原因,這既與既得利益的糾纏有關,也與制度設計的缺陷有關。
一、反腐敗的兩難:
反與不反的糾結
近年來流行一種說法:“不反腐亡黨,反腐亡國”。
前一句話好理解,從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到新任最高領導人習近平都承認,能否遏制腐敗,“關係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在一個國家,倘若腐敗現象愈演愈烈,執政黨最終將會失去民心,而不免被推翻。
後一句話需要解釋。有人說,“反腐不會亡國”。這是沒有理解上述說法的含義。在上述說法中,所謂“國”,不是指作為民族、地理和主權概念的“中國”,即便三歲小兒都知道中國不會滅亡,而是指党國體制的“國”,指一黨執政的國家政權。為什麼說,反腐敗會導致党國體制,即一黨執政的“國”消亡呢?因為按精英們的解釋,要徹底解決腐敗問題,離不開憲政改革,離不開民主選舉、三權分立和輿論監督。既然如此,那麼不難理解,如果採用這種憲政體制,這就意味著一黨執政的党國體制的消亡。
且不論上述說法有無道理,是對是錯,在上述說法中,“亡党亡國”其實是一個意思。其真實含義就是說:對於一黨執政的國家政權及其體制來說,反與不反的結果相同,即反亦亡,不反亦亡。可以說,這一說法反映了一些人心中兩難的疑慮和糾結。由此我們也許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多年來,反腐敗會被認為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二、反腐敗的嘗試:
不觸及體制的反腐敗
一直以來,當局試圖找到一種兩全之策,既不會動搖党的領導和現有體制,又能夠消除腐敗。為此有過各種嘗試。
(一)運動反腐。中共最駕輕就熟的就是搞政治運動。過去的整黨整風、三反五反、四清文革,無一不是運動。靠運動來反腐,雖然會有一時之效,但卻有諸多弊端。一是規模大了,有違文革結束後黨內“不搞政治運動”的共識,且有走文革回頭路之嫌,搞小了,沒有作用;二是有法不治眾的阻力,若全部清除,則國家癱瘓,若選擇性辦案,或特赦一部分,打擊一部分,則難以服眾,且有權鬥、清洗和厚此薄彼之嫌。多年來,每次新舊交替,外間總是紛紛猜測,作為顯示新政的“三把火”,會有“動真格”的反腐運動,然而這些猜測往往落空。究其原因,自然是問題棘手。
(二)增設反腐機構,今日中國可能是世界上反腐機構最多的國家。與反貪腐相關的機構有:紀委、檢察院、監察局、反貪局、廉政辦、預防腐敗局等。反腐機構越設越多,然而腐敗現象卻日益嚴重。可見,增加機構並沒有能遏制腐敗。有趣的是,近來又有人提出,反腐機構太多不好,應該減少才會有效率。他們沒有想過,原先是為了提高效率,才增設機構,如今機構增加了,如果還是沒能有效遏制腐敗發展的勢頭,那就說明,這種反腐機構的增減與反腐效率無關。
(三)實行民主評議制度。所謂民主評議,就是在幹部考核和升遷時,由組織部門出面,而由單位的下屬和同事評議此人的能力和品德。這種評議往往流於形式。一是礙於情面而和稀泥,“抬頭不見低頭見”,“日後還得相處”;二是牽涉利益糾葛和感情恩怨而不能實事求是,要麼互相吹捧,要麼互相詆毀。三是導致集體腐敗,利益均沾。大凡那些善於內部撒錢、集體分肥、照顧內部子弟者,通常會獲得好評。
(四)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早在1995年,當局就下發了《關於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收入申報的規定》的通知,然而這麼多年過去了,儘管民眾要求官員公開財產的呼聲不斷增大,但是,這項制度卻一直未見實施。究其原因,當然是由於這一制度的推進在上下各層級中均面臨巨大的阻力。其實,在現有體制下,這種申報制度,即便推行,也很可能會象各地上報糧食產量和GDP數據一樣,即不是“我有多少,報多少”,而是“先看別人報多少,我再決定報多少”。幾十年來,各地官員上報統計數字時有一個相沿成習的做法,就是指示秘書和下屬:“先去瞭解鄰近區鄉(地市)是如何報的,我們再定數字”。顯然,如果沒有有效的監督、核實和懲罰機制,這種財產申報制度只會流於形式。
(五)網絡反腐。在以往的年代裡,普通民眾要在媒體(如報刊雜誌和電視)上揭露身邊官員的貪污腐敗現象,幾乎是不可能的。互聯網和微博的興起,卻使這種在過去不可能發生的事情變成可能了。近來,網絡反腐頻頻使官員落馬,一些公職人員相繼因貪腐在網絡曝光而被立案調查或被免職。然而,由於網絡本身實際上仍受政府控制,因而網絡反腐所揭露的官員通常層級較低,難以涉及較高層級的官員。另外,由於網絡是一種輿論工具,它對傳統體制構成一種潛在的威脅。因而近來有一種聲音,主張對之加以限制。所以,作為輿論監督的一種方式,網絡反腐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其作用是有限的,或者說會受到限制的。
三、反腐敗收效甚微的原因:
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
為什麼多年來反腐敗的努力,對遏制日益嚴重的腐敗收效甚微?根本原因在於權力高度集中而缺乏制衡的舊體制。在這種體制下,從上到下,每一個地方的一把手都是權力高度集中,擁有對本地立法、司法、監督、傳媒和任何方面事務的領導權和干預權,這就是所謂的一元化領導。這種橫向聯繫的權力結構是一種“塊塊專政”的體制。按這一體制,每一個黨政首長在當地的權力實際上是無限的,其意志就等於法律,可以獨斷專行。不難理解,那些監督機構和地方媒體,作為被領導者,又如何監督他們的大權獨攬的領導者及其親朋故舊和圈子裡的人呢?
不僅僅是腐敗問題,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和“有法不依”等等國家法律在地方被“變通”、曲解和無視的現象,其實也與這種“塊塊專政”有關。那些日益增多的上訪人群和群體性事件,大多也與地方“土皇帝”們的“無法無天”有關。不難理解,當國家的法律條文與地方主管領導的意志相左時,地方執法者,由於其人事、工資和福利等關係屬?地方權力體系,自然是以地方頂頭上司的意志為優先考慮,至於國家的法律政策條文,則變得無關緊要了。
所以,在這種體制下,不論你增設多少反腐機構,不論你的“陽光法案”和“禁止以權謀私”等所謂制度訂得如何精細嚴密、聲色俱厲,不論你的法律條文如何咬文嚼字,甚至一字不漏地照搬西方國家的法律條文,都不免在“長官意志”和無限權力面前形同虛設和成為紙上談兵。
四、反腐敗的制度設計:
改塊為條,實現地方權力制衡
要消除上述體制弊端,應當採用權力分立和權力制衡。在當今世界,人們普遍認識到,實現權力分立和權力制衡的理想體制就是憲政體制。然而,前面我們提到,如果採用這種憲政體制,可能就意味著一党執政的現有體制的消亡。顯然,這是今日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死結。
筆者在《反腐敗與政治體制改革的另一選擇》一文中提出了一種思路:兼顧執政黨的利益和現代權力制衡的要求,改現有的“塊塊”體制為“條條”體制,形成一種傘狀結構:維持頂層權力結構不變,實現地方權力制衡。在頂層,仍是“党領導一切”,而自頂層以下,權力分立,改橫向體系為縱向體系。按這種新體制,監督機構被從包攬一切的地方權力體系中分離出來,不再從屬?地方當局,而是中央派出機構,垂直領導。其他權力制衡機構亦可酌情從地方權力體系中剝離出來。
這一方案並不是要否定、排斥或取代政治體制改革的終極目標和憲政體制的基本原則,而是在目前政治體制改革面臨瓶頸的情況下,與其舉步不前,不如另闢蹊徑,為解決人民最為關心的現實問題而採用的一種階段性、折衷性改革方案。其立意在於,將鐵板一塊的舊體制作分層處理,先易後難,先實現頂層以下的權力分立和權力制衡。至於憲政改革,當然仍可盡力推進。兩者並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