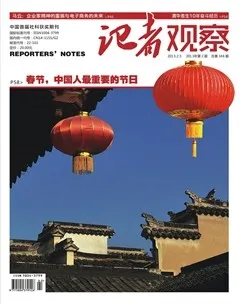微博政治:时尚的幻觉
德国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掌门人”尤尔根根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曾经有一个经典的论述:“有些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相抗衡。”
微博政治只能影响权力运作,而不能改变现实政治结构。这是一个有点残酷的宿命。事实上,“公共领域”里的意见表达,如果真要引发政治的裂变,根本就不能单打独斗。
当然,微博是社会现实的复制和投射,其“政治参与”游戏,隐喻着各国阶层结构和未来政治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未来更具广泛性和现实性政治参与的一个虚拟演练场。
按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研究,最开始的“公共领域”,是一帮欧洲贵族在沙龙里搞起来的。卢梭们那个时候经常出入这个夫人那个夫人的沙龙,对政府指指点点。凭借上流社会的贵族、文人们的社会影响力,他们的意见,间接地影响到现实的政治走向。
但这样的“公共领域”只是上流社会的人在玩,穷人与狗不得入内。其结果只是一部分人先“民主”了起来。对应于20世纪前欧洲“民主社会”的现实,就是根本没能做到普选。
中国今天的微博在理论上已经做到了让任何一个上网的人都可以参与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游戏。但其技术和生活方式的壁垒,还是把很多底层的人排除掉了,他们不懂,也没时间和雅兴玩这个。享受一下微博提供的“政治参与”,没有他们的份。
而即使中产、小资们啸聚于网络,在这个同时也是名利场、秀场的公共领域里,仍然看不出有多少“政治参与”的主体性,只有极少数的人通过自己提供的刺激性信息才能得到稍微有点影响力的关注,大多数人以“粉丝”的身份,作为无名大众淹没在“大V”们的意见表达中,构成“大V”们的群众基础,对“大V”的发言叫好或谩骂。
所以,看起来,在一个个公共事件及“大V”们的意见表达背后,关注度和粉丝数量构成了一个个粗鄙意义上的“政治压力集团”。然而,这样的“压力集团”仍然局限在抽象的“民意”范畴,以批评公共权力为预设,以明星崇拜为润滑,并不捅破“大V”们和底层,甚至和他们的粉丝具有不同的阶层利益和政治诉求。
正因为如此,“大V”们的意见表达,轻易就可以建立一个社会影响力、商业影响力、政治影响力的逻辑通道,使社会资本、商业资本、政治资本相互转化。微博的“政治参与”游戏,在实现对权力一定程度的监督和批评之余,也成全了“大V”们谋取自身利益的先验渴望。
媒体可以影响但永远无法变成实际的政治,真正的政治参与,是公民变成权利主体,而不是盘踞在虚拟空间的外在的批评者。任何人冷静下来想一下,在中国,微博的“政治参与”、“大V”们的“代言”如此发达,是很不正常的,它意味着在现实中,公民权利以及阶层结构仍在恶化。无论就政府还是公民而言,如果陶醉在“微博政治”这一时尚的幻觉中,忘记了从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参与上推进民主,将显得很不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