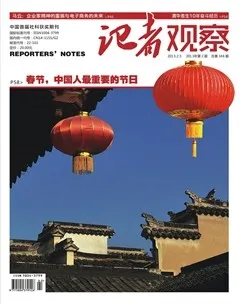公权力边界不清难以有效解决信任危机
迅速的现代化进程令中国社会正从“熟人社会”快速转向“陌生人社会”,而社会群体之间互不信任是转型社会的典型特征。怀疑已成为国人的生活方式,有人将之总结为“国民不相信运动”。这样一场运动是建基于国民的基本经验之上的,持续愈久,愈易固化为一种内在思维模式,一种“务实的生活智慧”:吃饭不相信食品的安全性,出行不相信铁路行业解决买票难的能力和诚意,上医院不相信医生没有给自己多开药,打官司不相信司法会保持公正……似乎只有不相信才是安全的。
在这样一种普遍社会信任危机之下,如何重构信任社会,是中国能否在经济发展成就显著、社会财富积累形成可观的“有形资产”的同时,遏制社会公信力“无形资产”的普遍流失,保护社会信任和社会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市场经济推动“陌生人社会”转型
自从有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有社会信任。信任其实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是社会共享的道德规范的产物。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信任建基于亲疏有别的熟人社会之上。
为何当前中国社会普遍缺失社会信任感和社会安全感呢?
自19世纪中晚期开始,在西方工业文明不可抗拒的冲击之下,中国遭遇“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意识形态长期以来的优越感被否定,一大批精英阶层开始进行反思,他们把罪责归咎于中国既有的价值体系及其所支持的社会结构,试图从西方寻求迅速“救国”与“强国”之路,并因此引发了一系列激进变革和革命,这对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
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的启动,更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急剧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引入一方面给社会增加了活力,另一方面也使社会充满了不确定性。传统血缘家族体系所能够提供的社会信任感和社会安全感在城乡地区都普遍处于衰退过程中。而中国迅猛的城市化进程,将大量农村人口和土地进行分离,促使他们进入城市工作;并且,原有中小城市人口的相当部分也在迅速向大城市集中。与此同时,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度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被瓦解,与城市社会个体相对应的往往是由“丛林法则”进行主导的市场,而不是曾经包办生老病死的单位。由此,“熟人社会”在政治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共同推动下,迅速转型为“陌生人社会”。
市场经济本身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市场经济信奉“丛林法则”,这将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并且资本的唯一本性就是攫取利润,不会考虑社会效应;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以社会信任为基础的契约经济,它必须建立在法治之上。如果缺乏法制的约束,市场的自发性必然会导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择手段,也会造成社会差距的拉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必须规范市场。市场可以有自发的市场,也应该有受规制约束的市场。自发的市场往往容易丧失道德、丧失诚信,造成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而受规制约束的市场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法律途径来制约这些行为或现象。
传统的中国文化本就缺乏法治精神,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急速地引进市场经济,但相应的法治建设并未跟上。现在中国每年都有好几起全国性的食品药品安全事故,而且“无良奸商”似乎越压越起,防不胜防。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商业欺诈、信用欺诈、就业陷阱和传销组织,使得人们对于现有的市场怯制环境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感。
公权力对社会保护缺位
一般而言,在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进行平衡的过程中,国家公权力应当通过法律制度对社会和市场二者分别进行规制,通过提供公共服务等对社会进行保护,这是弥补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本身所存在缺陷的重要路径。但在现今中国社会,由于对于公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制度,公权力的错位、缺位极其严重。
近年来,围绕着“国进民退”“国企垄断”“与民争利”等说法,引发了部分学者批评“权贵资本主义抬头”的趋势,进而升级为事关中国是改革还是倒退的体制之争。目前,虽然民营企业吸纳了大部分就业,但是在市场竞争中却由于起点低,再加上复杂的体制因素,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种种利益博弈等,易处于弱势地位;国有企业在重要的基础性行业占据主导地位,一方面和公权力捆绑在一起,另一方面拥有大量资源甚至垄断性资源,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占据天然的优势。这样两种完全不对等的待遇,使得人们对现有市场竞争环境的公平性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感。
同时,市场竞争与不完全竞争并存。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动力,但是,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表象上强调个人自由,却容易导致少数强者战胜多数弱者,进而垄断市场。而在中国,体制内与体制外差异、城乡二元制结构、行业差距与地区差距等导致市场机制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经济活动实质上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再加上收人分配不平等与财富逆向转移共生等现象,这些都有悖于对社会公平和人人平等的基本理解,这就使得人们对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难以接受,对现有社会竞争机制的公正性产生不信任感。
此外,在通过公权力强力推进市场经济的同时,国家自身也变为经济发展的“运动员”,在片面追求“有形资产”积累的同时,却忽视了制度建设和社会管理,甚至将毛泽东时代原本由政府或者单位提供的公共产品大部分委托给市场,由个人或者家庭进行购买。而由于财政体制和“GDP2政治锦标赛等原因,政府治理尤其是地方治理存在相当程度的权力滥用、权力寻租和非法行政的情形,使得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大为降低。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在这种市场力量和非市场力量冲击社会,国家公权力对社会保护缺位甚至联合资本进行中国式“圈地运动”的情况下,民众对政府产生了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各种群体性事件在全国各地被激发出来。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央政府为了维持其执政正当性,自上而下地推进社会改革。然而近些年的相关社会改革并没有实质性地解决上述问题,致使这场“国民不相信运动”不断摧毁我们的道德底线。
在这样一场信任危机之中,政府的责任在哪里?我们认为要从以下几点理清思路:
首先,要建立对法律的信任。在熟人社会中,人们彼此交往主要是靠信用取得彼此的信任,而不是靠契约。这虽然是中国传统的美德,但道德约束主要靠的是自律,契约却是法制性的,没有法制进行约束,那就失去监督的机制,而没有监督的信用并不可靠。如果说在一个熟人社会,彼此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进行小额的交易尚能维持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进行跨地区、跨国的贸易,在陌生人的世界中交易,根本无以为继。在宗族社会中,家庭是家长统治下的财产共有制,这种秩序养成个人缺失产权观念,许多民众至今都不知道怎样维权。由于法制观念薄弱,致使中国古代有高额的商业资本,却没有经济法。是自律还是他律,这是礼治与法治对社会管理的根本差别。中国要从前现代的小农社会向现代化过渡,必须要有相应的法制建设,要厉行法制就必须充分认识“礼治秩序”所造成的习惯势力,对执法可能发生的障碍,并采取应变的对策。
其次,划定公权力的边界。无论对市场还是对非政府组织,政府都应当依据法律规范对其进行监管,而不是直接管理。像英国这样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上百年之后才通过政府监管来弥补市场失灵。而中国是在市场发育尚不完全、法治尚未健全的时候就启动政府监管。市场本应当承担的责任,例如婴幼儿奶粉案等食品安全事件,由单纯的企业制假售假行为,升级为中国乳制品行业的危机,并且波及到政府监管部门的信誉,最后会被归咎于“政府隐瞒”和“体制问题”。从非营利部门角度而言,其存在的正当性来源于其公众形象,对非营利部门的公众信任是维系其组织生存和公民社会力量的基础。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本是慈善组织自身的问题,也因为中国红十字会与政府有关部门理不清的瓜葛,被批评为“首要责任在政府”。
政府部门将所有的监管权集中于一身,其实也是将责任集中于一身。出了问题,自然是千夫所指。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才是最为智慧的责任边界。
再次,建立对公权力的监督与约束机制,遏制官员寻租。中国的体制具有很大的“唯上不唯下”的特点,而“唯上不唯下”的必然结果就是“欺上瞒下”。应当建立常规的、制度化的利益表达管道,让各种社会力量的利益诉求在法治的轨道内得以规范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