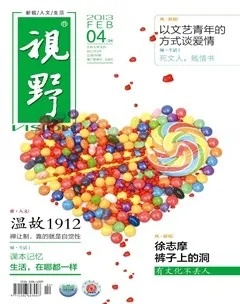那时爱情那时书
20世纪80年代高校间流传一个顺口溜:苦清华,乐北大,要谈恋爱到师大。清华当时是纯理工院校,学生学业繁重;北大人自带一股天之骄子的自信,所以老乐呵呵的;师大呢,恋爱之风盛行。
也真是。刚入学没俩月,光我们班迅速有三四对同学建立恋爱关系。毕业之后,全班120个人,不出本班有30人结成15对夫妻。我们毕业时,学校还管分配工作,可忙坏了那些成双成对的幸福人儿。分配原则是哪儿来回哪儿去,可结对儿时,不会专挑老乡啊,就得往同一个城市调配。
那时的爱情,不如今天年轻人谈得这般奔放,绝大多数都主打羞涩牌。有对恋人,因为女生太腻,经常没骨头似的吊在男生肩膀上,还引起不少非议。既羞涩,就要扯一块遮羞布,这块布就是读书。
那时生活简单,没网吧,没酒吧,更没夜店,街上连小饭馆都没几家,就算有,也不是穷学生惦记的,就没这风气。那时所谓谈恋爱,一定离不开读书。常见模式是:一大早起,俩人各挎着书包,饭厅碰头。吃完早餐奔教室,并肩坐在一起度过上午四节课。中午一起吃完饭,各自回寝室休息。下午在教室碰头,继续肩并肩度过两三节课。晚饭一起吃,吃完再奔教室,肩并肩地上自习。教室灭灯前,各回各宿舍,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当然不是所有同学都有幸找到意中人,孤男寡女们就把浓浓的荷尔蒙发泄到读书这事儿上。
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好学生,他们任何时候都独来独往,奉课本和考试为神,努力创造好成绩,以抵消青春期的孤独。当然,这么说,和他们立志学业、志在千里并不矛盾,一件事不同角度去看而已。另一种情况是一群自命不凡的家伙,他们最不喜欢上课,但天天逃课躲在宿舍或是图书馆,博览群书,而且专挑犄角旮旯的偏门书读,以求最广阔的视界。下次再有辩论时,他们口沫横飞,不把你侃晕绝不罢休。要说那时的所谓偏门书,也不是今天这个概念。今天资讯发达,哪有什么书想找找不到的,书店没有当当有,当当再没有,还有淘宝垫底儿。而那时所谓偏僻书,就是《梦的解析》之类的大俗书。
说到偏僻书,想起同寝室的一位江西籍同学,英文很好,他对我们把新批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这类书当成偏僻学问大读特读颇不以为然,讽刺我们傻乎乎尽拾人牙慧。我们请教他:依你看,该读何书呢?他嘴角一撇,很神秘地说:说了你们也看不懂,真能称得上偏僻的,当然是那些禁书啦,别指望会出中文版。多年之后,我在书店看到《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译本,顿时想到这位江西籍老兄,大概前后有半年时间,每晚手捧此书的原版,看得啧啧称奇。我们让他讲讲,他一个字没透露过。
那时买书真是问题,购书渠道只有书店一处,书店一缺货,就没着没落。不过后来我发现了一个办法,能将偏僻书据为己有。师大图书馆在全国图书馆系统算非常强悍的,藏书量和种类都名列前茅。图书馆有项规定:如果借阅的图书丢失,按原书价三倍赔偿。我有一阵四处想买法国作家罗布·格里耶的一本小说,因是几年前所出,书店早已下架。我在图书馆找到借出,然后借口丢失,赔了两块多钱,了了一桩心愿。
周末,恋人们纷纷打扮得漂漂亮亮,奔赴北太平庄、西单等处逛街,单身汉们会选择骑着车,把全北京的小书店逛个遍,不定在哪家旧书店,就能淘到一本心爱的书籍,拿在手中摩挲,那感觉不亚于面对美妙恋人。
(李冬月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东榔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