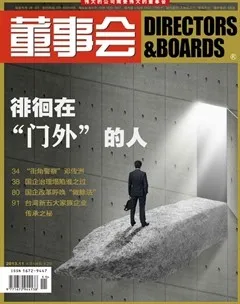开放体系:治理创新的支撑
“户枢不蠹、流水不腐”,这个古老的智慧告诉我们,唯有流动、开放才能保持活力,避免衰败。小到人的机体,大到国家社会,莫不如此。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始终踯躅不前,追溯缘由,就是我们的制度建设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下完成的——民间智慧无法有效传递给上层,而参与决策的人群往往被既得利益和“自上而下”的思维所固化。在企业的公司治理方面,“形似而神不似”的论断早已不新鲜,但始终没有一个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市场监管层先后出台的一些强化董事会独立性的办法也如同隔靴搔痒。难道真的是“无计可施”吗?非也,我们不但搞错了创新的源头,还创造了一个封闭的制度创新体系,这个体系对来自底层的声音置若罔闻。
创新的源头是大量、分散的市场参与者,而不是产生于社会的精英阶层,更不能从西方国家直接借鉴而来。没有一个现成、完美的治理模式可以借鉴。一种制度的好坏,需要由市场参与者来反复试错、检验;创新也是如此,只有适应本土市场和制度环境的方向才能成为推动变革的共识。两个看似相同的市场,在具体的治理准则上可能存在很大差别。例如,香港上市制度以股东为中心,坚守“同股同权”的治理原则,实质反映的是香港民众对资本的态度,在一个政治制度不独立,但经济又极其开放的市场中,这一理念几乎是整个市场的基石;反观美国,科技型企业可以选择双层股权结构上市,例如脸谱(Facebook)公司的上市,监管制度允许这一类公司的治理结构偏向“创始人”,无疑反映出美国资本市场对创业者及其创新精神的推崇。当然,这种推崇是有条件的,企业必须是“干净”的,自由创新的背后一定有一套严苛而完善的法律监管体系,否则上市后的企业就将沦为内部人控制的圈钱机器。在严刑峻法下的自由和创新,是美国市场选择的结果。
任何创新都离不开其所滋生的土壤和环境。生态环境本身是否具有开放性,又将决定创新是否成功。在目前投机气氛浓烈、投资机构普遍急功近利的市场环境下,资本市场需要什么样的治理创新,该如何变革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方式,才能使之对董事会决策和监督机制形成有效的影响?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其实是不知道的,只有在市场上摸爬滚打的企业最清楚。问题是,这些“民间智慧”能否通过一个畅通的渠道变成决策层的重要参考。
在马云看来,阿里在哪里上市并不重要,他更关心上市所在地的制度环境和监管理念。阿里需要一个能够支撑其长期发展的治理机制和监管体系。其实,阿里上市地最终是选择在中国香港还是美国资本市场,这个事情本身并不能成为评判两个市场开放水平高低的标准。港交所对合伙人制度的“不接纳”也许是市场选择的结果,美国纽约交易所及纳斯达克两大交易所的欢迎和任何姿态,也许是因为阿里的商业模式与美国的市场理念高度吻合。但无论如何,我们从这个事件中看到了开放体系对于创新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