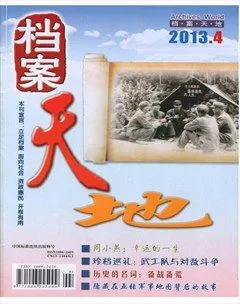幸运的一生
编者按:
周小燕,我国屈指可数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和声乐教育家,以“中国之莺”美誉驰名海内外。周小燕,1917年出生于上海,1939年赴法国巴黎俄罗斯音乐学院学习。1946年后在欧洲演出。新中国成立后,任职上海音乐学院。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50多年来,周小燕教授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祖国培养了像鞠秀芳、罗魏、魏松、高曼华、刘捷、张建一、顾欣、万山红、廖昌永等一批又一批高质量的专业声乐人才。1980年、1984年,周小燕先后两次被授予“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光荣称号;1989年,国家教委向她颁发了“声乐艺术教学优秀成果国家级特等奖”;1991年,成为第一批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高级专家。
我家的“儿童歌舞团”
鸿兴坊是近代上海石库门建筑的一个代表,在上海虹口区。1917年8月28日,我就出生在这里。那时候,我爸爸周苍柏是上海商业储备银行的职员,母亲董燕梁是大家闺秀,成家后,在父亲的支持下,学会了弹钢琴、拉小提琴,显示了良好的艺术天赋。在我不到一岁的时候,父亲调到了上海银行汉口分行,我们也随之来到了汉口。
我小的时候,非常顽皮,像个男孩。我对艺术好像也有一种悟性。在幼稚园里,老师教唱歌和跳舞,第一个学会或者学的最好的总是我。回到家里,有客人来了,爸爸让我表演一个,我也总是大大方方地又唱又跳,一点儿不怯场。爸爸从事的虽然是金融业,但是对音乐喜欢的不得了。有一次,他路过一家琴行,买了一把曼陀铃回来,我看到后非常喜欢,不久也学会了。后来,爸爸带着我和两个弟弟又来到这家琴行,看着满屋子的乐器,我和弟弟们高兴极了。爸爸聘请琴行老板白俄罗斯人舍夫索夫教我弹琴。
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有声电影出现了。这对于我们家这些喜欢艺术的孩子来说,实在是件大好的事情。电影一放映,我们就买到了电影里面插曲的唱片,很快我们就会唱了。后来我们又觉着光演不过瘾,我就带头在母亲的卧室里,先关起门来,把床当舞台,床单之类的往身上一披,就成了戏服,在上面唱啊跳啊,不亦乐乎。一天,来家里玩的四姨妈听到我母亲的房间里怎么这么热闹,过去一看,把她逗乐了。父亲母亲知道后,不但没说我们,反倒有些埋怨我们为什么要关起门来演?我一听就更来劲了,把“剧场”从卧室搬到了客厅。从此,我们被称为周家的儿童歌舞团,我们的演出也成为了惯例。
日子,在我们快乐的唱唱跳跳中过去。我13岁那年,扁桃腺发炎,被迫住院开刀。手术后发现,我原来的哑嗓子,竟然变得圆润、爽亮起来,高音也能唱出来了。一天,家里来了位上海的朋友,他看了我们的演出后对我父亲说:这小姑娘嗓音这么好听,为什么不送她到上海学习唱歌呢?这就样,我告别了少年时代,告别了儿童歌舞团,1935年,18岁的我随母亲回到出生地,报考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
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是中国成立最早的高等专业音乐学府。在我报考之前,学生中就有冼星海、贺渌汀、刘雪庵等人。我那期共招收了46名学生,我主修的是钢琴。没成想,好景不长,两年后的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武汉成了全国的抗日中心。我放假回家后,参加了好友在武汉和汉口组织的两支歌咏队,投入到抗日宣传中去。工厂、学校、车站、医院、街头,到处都有我们合唱团的身影,《义勇军进行曲》、《在太行山上》、《毕业歌》、《游击队歌》等歌曲响彻四方,武汉合唱团成了全国孕育和推广抗日歌曲的重要之地。刘雪庵,中国近代最著名的作曲家。那时,他为正在筹拍的电影《关山万里》谱写了抗日歌曲《长城谣》。刘雪庵拿着谱子找我,让我演唱。我们武汉合唱团不断发展壮大,影响越来越大。有人建议,我们应该唱到国外去,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和支持。有一个叫陈炳文的人对此事非常热心,他四处奔走,最后联系好去美国演出。我听后自然很高兴,但却遭到了父亲的反对。父亲的意思是我可以到美国去,但不是现在。因为在艺术上我还是个小孩子,懂得不多,眼下最好是下决心多学习,成为真正的艺术家,那时再去也不晚。其实,父亲有着他更深远的考虑,他想让我去意大利,那里是美声唱法的发源地,那是多少音乐人向往的地方啊。父亲还说抗战总会结束,日本人早晚会滚回去,那时候国家要建设,各方面都需要人才。你学成回来后,踏踏实实为国家做点事情。就在我正要出发的时候,传来了意大利出兵埃塞俄比亚的消息,父亲非常生气,当即决定不让我去法西斯国家留学,后来决定把我和弟弟送到法国巴黎学习,因为那时的法国是欧洲乃至世界的艺术中心。
欧洲飞起来“中国之莺”
去法国之前,当然想的很好,甚至是想入非非。想象着巴黎那个大铁塔怎么怎么漂亮,还有那个卢浮宫,也会是光彩照人。当然,这一切的印象都是在资料里看到的。我到巴黎的时候,大概是是七八月份了,所有的巴黎人都去避暑了,巴黎城几乎没有什么人,房子和天空一样,都是灰色的,埃菲尔铁塔像个破铁架子,特别的萧瑟,整个城市空荡荡的。我想,这就是巴黎啊!好在有中国大使馆的帮助,我和弟弟暂且找了一个住处安置下来。后来,在俄罗斯作曲家齐尔品先生的帮助下,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当时我们姐弟还没有找到学校,齐尔品夫妇认为报考巴黎音乐师范学院比较合适,于是,他们就带我们去报名,给我们辅导补课。考试那天,齐尔品还陪着我们到学校,我演唱的是歌剧《蝴蝶夫人》中的咏叹调《晴朗的一天》。那时,巴黎音乐师范学院,中国学生非常少,一位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姑娘将普契尼的名曲演唱的如此有滋有味,立刻在学校传开了,引起了学生们的好奇。我就这样考上了,入学后,同学们都叫我“小蝴蝶”。但是不久,我在主修课声乐方面又出现了问题,高音上不去,一唱就破,主课老师也没有好办法。我非常着急,夜夜睡不好,一下子瘦了许多。齐尔品老师向我介绍了巴黎的俄罗斯音乐学院的一位意大利老师贝纳尔迪。贝纳尔迪出人意料地只是让我唱几首简单的意大利歌曲,一遍又一遍。后来又赶上战乱,很长时间没怎么练过嗓子。再次见到贝纳尔迪老师的时候,老师拿了一本歌谱,说让我试试这个。我一看,吃了一惊,是经典歌剧《弄臣》中的咏叹调《亲爱的名字》。在老师的鼓励下,我走到钢琴旁轻声哼唱,唱着唱着,感觉嗓子很通畅、很舒服,不由得放开了声音。一首难度极高的咏叹调,居然被我唱下来了。我明白了,老师是在用如同我们中医调理的方法,来治疗我受伤的嗓子,同时,科学地训练我准确的发声方法。此后,贝纳尔迪加快了对我的教学进程,为我造就了一个音色清脆、声音灵巧、上下贯通的花腔女高音嗓子。后来在齐尔品的介绍下,我又认识了法国著名歌唱家佩鲁嘉夫人。在她的指导和培养下,我不仅学会了许多法国艺术歌曲,更为重要的是能准确地诠释这些作品的内涵和风格。
战争结束后,我也频繁出现在巴黎乃至欧洲各国的舞台上,每一场演出都给欧洲人带来了莫大的惊喜。特别是在德国柏林的音乐会后,德国报纸写到:“‘中国的黄莺’歌唱德国舒伯特的情趣,花腔技术高超。”从此,我身上就有了“中国之莺”的称呼。也就在这时,我也收到了千里之外的家书,我想我已经学成了,该回国为国家效劳了。我马上买好了船票,在大家的惋惜声中,踏上了归程。
从黑夜唱到黎明
我虽然归心似箭,但回家的路并不平坦。那时,巴黎还没有直达中国的邮轮,我从巴黎乘火车到了荷兰阿姆斯特丹,想从那里坐船到上海。但是,邮轮走走停停,到了新加坡后就不再往前走了。我只好从那里下船,在新加坡停留了几天,又买的去泰国的飞机票,从泰国飞到香港。到了香港之后,又等了几天,买到了飞上海的机票。这一路,竟然走了两个月。
回国之后,又是一系列的专场演出,邀请我去演唱的地方越来越多,几乎都应接不暇了。有一天,交通大学学生会的同学们来登门拜访,他们希望我能去交大举办一场独唱音乐会,甚至说可以付点酬金,我说演出肯定去,但我是义务的,钱不会收。演出那天,交大师生都到礼堂看演出,大礼堂爆满了。学生会的同学想了个办法,把喇叭接到操场,让大家席地欣赏。演出结束,同学们纷纷起立鼓掌,学生代表手持一面锦旗,走上台献给我,上面写着一行大字:“唱破这阴湿的天——国立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敬赠。”
我在交大演出的消息,很快在上海高校传开了,各校都来请我去演出。圣约翰大学特意为我的演唱会印制了一份节目单,上面有这样一句话:它与旧音乐不同,主要不是形式上,而是思想系统上,它接近大众,唱出大众心底的呼声。新中国的音乐,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四万万颗心的事。
复旦大学的学生歌咏活动,当时在上海很活跃。歌咏队队长是司徒汉,那时他是新闻系的学生,后来担任上海乐团团长,成为中国著名的指挥家。复旦歌咏队由司徒汉指挥的《黄河大合唱》巡演于各个高校,深受学生的喜欢。我到复旦大学演出那天,前半场是我的独唱,后半场是学生们的大合唱《祖国大合唱》。演出结束后,学生们送我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从黑夜歌唱到黎明!”我很激动,把这面锦旗和交大送的那面锦旗挂在家里的客厅中。真是应了锦旗上的话,没多久,上海解放了!
为人民歌唱
上海解放了!兴奋和激动的心情还没平静下来,我就收到了一份会议通知书。回国两年了,我收到的邀请都是演唱会的,去开会的还是头一次。到了会场才惊讶地发现,参加会的有郭沫若、巴金、梅兰芳等大家、名家。会议由夏衍主持,他告诉大家: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将在北京举行,今天的会就是为这次大会做准备的,在座的都是将要出席会议的上海代表。首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于1949年7月2日在北京开幕,上海的大部分代表都是一块儿坐火车去的。记得那天在火车上,一位个子不高、和蔼可亲的大姐姐对我关怀备至,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是有“东方第一老太”之称的著名电影演员吴茵。那时候从上海到北京需要几十个小时,但大家一点儿都不觉得累。我记得赵丹最活跃,笑话不断。会议期间,我看到有些代表拿着会议发的一个小本本,请这个签名,请那个人题字。我觉着很有意思,也学着拿着小本本请人签名、题字。周恩来的题词是:“为建设人民音乐而努力!”郭沫若的题词是:“为人民服务!”茅盾的题词是:“为人民服务者,拜人民为老师!”田汉的题词是:“唱出人民的声音!”我当时就想,怎么都有“人民”这两个字,这是我参加这次大会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后来我慢慢明白了,我要为人民唱歌,为人民唱歌,这是我终生努力的方向。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来到了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慰问最可爱的人;我站在安徽治淮工地上,顶着寒风为工人演唱;我走访山东革命老区,将歌声献给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巨大牺牲的纯朴农民;我还来到上海的农村、工厂、广场、公园、学校演唱。
就像著名作曲家、钢琴家、音乐教育家丁善德先生说的那样:50年代是周小燕作为歌唱家的黄金年代,她演出频繁,深受欢迎。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几年里,我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代表中国出访,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心声唱到世界上去。再难以计数的出访中,1954年出访苏联很值得纪念。这次出访,阵容非常强大,代表团是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钱俊瑞,团员有张光年、黄佐临、柯仲平等人。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大剧院有一场演出,原定的节目是中国的一些戏曲,如京剧、川剧、汉剧等,没有我的演出。但是,演出的前天,代表团访问莫斯科音乐协会时,我应邀演唱了一首阿拉比耶夫的《夜莺》。这下,莫斯科音乐节传开了:中国代表团里有一位花腔女高音,能唱意大利、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的歌曲。于是,他们强烈要求中国文化代表团在莫斯科大剧院的演出要有我的演唱。这个晚上,我的歌声打动了观众,掌声经久不息。后来,我又被邀请到了莫斯科电台,录制了好几首歌曲,其中包括中国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歌剧《白毛女》选段。
大海给我送来了恋人
1951年9月,是我第一次代表新中国出访。我受命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和缅甸。因为是第一次,所以中央很重视,全体出访人员临行前集中在北京学习相关政策。这个代表团还有吴冷西、吴作人、季羡林、钱伟长、冯友兰、刘白羽、张骏祥、陈翰笙等文化科技界人士。这次出访,有几篇发言要用英文讲,我、张骏祥、陈翰笙、季羡林四个英文好,就由我们负责英文发言稿。一天,张骏祥来找我,商量对英文稿的意见。过了几天,他又来了,还是让我再看看稿子。随后,张骏祥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来北京?要不要一起去北海、颐和园转转?我心想这个人是北京电影界的,电影界很乱,人很花心的,我跟他没有交往过,跟一个陌生人出去乱跑,给人家看见影响不好。于是,我拒绝了他。出发前路过广州,我们到岭南大学去玩。岭南大学非常漂亮,像个大花园。张骏祥摄影技术好,他给大家拍了很多照片,也给我拍了。在一棵大树下,他为我拍完后跟我说:这个景好,我也坐到那个地方,你给我也拍一张。我拿起相机对准了他,忽然发现这个男的长得不错,挺帅的,自己原来竟然没有好好看过他。
张骏祥,出生于1910年12月,江苏镇江人,比我大七岁。张骏祥六岁时,全家迁往北京,早年就读于北师大附中,1927年考入北师大,一年后转学清华大学外国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35年,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留美专业中,有一个“戏剧专业”的名额,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当时已是外语系秘书的张骏祥,决定去试一试。据说,与他同去考的还有一名清华学生万家宝,也就是曹禺。曹禺比张骏祥晚几届,此时已发表了《雷雨》等著名作品。谁知考试的结果是幸运之神落在了张骏祥身上。1936年,张骏祥赴美国耶鲁大学就读。三年后,他获得戏剧专业硕士学位后回国。
长达一个月的海上之旅开始了。我开始注意观察他,发现这个人朴实、幽默,为大家服务,忙得汗流浃背,也不会表现自己。我认为这个人是一个“实而不华”的人,有文化,有水平,品德好,人长得又帅,我心动了。到了印度以后,我俩自然而然地经常走在一起,并且合影留念。在美丽的泰姬玛哈陵,张骏祥向我表白了心意,我答应了他。
当时随同我们一起出访的画家吴作人后来还画了一幅《双象图》送给我们。画面上,公象伸长了鼻子,目不斜视,显得严肃老成;母象美丽活泼,鼻子卷着,尾巴翘着,一只脚抬着,似乎在欢快地踩着舞步,俏皮又大方。熟悉我们俩的人一看画就乐了,画家把我们的性格完全表达出来了。
回到上海,我向父母说了这件事情,他们很赞同,很高兴。有一天,我的好友把我拉到她的房间,指着桌上一张白杨的照片说:他和白杨结过婚,已不是初恋了。我想,初恋或不是初恋,有什么关系?初恋往往是冲动的、浪漫的,不切实际不符合现实的。相反,有过失败的初恋,他会更加珍惜当前的爱情。关键是这个人品质要好。
1952年5月5日,我和张骏祥拍了张结婚照,在我舅舅董方中家办了一桌酒席,请了男方的证婚人夏衍,还有我这方的证婚人贺渌汀,还有我舅舅的好友潘汉年夫妇,我的姑妈周莘柏夫妇等十多位亲朋好友。当时我的父母在武汉,他的父母在镇江,都没能来参加。
婚后,我们在张骏祥的宿舍住了一段时间,随后搬进了复兴西路44号弄一套公寓楼的二楼,这里原来住的是著名编剧陈白尘。在这里,留下了我们的温馨和幸福,直到1996年张骏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