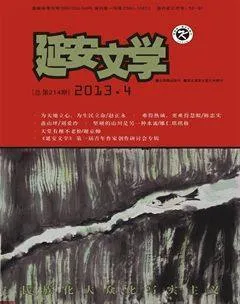母爱如莲
张晓润,陕西定边人,陕西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诗选刊》《诗歌月刊》《中国诗歌》等刊。诗作入选多种选本。
年届不惑,被青春期的孩子搞得晕头转向时,才体会到了做母亲的真正的辛苦,才开始重新认识母亲这两个字的含义,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母亲,此时,母亲已是七十整岁。这个七十的数字于我,似乎是个惊诧,因为在我的眼里,这个数字离母亲离我尚很遥远。
重新认识母亲的年龄,是从母亲的头发开始。七十岁之前的母亲,满头已是花发,但她在我们眼里,在周围人的眼里,一直是个乐观而新潮的老太。我们一直绕过她的白发而径直带她走进染烫中心,直到某一天,母亲的眼睛因为药水的缘故开始模糊甚至流泪,我和姐姐才如梦方醒,这才知道我们的母亲果真是老了。接下来再次认识母亲的衰老,是多日后她露出豁豁的牙笑迎我。这一次我抱住她,心疼的感觉那么烈,泪不可抑制地掉下来。她说加速她“衰老”的原因,是她用她的虫吃牙为她的三胞胎重孙子每人启了一次瓶盖。这几个瓶盖,让她的某颗牙提前下岗,也就是这颗提前下岗的牙,彻底让我的母亲准确而不留余地进入到了她真正的老年。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伤感的泪从我的眼眶溢出,模糊了我的键盘,我抬起头望着窗外,突然觉得我们的人生摔打着摔打着就变成了薄脆的瓷器。2012年年末,当母亲因为面部浮肿而被查出肾问题的时候,在年关将近的日子,我们兄妹带着她赶乘飞机前往西京医院手术,在医院半个多月的日子里,我再一次见证了母亲的衰老,见证了生命的起伏和动荡,见证了岁月的仓皇与不经。
2013年,是我惊梦的一年,孩子强说着他的强大,母亲弱示着她的弱小,站在这中间的我,既不敢逞强也不能示弱。我一直在想,我到底应该保持怎样的一个国度,我该怎样做好一个码头,才能把这流水一样的人生从两头摆渡好。
当我写下母亲这两个字的时候,我觉得我人生的电影,正上演在童年时代露天的打麦场上。父母忙的时候,我们经常流浪在别人的屋檐下。由于父亲幼年丧母,所以父亲的继母永远手搁袖筒漠视着我们一家。我们来自长辈的温暖,除了父母,似乎再找不到第二个源头,所以,我们的童年就多了一些悲壮的色彩。大我四岁的姐姐,在大人为生计奔忙的日子里,走走歇歇,接应母亲拉着我跌跌撞撞走完了整个艰辛的童年,成为我生命中需要感激的第二个女人。我感谢我的母亲,在我们懵懂的人生初期,让我们姐妹在逆行的鱼与顺流的叶间相遇,并同时,让我和姐姐能有机会在同一个城市相扶在她的左右。如果一切都还来得及,我想说,这人生若还有惶恐,这惶恐就由我来担待,这人生若还有碎片,这碎片就由我来拾拣。因为在我眼里,在我人生最初的信仰里,所有迟到的人必是要主动接受爱和时间的求证、洗礼和检阅。
现在,当我再度回头注目这些行走着的文字时,我觉得我人生的电影,转而上演在村东头的老式戏台上。上小学的时候,我经常做节目的报幕员,那时报幕的站姿好像要成丁字型,因为没有脑子,被当时在学校当代课老师的母亲不知教训了多少回,流了许多委屈的泪水。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的严格是出了名的。我人生的第一台戏是《手拿碟儿唱起来》。为了演好它,我常常一个人站在院子里不知要练多少回,一个小小的学校文艺宣传队,让我的童年走上了迷幻的戏台,而小小舞台的背后,母亲,就是那盏永远亮着的镁光灯。沉静的时候,我觉得我骨子里天生有文艺的味道和气质,只是我不明白,后来的后来,为什么退化的如此厉害,以至于在多个场合,竟一改年少的轻狂和欢快,被死寂的世界所打败。是年少的大戏唱尽了一个人的繁华,还是中年的仓皇躲不开俗世的盘剥和掠夺,当一个人无限进入时间的凉薄期,是否一切都存在于怀疑现在和误解过去的鼎盛期?
现在,我坐在不惑之年的门槛上回忆过去的光阴,我感觉那些像树影子一样的光阴就是投在墙上的壁画,美得欢愉而凄凉。我在这些树影中间常常看见母亲年轻时的模样,劳动时的模样,生气时的模样,微笑时的模样,进而看到我跟进在大人后面唱大戏的模样,看到自己唱小戏的模样。现在,这些模样加在一起构成了一张庞大的脸谱,这些脸谱,到最后变成两个巨大的圆,一个是母亲的,一个是我的。我和母亲是两个永远不等的圆,我的圆再大也大不过她的圆,我只是她永远的半径,因为她是母亲。我和母亲是两个永远不同的海,我的海再宽也宽不过她的海,我只是她碧波里的一条小船,因为她是母亲!
在一个城市居住,常常遇到痛疾便去投奔母亲或者要母亲来家服侍。从西门到东门,心情宽敞的时候,沉溺在自己的小窝里,多会无耻地忽略母亲。但每每站在母亲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听她指着那些青涩的果实说话,就会觉出她的絮叨如葡萄般晶莹和温暖。便想,母爱是什么呢,时光有多么无情,盛放在亲情碗里的水便有多么忘情!这份厚重的大礼常常让我泪湿衣襟,不能自己。某日读北岛,他说文字是他一生不可丢弃的行李,那么我想,我的母爱也是,相信全世界的母爱亦如斯。
是的,我们做母亲的孩子时,把皱纹都抛给了母亲;我们做孩子的母亲时,把活力都捐给了孩子。我们做母亲的孩子时,喜欢在播撒的时候结伴;我们做孩子的母亲时,更喜在收获的田垅上分行。是的,母亲这个词,无论它存在于一个人的过去还是将来,它都会是一种恒定的温度,永不因时光的破损而落旧。
听到过一位母亲的故事,给她脑瘫的儿子日复一日地熬粥和讲故事,那熬粥的料精选至最长最大、颗粒饱满、质地晶莹、略带些翠青色的米粒,她把它放进一只瓦罐,倒上沉淀过的泉水,用柴火慢慢熬。火不能太猛,否则粥会受热不均匀。她把火候调理得恰到好处,而每熬一锅粥,通常要花费两个半小时。她对着粥吹气,直至吹到自己呼吸困难。等粥凉了,这才喂身边的儿子,可她的儿子双目紧闭,一次又一次地拒绝着她的劳动果实。年复一年。她的手指已经变得粗糙而迟钝,她的力气也大不如从前,往往是粥冷到一半时便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必须借助蒲扇来完成下一半的降温。可就是这样的坚持,最终迎来了“妈妈,我要喝粥”这样一句简单却曾经无比艰难的话语。
这只是个母爱如粥的故事,还有更多关于母爱的故事供我们在其中叙谈。此时,我更愿意把母爱比做莲,无论从物质还是精神上,它都赋予了人世最高的旨意。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洁净如斯。在我看来,这莲,它既是佛国的象征和圣花,也是凡界的姿态和品质。而我更想说的是,如果我们每个人心中真的有佛,那蝴蝶就该是三月的佛,那胡杨就该是大漠的佛,那寒梅就该是冰雪的佛,而母爱,就该是端坐于儿女心中的佛,永远值得我们用毕生的虔诚去诵读,去热爱。
我想我接下来需要更加在意的,是要看管好我心中这佛一样的母亲般的莲,我知道,我是母亲身上的叶子,当她老到一个根时,我想我就是终要回到她身边的泥土。现在,我要趁夏天未到而春光四溢的日子,递给母亲一杯水。这水里,有我们紧紧握住的两截时光。我要我们母子的眼光在这里交汇,在这里碰撞,用溅出去的水珠,折射和照耀我们共同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