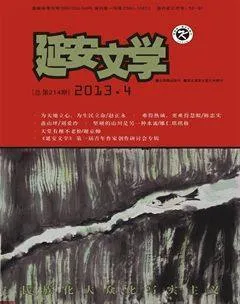难得热诚,更难得慧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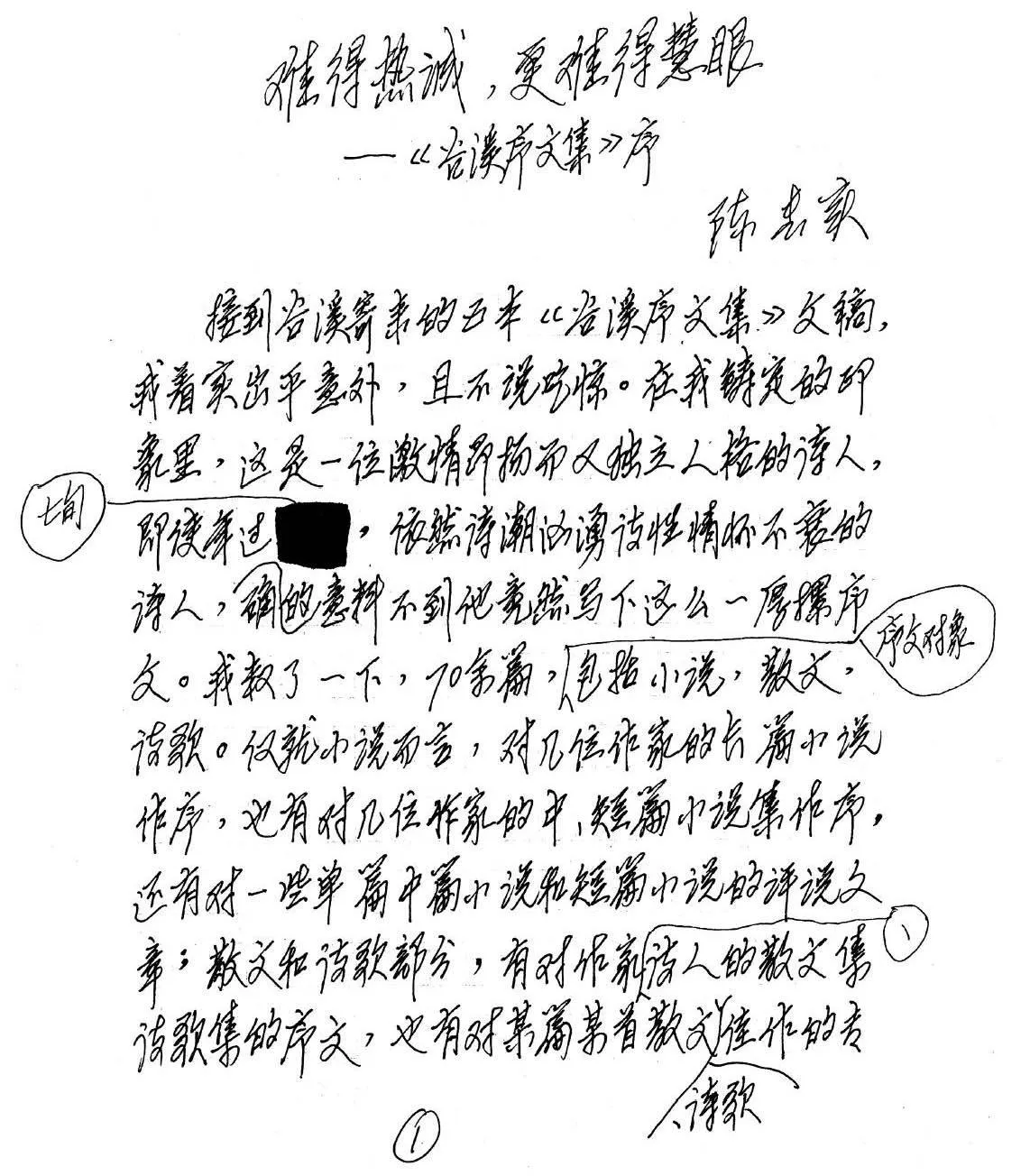
接到谷溪寄来的五本《谷溪序文集》文稿,我着实出乎意外,且不说吃惊。在我铸定的印象里,这是一位激情昂扬而又独立人格的诗人,即使年过七旬,依然诗潮汹涌诗性情怀不衰的诗人,的确意料不到他竟然写下这么一厚摞序文。我数了一下,七十余篇,序文对象包括小说、散文、诗歌。仅就小说而言,对几位作家的长篇小说作序,也有对几位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集作序,还有对一些单篇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评说文章;散文和诗歌部分,有对作家、诗人的散文集、诗歌集的序文,也有对某篇某首散文、诗歌佳作的专论。我约略估计,由他作序的这七十余部(篇、首)的小说、散文和诗歌,少说也有千万余字吧,这是一个很大的阅读量,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肯定要舍弃他的不少诗歌创作时间;更难得的是他写的序文,都是他认真阅读作品的真知灼见,无论一部长篇小说,乃至一首诗歌,他都能切中作品的独特品性,道出作家和诗人的独特体验。这不仅显现着谷溪鉴赏作品的独特品位,我更感沛他阅读的老实和认真,不仅是对序文作品和作者的尊重,也见得他对文学艺术的始终不渝的虔诚和神圣。看了这些序文的写作时间,且不说他在年富力强的年龄区段里写的或长或短的文字,我更感沛的是他近年间的序文写作,一个年过七旬的陕北老汉,依旧在认真地阅读长篇小说和散文、诗歌,依旧激情不减地写作他的阅读感受。从他的序文文字里,处处都可以感知他的思维的敏锐和一如既往的激情,我便不由地感慨自语,这个陕北老汉不见老啊——许多年前,我嬉称谷溪陕北老汉,他还我以关中老汉,到了真正成为老汉的今天,我读谷溪为诸多作家、诗人所写的序文,却感知到他的思维依然保持着既往如青年时代的活力,那根敏感文字的神经依然敏锐。
阅读谷溪所写的一篇篇序文,领略他对那些小说、散文和诗歌的精道而又坦诚的评说,不仅令我信服,而且诱发起我对那些作品的阅读欲望。于此同时,我甚为强烈地感知到序文著者谷溪对他脚下的那方地域——陕北的情感色彩,这种堪称浓到化解不开的情感,是一种不自觉到自然的流露,浸洇在文字之中。须知这些序文多是写给那些以陕北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散文和诗歌,而非谷溪自己直抒对陕北这块大地的情感和体验的散文和诗歌,依旧能让我甚为强烈地感知他对自己足下那方地域——陕北的情感。我便想到,但凡涉及陕北这块大地的文字笔墨,无论作者是他的新朋老友,抑或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都会触发他的情感激情。他为知青作家许复强的长篇小说《情感之恩》所做的序文《深播高原的爱,破土萌发》一文中,叙述了许复强“怀胎十年”或者说“十年磨一剑”的矢志不移的精神写成长篇小说《情感之恩》,也作出精当而又令人信服的评论。然而让我尤为感动的是他的情感。许复强是一位到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谷溪曾在延川当过专管北京插队知青工作的专职干部,并不认识在另一个县插队的许复强。直到三十多年后的2011年,谷溪接到“一个陌生的长途电话”,是许复强邀他为刚刚写成的长篇小说《情感之恩》作序。他说:“作为一个年逾古稀的文艺工作者,曾一次又一次地下决心不再写序文之类的文字了……我还有什么托辞的理由呢?我的‘知青情结’驱使我不仅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并告诉他正要赴京开会,届时一见。”
我甚为敏感谷溪的“知青情结”,不单是作为“知青专干”和北京插队知青的情感业,已凝结成为一种“情节”,更让我感知到他对陕北的情感,已经扩展到在陕北经历过风雨的北京知青身上,成为他乡土情结的另一个载体。似乎可以说,但凡与陕北这方地域有关系的人和事,都能触发他那根情系乡土的神经,既是本能的又是自觉的。
谷溪这种乡土情感,在对诸多陕北籍作家和诗人的作品的序文里随处可以感受得到,他把对这方地域的情感很自然地转化为对陕北作家诗人真诚的关爱和扶助。在给女作家魏常瑛的长篇小说《大山深处》所作的《令人在灵魂深处隐隐作痛的土地》序文里,谷溪言不由衷地感慨:“为什么陕北的后生们强悍耿直,姑娘们漂亮而灵秀?为什么在那赤裸裸的山沟里总弥漫着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文化气息……”在他沉浸在陕北山沟里的“古老而神秘的文化气息”里的时候,顿然惊悟:“一说陕北,话头就长。”可见陕北在谷溪心中的分量以及迷恋的状态。他对女作家魏常瑛由发现到写这篇序文,竟有二十余年的连续而直接的关注和扶助,最初发现她的一首小诗和一篇散文,由他推荐发表在《榆林日报》和由他主编的《延安文学》上,直到二十年后为她的长篇小说《大山深处》作序,就把一个痴情文学的陕北女子导引为可以自由挥洒笔墨的作家,他对《大山深处》的成功面世,对其艺术创作的独特魅力的点评,似乎比自己某篇作品的出手更欢欣鼓舞。
在对兰一斐的中篇小说《龙冢》的点评里,由这部中篇小说题材所涉及陕北大地历史渊源这个独特视角的诱发,谷溪便以诗人的敏感由衷抒怀:“山穷水瘦的陕北高原古老神秘,充盈着浩瀚的沧桑感和原始的韵致,每每使人感动,却又令人难以尽解其中底蕴……”因为《龙冢》成功开掘到“其中底蕴”,它不仅赞赏《龙冢》的“多义性象征的叙述体系”、“开放性的召唤结构”,也抒发他对这方神秘而又神奇土地的诗性情怀。再如点评王冠的中篇小说《黑衣鼓手》时,对陕北一种源自狼皮做的鼓的传承,鼓手和鼓道的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和精神的揭示,都使谷溪发生连连赞美和赞叹。在对赵秉宙的小说创作所写的述评里,谈到《黄土冲动》里陕北汉子走西口的生活,我看到谷溪已经不像是在评点一部小说,而是对陕北高原和高原上的人在呐喊……我在文头所说的谷溪对陕北高原有浓到化解不开的情感,是我最直接的阅读感受。
在谷溪序文的阅读中,我的又一种甚为突出的感受,是他对作家和诗人的个性化艺术追求的敏感和推崇。任谁都晓得,艺术都是以独具个性的魅力才呈现其生命力的,个性化的艺术创作本身的含义便是独辟蹊径,即创造。既有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独立发现独到理解独特体验,也不可或缺艺术风景的别具一格的新鲜。谷溪不仅深谙此创作规律,而且尤为关注作家和诗人的个性化特质,对他序文的写作对象的个性化艺术的发现和强调,不仅让我看到他对创作的深刻理解,也会使序文写作的对象受到启迪,进而坚定业已呈现的个性化创作的信心和勇气。
《背着爱与亲情去偿还爱》这篇序文,是写给青年作家常胜国的小说集《以生的名义》的一篇评论。他对常胜国的小说逐篇做了点评之后,便发生了“为什么同样的故事,由不同的人讲出来,效果差别甚大”的思考,及至和常胜国交谈时,常胜国道出自己信奉且“常常品味海因里希·伯尔的一句话,‘经过许多磨练,后来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在这里,谷溪完全意识到这位青年作家的个性化艺术追求的难能和可贵,便欣然坦言:“我以为‘强烈的个性色彩’不仅是画家的追求,也应该是一个作家的追求……”可见谷溪已经领略到创作的真谛,不仅自己循此创作,也和青年作家形成共识。写到这里,我也颇多感触,我很信服海明威关于自己的创作概括为“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的语录,与谷溪和常胜国信奉的海因里希·伯尔的“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不仅英雄所见略同,连语录的文字都相似。对于散文写作,谷溪同样尤为关注作家的个性化气质,包括语言。他赞赏刘凤珍的散文正是基于这一点:“如果说美学理想是作家美学追求的目标,那么审美情趣则是作家个性化风格的集中展示。”正是在刘凤珍的散文中敏感到“个性化风格”,便涌出洋洋洒洒的欣赏和赞扬的评说文字。仅从他对常胜国的小说和刘凤珍的散文创作的个性化艺术的发现而言,可以看出谷溪对作家的深层理解的准确,才显出识才的慧眼,颇令我钦佩敬重。
早已耳闻谷溪关爱文学作者的动人佳话,却只有在读过他的序文集才明白其底里,他不是通常所见的热心热情抑或关照等等,而是对作者作品的理解。理解作品才是对作家的最可贵也最难得的关爱。道理很简单,无论初登文坛的青年作者,抑或痴志不改几十年的中、老年作家,他们最感开心最为欣慰的事,莫过于新作出手便能被一位编辑或朋友理解其中的用心,常会发出“知我者某某也”的酣畅的人生慨叹,较之饥与饱,冷与暖等生活关照相去甚远。无论作《延安文学》主编时长年累月审阅文稿,无论接待各方诗朋文友切磋艺术,及至年过七旬依然为他欣赏到欣喜的长篇小说《情感之恩》作序,便可见得对文学的痴情。痴情表现最为重要的关键一点,便是对作家作品的理解的慧眼和慧心。这是谷溪赢得老少男女文朋诗友称赞的关键,也是难得的一点。
《亮开一个陕北女子的心灵世界》这篇序文,是写给耿永飞仔的小说散文集《恣意盛放》一书的。这是一位80后的青年女作家。谷溪对这位在他看来“与生俱来的文学天赋”的作家的作品集逐篇点评,尤其欣赏中篇小说《恣意盛放》,给出了切贴而又非同寻常的评价:“作者在用法律、道德、情操的准则去审视、掂量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更重要的是,作者自觉不自觉地向人类灵魂提出了严正的质疑和拷问。”我推想小说作者耿永飞仔读到这些评说文字,会有一种被理解的欣慰和舒悦。他对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者胡同的发现,亦是从他的非同凡响的中篇小说《村政》发生的。面对一位“清癯的陕北后生”送来的几部中篇小说手稿,也面对缺乏资金而难以付印的《延安文学》的困境,他不惜版面(刊物80页码)头条推出中篇小说《村政》。“《村政》的刊发,在国内一度引起不小的争议和关注,许多读者纷纷打来电话,询问作者情况,索要他的联络地址。评论界人士也很快写来评论文章……”关于这部小说的评论,请读谷溪序文原文,我不再赘述,让我感动的仍是谷溪对《村政》的理解。若要证明谷溪这种理解的准确,是作品面世后的强烈反响;一个地级市的文学刊物的一篇小说能引发全国读者的阅读兴趣和评论家的关注,确非易事。我替青年作家胡同庆幸,他遇到一位能理解其杰作即识货的谷溪,便破土而出了。如果说对胡同的发现是他编辑职责范畴的事,而对张志远作品的敏感和理解却是一个偶然,他到周至楼观台看望一位朋友时,朋友说到当地一位“酷爱写作的人”张志远,晚上便热心地翻阅张志远的小说稿,“虽然有些地方显得粗糙,可是取材新颖,构思奇巧,字里行间喷发着一种惊人的力量。有一股匪气、霸气和山野之气,扑面而来……”这是他初读的印象,可以说是独具慧眼独特感知的印象,由此而断定,“他是一块急待打磨、抛光的玉”。谷溪便用心着力“打磨抛光”张志远这块内蕴文学创作天赋的玉,一年后推出他的短篇小说《塔里木叔叔》,成为他叩开文学之门的第一块敲门砖,之后便有中篇小说短篇小说不断出手,这块玉就亮出其独有的光彩和魅力了。谷溪对高安侠散文集《弱水三千》所写的序文《弱水心中流》,本身就是一片动人的散文。谷溪对一位获得生命体验的作者的散文佳作的领会与感动,形成倾泻般的激情文字,既是对一位创作者的才华的赞赏,更在为难能进入深层的生命体验的散文佳作的面世而倾洒激情的文字。其实,谷溪这种沉迷的阅读在多篇序文和编稿手记的短文中都有流露,那种对作品理解和赏识的文字行间,让我时时都能看到一双智慧的文学眼睛。
读谷溪所写的序文,我不仅有如上几点感想,竟而发生感动,这是少有的乃至仅有的阅读现象。被一篇小说、散文或一首诗感动是常有的事,而被评说作品的序文感动,却也难得发生。况且,在人们通常的印象和意识里,序文多是连篇累牍的溢美文字,读者甚至可读原文而避开序文,使序文丧失了公信力。谷溪的序文不仅让人深信不疑,而且让我发生陷入性的阅读,这其中的魅力不单是诗性文字,更是他的真诚。他对作家个性化艺术气质的敏感和对作品的深刻而独到的理解,也异常鲜明地呈现出序文作者谷溪的独特禀赋,序文的个性化文采就令我进入沉迷性阅读了。
为作家朋友的新作写序,我也写过多回。而为一部序文集写序,在我却是唯一的一次。这篇序文之序,举例多涉及到谷溪序文中提到的小说和散文,而未涉及诗人和诗歌,留一点遗憾,其实在谷溪的序文中都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