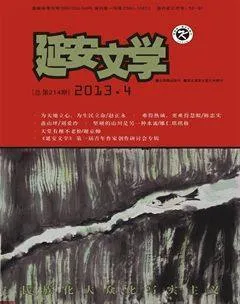路遥:文学的役夫与殉道者
一、路遥是一位用整个生命打造自己文学世界的作家,他是文学的役夫
路遥的生命非常短暂,只活了42岁,在1992年就英年早逝,过早地离开了他深爱的土地与人们。但他一生活出了质量,活出了高度,活出了精彩。
路遥一生有许多名言,值得人们铭记:“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人可以亏人,土地不会亏人”;“只有白受的苦,没有白享的福”;“只有庄重地生活,才能庄重地工作”;“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艺术劳动应该是一种最诚实的劳动”;“最渺小的作家关注着成绩和荣耀,最伟大的作家常沉浸于创作和劳动中”;……这些朴素而又富有哲理的话语,是路遥人生精神与文学精神的最好诠释。
路遥是一位怎样的作家?路遥的朋友、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描认为是一位“永远的跤手”,他一生跟自己摔跤、跟别人摔跤。我倒认为路遥是文学役夫,是文学的殉道者。路遥成功的原因很多,有一点不容忽视——他是一个视文学事业为神圣使命,并用整个生命去打造自己文学世界的作家,他是用燃烧生命的方式进行着文学创作。
文学作品是作家心路历程的复杂显现。要了解作家的创作,必须了解作家的生平状态。
在路遥的人生道路上,有这样几个关键性的节点,必须引起研究者高MW3tbdyAnv3hJV+knwO5OVJ/uvPhyo/fkD17A0CAgv0=度关注:
一是1957年秋被过继给延川县的大伯为子,使路遥形成了敏感与克己的独特心理。父母没有文化,兄弟姊妹众多,家境异常贫困,到1957年,他已经是拥有三个弟妹的老大,也是一个非常懂事的陕北男孩。父母因为家穷,无法供路遥上学。而要满足这个最低的愿望,只有被过继。于是,在很多年后路遥回忆到这个令人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我特别伤心,觉得父母把我出卖了……但我咬着牙忍住了。因为,我想到我已到上学的年龄,而回家后,父亲没法供我上学。尽管泪水刷刷地流下来,但我咬着牙,没跟父亲走……”(路遥《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这就是当时一个实际年龄不足七周岁孩子的真实心理与选择,苦难让他过早地懂事,并拥有超乎寻常的强大控制力。
现代心理学认为,五至七岁是人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此时的心理积淀将形成一种定势,成为影响个体性格和行为特征的重要因素。幼年时期的人生变故,对于路遥敏感心灵的形成,无疑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路遥曾说过:“正是这贫穷的土地和土地上贫穷的父老乡亲们,已经教给了我负重的耐力和殉难的品格——因而我又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是富有的。”他当年创作《平凡的世界》的种种思考和工作方式,在其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有真切的记录。路遥的“克己”令人颇为感动:1984年冬天,他当选为全国作家大表大会代表,有机会赴京参加作家们的盛会,但是他因做创作《平凡的世界》前繁复的准备工作,毅然放弃参加这次会议;1991年冬天,他本来被指定为中国作家赴泰国访问团的团长,但是因为正在写作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而又一次放弃出国机会。像路遥这样敢于放弃各种诱惑而心无旁骛地谋大事的当代作家,并不多见。
二是在延川能够接受完整的小学到初中的教育,对于培养路遥高远的人生志向提供了重要条件。苦难的童年经历,形成了路遥独特的心灵感受,同时也培养了他高远的人生理想。1958年春,他插入延川县马家店小学上一年级,并正式取名叫王卫国。1961年,他考入延川县城关小学高小部上“完小”。在城乡差别严重的1960年代初期,路遥是生活质量极差的“半灶生”,但他克服了自卑,由自卑走到自强,由虚荣走到包容,他的心理成熟与稳定得令人不可思议。1963年,小学毕业后,养父不愿他参加全省的升初中考试,让他回农村“受苦”。路遥明确告诉大伯,他必须参加全省的小学升初中统考,他要证明自己是有能力考上的。考试的结果可想而知,当年全县一千多名考生,只招收两个班的初一学生,路遥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名列“榜眼”位置。在伯父没有条件供他上学的情况下,路遥在同学的接济下硬是把中学读下来。路遥当时所在的班级是尖子班,班上同学大都是县城干部与职工子弟。路遥不仅衣服破烂,而且还经常吃不饱。一个正在成长的男生,经常饿得发晕。但是,他却在不断丰富自己的阅读中(去县城的文化馆与书店阅读),获得了精神的高度超越。他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宇宙飞船在太空遨游的消息后,竟兴奋得彻夜难眠,站在县中学空旷的大院里,遥望夜空中如织的繁星,寻找着加加林乘坐的飞船轨道。以至于他在创作中篇小说《人生》时,给主人公起名时,第一感觉就是“高加林”三个字。由孤愤到倔强,由绝望到渴望,由征服到宽容,由激情到理智,成为男生路遥初中三年的主色调。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有了最初的文学冲动……
三是路遥在历经一次极速的“青春过山车”后,开始用文学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1966年夏,路遥在初中升中专考试中,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当时的西安石油化工学校。在当时的情况下,农家子弟要是考到中专学校去,就意味着鲤鱼“跳农门”,从此彻底脱离农村这个苦海。然而,命运总是无情地捉弄着这个饱受饥饿折磨、却又志向高远的农家小子。“文革”爆发了,全国所有的大专院校招生无限期停止,所有毕业班学生留在原校就地闹革命,即是已考取大专院校的学生也要返校参加革命。就这样路遥被卷进这场革命风暴与革命闹剧中,他用一种近似荒诞主义戏剧表演的方式,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消耗着青春与精力。1968年9月15日,19岁的路遥就以群众组织代表的身份结合进了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成为县革委会副主任。然而,命运再次跟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路遥倾注了满腔热情的这场政治运动,突然显露出残酷的一面。一心想要跳出“农门”的他,又一次以“返乡知识青年”的身份背着铺盖回到农村。
就在强大的政治肆意捉弄他的时候,路遥开始迷恋上文学,狂热地喜爱上诗歌创作。他最初的诗歌创作明显地带有“顺口溜”式的灵气。如《老汉走着就想跑》:
明明感冒发高烧,干活还往人前跑。
书记劝,队长说,谁说他就和谁吵:
学大寨就要拼命干,我老汉走着就想跑。
他第一首以“路遥”笔名发表的诗作是带着政治印记的《车过南京桥》。从此,“路遥”,这位在政治失意后钟情于缪斯的年轻人,他决心手握文学之笔,在文学上“突围”,实现重新拯救自我人生的独特道路。
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即北京知青对路遥文化心理形成的重要影响。“文革”期间,先后有二万八千名北京知青来到当时的延安地区插队,其中的大部分人是1969年2月初来到延安地区的各个县农村的。延川县当时接纳了两千多名北京知青,全部来自海淀区,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还是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拥有高知与高干的家庭背景,他们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一夜之间撒落到延川的各个村庄。兵团知青始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整体,与百姓没有更深切的接触。而插队到延安的北京知青,与他们的最大不同,是撒到延安农村的,接触到中国最贫穷地区的真实情况。现任党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当年曾在距我的家乡禹居村六七公里左右的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他后来接受过延安电视台记者的采访时说,他当年在延川农村插队,是过了“五关”的历练——即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著名作家史铁生回望陕北,创作了著名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知识青年插队到农村在受苦受罪的同时,也传播了现代文明。路遥就受到现代文明的巨大诱惑,他喜欢与北京知青交往,甚至他的初恋的女友就是北京知青。在经受一次极速的“青春过山车”的大喜大悲后,他与北京知青短暂的初恋也宣告结束——年轻的路遥把招工指标让给这位姑娘,这位姑娘远走高飞后用“绝交信”断绝了路遥的全部希望,甚至差点把他推到“死亡”的边缘。1991年,路遥在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轻描淡写地回叙了当时的情形,说:“后来的一次‘死亡’其实不过是恋爱期的一次游戏罢了”。他后来的妻子也是北京女知青,他们经过七八年的相恋,最后走进婚姻的殿堂。路遥喜欢在雨雪交加的天气中散步、喜欢唱忧郁的俄罗斯民歌、喜欢喝咖啡等具有贵族式的生活方式,均带有他青春的印记。
四是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让他有机会贮备了振翅高飞的文学能量;分配到陕西省作家协会当编辑,更使他拥有了进行文学远征的充分条件。并不是说年轻的路遥追求文学后就万事大吉了。相反,关于他“文革”时期担任造反派学生组织头目的事情,始终是他的人生梦魇,甚至伴随了他一生。就在他从事最初的文学创作卓有成效之时,路遥当初的政治敌对派们并没有放弃对他的纠缠,状告他在武斗中有人命官司。在事实得到澄清后,他才好事多磨地进入当时延安大学中文系73级学习。这个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路遥人生的飞翔方向。进入大学,使他一方面有机会储备充足的文学能量;另一方面,也使他拥有更广阔的文学视野,为其文学远征做好准备。1976年,路遥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当时的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的《陕西文艺》编辑部工作(即后来的陕西省作家协会《延河》杂志的前身),获得了文学创作的必要条件,开始了雄心勃勃的文学远征。
五是在新时期“相互拥挤”的文学环境中,“农裔城籍”的路遥找寻到“城乡交叉地带”这个属于自己独特生命体验的优质文学表达区位。新时期到来后,路遥还始终是位文学杂志的“小编辑”,他只能在编辑之余,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在新时期之初,他“马拉松”式的恋爱终于有了结果。1978年元月25日,他与相恋七八年之久的北京知青林达结婚。1979年11月,他与妻子的爱情结晶——唯一的女儿降临人世。新时期之初,文学界拨乱反正,一派生机,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得到极大的鼓励,这对于心性刚强的路遥来说,均构成了巨大的冲击波。路遥一边冷静地审视着文坛动向,一边认真思考与创作。直到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当代》杂志1980年第3期发表后,他在陕西文学界坐冷板凳的际遇才有所改变。
这篇小说没有迎合当时“伤痕文学”逞一时之快发泄情绪的路子,而是进行彻底的“文革”反思,写一位县委书记在“文革”中为制止两派的武斗而进行飞蛾扑火式的自我牺牲。这篇小说在屡退屡投的坚持中,终于等到了文学前辈秦兆阳的赏识。这样,路遥的文学创作命运有了转机。他真正的文学创造道路是从这篇小说开始的,作为作家的艺术个性也是从这部小说开始显露的。从此,路遥的创作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路遥是从中国底层一步步地成长起来的“草根”奋斗者,他在心无旁骛地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还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处理他无法回避的事情。他虽已是公家人,身在“城籍”,但他却是“农裔”,他的根尚在陕北农村,他无论如何必须正视。他是家中长子,众多的弟弟妹妹需要他帮扶。尤其是他在帮助三兄弟王天乐由农村招工到铜川煤矿的过程中,更是绞尽脑汁,不择手段。另一方面,他又从自己和兄弟们的现实处境中由己度人,深入思考中国广大农村有志有为青年人在城乡二元对立社会中的出路问题,催熟了先后创作三年、三易其稿的中篇小说《人生》,甚至为日后创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找到了现实灵感。
《人生》的创作是路遥找准创作发力点后对自身的一次成功超越。这篇小说在透视社会的深刻和描摹现实的真切上,超越了路遥以前所有的作品;它在表现生活的深度上和人物形象的复杂性上,也超越了同时期的作家思考。《人生》发表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致于1982年被文学界称为“路遥年”。这部中篇在1983年荣获全国第二届中篇小说奖的前列。《人生》发表后路遥又接连发表了《在困难的日子里》、《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你怎么也想不到》等中篇小说,继续在“城乡交叉地带”思考当代青年的命运,抒写城乡融合的独特感受。后来创作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也走的是这条路子。
六是奋进中的路遥每每在“山穷水尽”之时,总有“贵人相扶”,这也使得他拥有了更坚定的人生信念与更开阔的、包容万物的人生胸襟。对于在卑微中崛起的路遥而言,吃苦是生命的基本底色与常态,他有的是毅力与吃苦精神。他明白,“贵人相助”只会出现在奋斗者的身上,机遇永远不会降临到没有准备者的身上。1963年,他在由小学升初中的过程中,是他的“干大”刘俊宽的倾心相助,他才能够进入中学学习;1971年,他为“文革”造反派头子之事焦头烂额、初恋情人又决他而去之时,是延川县当时的诗人曹谷溪给他提供了文学阵地《山花》文艺小报;1973年,在众多大学拒绝路遥入学的情况下,是县委书记申昜多次亲赴延安大学力荐,才使他能够进入大学之门;1976年大学毕业时,也是当时《陕西文艺》编辑部的负责人们因为爱惜人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他进入省城的文学杂志工作;1980年,他的中篇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周游众多文学杂志无果的情况下,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当代》主编秦兆阳发现并赏识,才使路遥的作品在《当代》发表,荣获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并被全国文坛所关注。甚至到1987年,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在文学界遭到冷遇后,又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叶咏梅女士用一片柔弱的“叶子”托起了它,使得它最后乘着广播的翅膀飞到全国千百万听众那里……
陈忠实曾这样评价过路遥:“路遥已经形成的开阔宏大的视野,深沉睿智的穿射历史和现实的思想,成就大事业者的强大气魄,为实现理想的坚忍不拔和艰苦卓绝的耐力,充分显示出这个古老而又优秀民族最优秀的品质。”
是的,路遥特殊的人生经历与独特的生命体验,使得他在强大的理性精神下不断超越自己,成为文学的役夫,文学的殉道者。
1992年11月17日,路遥因积劳成疾,在42岁时英年早逝,令无数读者扼腕叹息。贾平凹说,路遥“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他的文学就像火一样燃出炙人的灿烂的光焰。”
时代在变,但勇于超越自我的优秀品格却是永恒的。就路遥的拼搏精神、奋斗精神而言,理应值得中国文坛的尊敬!
二、《平凡的世界》提供了鼓舞人向上和向善的正能量
文学的本质不是华美的语言与复杂的结构技巧,而是展示人性的光辉,传达一种精神和力量。
新时期之初,当许多作家还沉浸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之时,路遥却把目光投向变革中的现实生活,关注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情感。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精心刻画自尊、自强的少年马建强形象,并着力歌颂在困难的日子里人们的美好心灵;中篇小说《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不仅是关注普通人的家庭伦理道德生活,更着力赞美宽厚与包容的人性美德;中篇小说《你怎么也想不到》,则是通过男女主人公的限知视角“我”的叙述,塑造了献身家乡的女大学生的美好形象。他的代表作《人生》,则把人物置身于“城乡交叉地带”,关注现实的农村有志有为的青年人的出路问题,直击中国城乡二元社会之弊。《人生》的巨大成功给路遥带来荣耀,但他更清醒地认识到“眼前热闹的广场式生活必须很快结束”。于是,他从《人生》成功的幸福中断然抽身,潜心创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进行更加艰苦的文学远征。
路遥最早给这部长篇小说取名为《走向大世界》,他决心要把这一礼物献给“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他设定了这部小说的基本框架是“三部、六卷、一百万字。作品的时间跨度从1975年初到1985年初,力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他还分别给这三部书取名为《黄土》、《黑金》、《大世界》。
这部三部六卷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先后花费路遥六年左右的时间。其中,仅扎实而认真的准备工作就断断续续地准备了三年——他潜心阅读了一百多部长篇小说,分析作品结构,玩味作家的匠心,确立自己的小说大纲;他阅读了大量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以及农业、工业、科技、商业等方面的书籍;他甚至还翻阅过这十年之间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延安日报》。十九世纪法国美学家泰纳曾提出文学创作与发展的“三要素(即种族、环境、时代)论”,并认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 。1980年代,正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黄金时期”,许多人都有自己美好的人生梦想。路遥以孙少平、孙少安兄弟的奋斗串联起中国社会这十年间的城乡社会变化,用温暖的诗性现实主义方式来讴歌普通劳动者的奋斗。
1988年5月25日,路遥终于为《平凡的世界》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这部小说,在1988年就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续广播”节目在每天中午十二点半播出,它乘着广播的翅膀飞到千万读者的耳畔与心头,并产生了强烈共鸣,这让文学界最始料未及。可以这样说,是亿万读者把路遥推到茅盾文学奖的领奖台上。
《平凡的世界》为何能产生巨大的反响?评论界有多重解读。著名学者王一川教授认为,《平凡的世界》是“改革年代的现实型自我镜像”;学者邵燕君认为:“《平凡的世界》深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是,作品中对农村贫困生活大量的细节描写在相同经历者中引起极大的情感共鸣,主人公不屈服于命运的奋斗精神也给读者极大地精神鼓励”;甚至有评论家认为《平凡的世界》是《人生》扩展版,我不苟同这样简单的概括。
我的理解,与《人生》相比,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则具有了人性的高度,作家把苦难转化为一种前行的精神动力。
就《平凡的世界》而言,它不仅展示小人物不甘于屈从命运的不懈奋斗,更在于传达一种温暖的情怀。一是作者对作品中的人物寄予了同情心,对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做到了极大地尊重和认同。不要说作品的主人公,就是作品中的一些消极人物,如乡土哲学家田福堂,游手好闲的王满银,善于见风使舵的孙玉亭,甚至傻子田二身上却直接或曲折地折射出人性光彩。作者充分理解各种人的存在、生活方式以及意义,并按照他们的行为逻辑安排他们的命运。二是作品处处展现温暖的亲情与友情,是一部温暖人心的小说。小说中有大量关于人间亲情的描写,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孙玉厚一家了——孙玉厚勤劳吃苦、忍辱负重;他的儿女孙少安、孙少平、孙兰香等懂得自强自立、善解人意、善于帮助别人。小说还书写了美好的同学之情、朋友之情、甚至同事之情、乡邻之情等人间美好的情感。三是作品中的爱情写得很美,完全超越了世俗与肉欲,而赋予无比美好的内涵和想象空间。这在1980年代后期“无性不成书”的长篇小说创作风气中几乎是绝无仅有。如孙少平和田晓霞在杜梨树下的近乎于柏拉图式的恋爱,就写得很纯美,让人为之感动。
《平凡的世界》传达出使人向上与向善的正能量。我的理解,这部小说所传达出的精神内涵,正是对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传统的继承。这些小说人物成为改革开放大潮下芸芸众生的缩影,人生充满挫折但自强不息,出身卑微但敢于追求爱情,它重构了中国社会的精神食粮。
这样,我们不难理解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产生如此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力的原因。
三、只要广大读者不抛弃你,艺术创作就不会在心中熄灭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与作家的“才、胆、力、识”分不开。今天回过头来看《平凡的世界》,我们不得不佩服路遥当年深邃的历史意识、逆风而行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创作毅力。如果没有路遥当年决绝般的坚持,《平凡的世界》这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兴许不会面世,更不要说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了!
事实上,路遥当年的创作是冒着很大风险的。首先是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并没有得到当时文学界的认可。这种不认可,主要是文学评论界指责路遥的创作方法“过于陈旧”。路遥在构思《平凡的世界》时,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已经是铺天盖地、滚滚而来。各种外来的文学思潮和表现方式如同“走马灯”一样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过时论的言论更是甚嚣尘上,作家们唯恐自己不新锐,唯恐自己不时髦。文学界在由“写什么”到“怎么写”的风潮转向中,许多作家纷纷开始向“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象征主义”、“黑色幽默”、“寻根文学”等方向突围。许多作家强调创作的潜意识性、非理性,强调表现人的情欲——性欲,表现人的非理性状态,表现人的原始性。似乎小说里不写人的原始性欲,这就不是小说;似乎小说在形式上不玩一些所谓的“花活”(白描语)就不是好小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路遥却坚持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这无疑是“个人向群体挑战”,这不仅要冒很大的失败风险,更要有强大的定力!甚至有人说,路遥当年坚持传统现实主义的阵地,是因为他不懂得现代主义的手法。非也!路遥不仅懂,而且很懂,他在短篇小说《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以及中篇小说《你怎么也想不到》中,曾娴熟地运用过这种创作的一些手法。他后来在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考察一种文学观点是否‘过时’,目光应该投向读者大众。一般情况下,读者们接受和欢迎的东西,就说明他有理由继续存在。”“‘现代派’作品的读者群少,这在当前的中国是事实;这种文学样式应该存在和发展,这也勿容置疑;只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负责任地弃大多数读者不顾,只满足少数人”、“至于一定要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现代派创作方法之间分出优劣高下,实际上是一种批评的荒唐。”他坚信:“只要广大读者不抛弃你,艺术创作之火就不会在心中熄灭。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
路遥更明白,“在中国这种一贯的文学环境中,独立的文学品格自然要经受重大考验”,“在这种情况下,你之所以还能够坚持,是因为你的写作干脆不面对文学界,不面对批评界,而直接面对读者。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路遥当时才35岁,但却拥有同时代作家所不具备的冷静与深刻、清醒与理性的思维品格,没有跟风。开始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注定拥有卓然而立的姿态。
其次,是路遥创作这部书时,注定是要与自己的意志品格搏斗。《平凡的世界》的第一部发表后,评论界几乎是全盘否定。路遥好友、现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的白描清楚地记得1986年冬天在京开研讨会的情景。他回忆,当时一些评论家甚至不敢相信《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出自《人生》作者之手。面对许多人的尖刻批评和否定,白描回忆当时真有些“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苍凉与悲情。路遥没有被打懵,而是在大雪纷飞的时候踏上归程。这足以证明路遥拥有何等坚强的意志品格与定力。他以极大的艺术自信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行,相继完成了第二部、第三部的创作。在写完第二部的时候,他健壮如牛的身体出了问题。我怀疑就在1987年夏天,他已经发现自己是肝硬化患者。他“身体状况不是一般地失去了弹性,而是弹簧整个地被扯断”,“身体软弱得像一滩泥。最痛苦的是吸进一口气就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一下坐,就会睡过去……”他甚至想到过放弃、想到过死亡。结果是他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在简单的保守治疗后又开始第三部创作。
路遥说过:“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当代,而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历史证明路遥的坚持是对的。据中央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李野墨先生回忆:《平凡的世界》在1988年首播时,第一部是成书,第二部是校样,第三部直接就是手稿。《平凡的世界》的广播听众达三亿之多,听众来信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最。这部小说在产生如此之大的社会反响之后,迫使评论家们重新反思自己的判断。这样路遥才有可能在1991年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茅盾文学奖已经连续评过八届了,其获奖作品已有几十部之多,但读者记住的就是其中的几部;新时期以来,著名作家也有好多,但在读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就是屈指可数的几位,而路遥的文学影响却是千百万读者所拥戴的。荣获茅盾文学奖后路遥仍保持着高度清醒的头脑,“对于作家来说,他们的劳动成果不仅要接受当代眼光的评价,还要接受历史眼光的审视”、“全身心投入生活之中,在无数胼手胝足创造伟大历史、伟大现实、伟大未来的劳动人们身上领悟人生大境界、艺术大境界应该是我们毕生的追求。”
再说远一点,路遥的这种执着精神,既是其个人魅力的彰显;也与其所拥有的陕北精神血脉不无关系。陕北自古是征杀伐掠之地,也是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化交锋、对峙与充分融合之地。陕北人在先天的文化血脉中就拥有敢于承担和宽容、包容之气,不排斥外来文化,同时又坚持自我品格。路遥的文学导师柳青就是位拥有史诗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家。因此,路遥深邃的历史意识是许多作家所不具备的。他背对文坛,迎风而立,敢于接受历史眼光的审视。事实上,路遥在面对历史眼光的审视时,他交出了一份令时代信服的答卷。《平凡的世界》不但恪守了现实主义原则,更是发展了现实主义,在新时期以来文学向“经典现实主义”回归的道路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长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对路遥这样一位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史述的空白现象。任何文学史的叙述都有一定标准的,当代文学史也不例外。在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文学的审美性成为一种合法性标准。这样,路遥的“手法陈旧过时”的《平凡的世界》就被遮蔽、被忽略不计。在诸如洪子诚教授个人治史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及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中存在被冷落、被遗忘的尴尬情况。文学史是什么?文学史的书写,不仅仅是谁拥有审美领导权与历史发言权,更在于要准确地梳理与陈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优秀文学作品,具有客观、公允的记录文学历史、启迪未来的功能。正如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所指出的那样:“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它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像路遥《平凡的世界》这样呈现中华民族精神、情感和灵魂的文学记忆的优秀作品,理应堂而皇之地进入当代文学史,而且理应占据重要位置。相反,任何忽视它的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均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与对当代文学的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