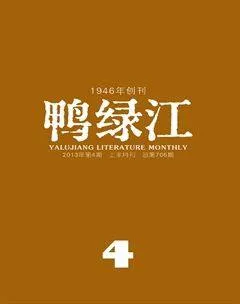云贵的粽巴叶
芦苇岸, 土家族,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生。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嘉兴市十大杰出青年,嘉兴市南湖区作家协会副主席。1989年开始公开发表作品,迄今已在《人民文学》《诗刊》《诗林》等数十家文学刊物发表诗歌、小说、散文、评论近百万字。有作品入选《星星》“诗刊甲申风暴大展”《70后诗歌档案》《浙江诗典》等选本。多次获奖。主要作品有《光阴密码》《冷,或曰道德经》,长诗《空白带》和大型组诗《湖光》等。
我们管包粽子的壳叫“粽巴叶”,发音时舌尖往里卷,双唇两边拉,尾音下吊,这“叶”字,儿化得很厉害,几近唱了。山里人的语言有个特点,哪个字被儿化,那么这个字所指代的事物就稀罕,金贵,诱人。这样说,莫不成“粽巴叶”比“粽子”还俏?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管“粽子”叫“粽子坨坨”,“坨坨”嘛,当然属于货色好,斤两足的一类。叫“叶”为“叶儿”,拖腔长,有一种悠悠美的成分在里头。显然,能够裹米为粽,为一个民族集体性的美食,还被赋予历史人物的象征意义,这粽巴叶,不美还真不行。
粽子好吃叶难采。云贵高原上的粽巴叶专择悬崖长。端午节前后,雨水好,光照足,叶子蹿得快。夜晚,耳聪目明的人,听得到像巴掌拍响的声音,看得见巴掌一样宽大的叶子在峭壁上舞蹈。这时候的粽巴叶,筋骨里蓄满清香,仿佛它自己就要去裹一把米,跳到生铁锅里,在沸水中噗噗地闹腾一番,这粽子那个香,是合了自然之精气,日月之灵光的。所以天下美食,单就粽子的动静为最大。
还是继续专注于采粽巴叶吧。背了背篓,握了弯刀,循着河谷两旁的山梁蜿蜒而去。那能裹粽子的,是精品,自然就稀少,一拨拨的人,一双双火眼,搜罗,所以留下的新叶,那是看得见采不着,让你干着急。无限风光在险峰,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有一回,大人给了我这个活,可我人小,看得见的好叶子都是人家想尽法子也采不着的。怎么办?我就劈开荆棘,往下钻,用“砍伐”这种破坏性的方式获得劳动成果。
最近听人说包粽子的叶子是芦苇叶,我就笑,这是常识性错误。粽巴叶是丛生的,不过人高,秆也比芦苇精细,特别是叶子,粽巴叶圆长,光洁,青翠,叶面泛着春光,超级明星的身材,而芦苇叶太窄,也就二指宽,这样吝啬的长相能裹粽子么?二者如果真要相比,那就是偶像与粉丝的区别,因为连我都是粽巴叶的粉丝嘛!我砍倒它们后,抓住秆子拖近,再摘叶子,效果奇好,不需要多长时间就能装满背篓。但这个破坏性行为的风险是最高的,那次我伐得兴起,脚下就轻飘飘的,脑子里只想着回家后大人的夸赞。没想到一脚踩空,呼地滑倒,整个人就咕噜着往悬崖下滚,当时心里咯噔,这下肯定粉身碎骨了。可我命大,一棵青藤缠住了腿,把我悬在半空,哗哗的河水在头皮下飞溅……险啊,事后汗流浃背,浑身乏力,采的粽巴叶最好,包的粽子最大,可我吃得最没味。
包粽子也很讲究,先把粽巴叶放水里泡,然后一张张地刷净,垒在盆里。米要新糯米,加水发上几个时辰。再爬上高高的棕榈树,砍下枝丫,将叶子撕成丝,去筋,阴干,这东西韧得很,比用棉线或尼龙线包的粽子味要纯正。再说山里人用棉线包粽子,那太铺张了点,会被人骂败家子的。将一整匹阴干的棕榈叶挂在钩子上,一根丝包一个粽子,一匹可以包几百个,齐刷刷的,像小猴崽子。啧啧,壮观!再放清水里煮,注意,是清水,煮得满屋子都弥漫了清甜的味道,那粽子就可以享用了。吃的时候,碗里放白糖,筷子夹了白白的棕身蘸着白糖,入口糯糯的,清香扑鼻。民间有此一说:某某女子长得像个粽子。如果喻体是山里人的粽子,那应该高兴。白白的就给你一个环保的恭维,这可是高档化妆品怎么也达不到的美白效果啊。
话宕得开了,离家多年,已经习惯了黄酒一样颜色的粽子了,更习惯了它的大名声。正好有朋友送了我一箩好粽,还有不少鸭蛋。好,我保证:今天吃粽子!
班船
船由鱼圻塘开出,在密匝匝的苇丛间时隐时没,抵近前港时,汽笛声骤然欢快。那个大家伙,从两河交叉的地方突然冒出来,再慢慢折身,迎向热闹的乡场……
“来了——来啦——”每天,它都会在迫不及待的欢呼声中缓缓靠岸。有时迟有时早。
简易的码头吞吐着乡场上的繁华,松散的队列稍显拥挤,肩挑背扛或者游手之人鱼贯而入。票价一元四角。茶水五角,自愿。
我愿意坐船,那时候,我闲散,不似现在慌张。
船离岸了……我在云贵高原上的乌江边专注地看过船只的往来,偶尔也坐过。铁家伙的那种吨位大,排场也大,不怕风高浪急,打近前开过猛然掀起的气浪声浪水浪总叫人惊悚不已。木壳子的那种都有一个“歪屁股船”的俗称,大小规格不一,可视船主性情。大的笨重,小的灵活。笨有笨的雅处,那便是必然响起纤夫的号子,带着血的颜色,浊重沉闷高亢苍凉,直往驻足者心里钻去……读高中时,我在乌江溯源一月有余,写过一首叫《乌江纤夫》的肺腑之诗,记得开头一句是,“大口大口地吐着带血的凄凉敲响乌江深沉的寂寞……”听惯了,也就麻木了,连那些浸染心血的文字也丢光了。灵活的呢,风吹浪涌无踪影,漂得太快,感觉都来不及找。
而缓慢开动的班船是切实的,它的速度唤起人的睿智。船体像一条拉链,在水面朝前划去,船舷的两侧,水花翻卷。这些液态的事物,一生都很平静,相互间像订了契约,谁也不曾有过主动的争先,现在,因外力的刺激被迫凹凸,才有了个高下。但也只是短暂的游离本性——它们,迅疾归位,依旧忠实于集体的沉默。
那么,在沉默的水上行进,船只能慢了,突突突地。两岸的风景,旖旎着,悄然无声。船里的客人:结伴的,邂逅的——家人、朋友、同事、知己……真正被风景感动的不多,他们喝茶,谈天。他们大多被自己感动着,被旅程聚集的愉快感动着,被迷恋终点的期待感动着。偶有几个将下巴搁在窗台上,眼光凝滞,心随逝水滑动,才会猛然发出数声幸福的惊讶!
这多半是深潜的鱼不守规矩,银白的身子从水里发射到空中,把太阳光拍得啪啪直响,然后,擦着船舷落下……或者,是高天盘旋的鸟,做了一个什么出格的动作——把稻丛间游窜的田鼠生擒了?把岸边游弋的水蛇叼跑了?把树上喧闹的夏蝉制服了?把人家晾晒的鲜鱼虏获了?不得而知,只发现惊讶声回旋的尾音,把喧嚣的船舱打搅了,制造了片刻的清静。
自然,我是惊讶者之一,不过,我惊讶在心田,在表情,在眼神。今天,那些惊讶已经渗透在血液里。我怕我异样的发声是一种破坏,在这样的旅途,我是最孤独的行者。
于我而言,很多年,鱼圻塘是一个绝对遥远而神秘的概念,隐藏在东北方向起伏的苇子里。后来,我多次从陆路去新埭得以经过,却依然不知班船泊靠的码头,那么,我在这段旅程上的起点只能从前港开始丈量。那就从前港开始吧,锁上门,穿过百米长的小巷,过桥;在临河的菜场边上,水泥码头空了,我已乘船西南而去。现在,船已驶离集市几百米,正穿过一片竹林……
河面上,随波荡漾的水草漫向岸边,拍打老朋友一般拍打着岸畔。绵延不绝的岸际,葳蕤着的芦苇、茭白、杂树、绒草,因了水浪的推送而大幅度地抖动着身子。在我看来,那种处于同一节奏中的摇曳只有脱离了人为的修正或强加给它的意义才真正地有意义。如果春风吹拂,岸上,蚕豆就会静静地开花。它们矮墩墩的躯干在隆起的滩涂等距离地排展,圆润的叶子微卷,积着一窝儿晶莹的清水。它们也懂得为自己储蓄,为明天储蓄,为内秀储蓄。它们的背后,田垄金黄,油菜花热烈妖娆,让人猛烈地感受到春天的重量……船,越开越慢……有时想,这些年年岁岁都能露一手绝活的生命,它们怎么总是选择无声?它们不像飞禽走兽,可以用超常的动作博得自船窗飞出的“惊讶”。它们静静地生长着,全然不曾焦虑生命的谢幕!
而更多时候,我被那些荒草萋萋的所在吸引。那些蓬蓬勃勃的勒勒藤、野月季……周身长满小刺,以拒人的态势蜿蜒在两岸。是不是,学会拒绝方能成其一景?就像《圣经》里的意思,天国里,孩童因纯真所以成其大。纯真即不市侩,不圆滑。那么,勒勒藤、野月季,它们是不是以长刺的方式无言地维护自尊,无言地维护着自身生命力的蜿蜒?
就这样,从鱼圻塘开往平湖的班船,在密织的河网上蜿蜒着,每天一轮回,有些孤独,但无限欢快……遗憾的是,2000年我离开前港落户新埭后,它就不再开动了。我不知道最后一班船是哪年哪月哪天以怎样的方式完成最后一次行程的,我想象不了它那时的表情。我恍惚觉得它的停开是一种误传,因为,我每天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在广袤的江南水乡和潺■如流的光阴中,它被我开着,在心里开着……
看见
站上三楼,屋子背后的浙北平原犹如经了年月的大凉席,在深冬里袒露特有的色调:草黄。那些黏在田垄的小麦呢,一律的营养不良;油菜是少见了,我们应该拥有的激动,早已学会退场,拜拜了!
只有阳光一如既往。尘埃不舞,这是冷冻的功劳,尽管沿着公路在大兴土木,排污工程壮观地向着两头延伸。空气的干净加剧了日光的坚硬,那些被照耀的枯枝败叶,寂静得发出清晰的咯咯声,风,总是不忘凑热闹,而且,特别地投机。
“啪!”这是房屋东边的那棵构树干的好事,苍老的体格逢冬即瘦,嶙峋的梢头挑着干瘪的黑果。显然,风是见不得这般炫耀的,坚决把它赶下高位,让招摇的它到冰冷的鱼塘里接受教育……
鱼塘早已废弃,芦苇不安分,汹涌着从河岸爬了进来,安营扎寨,地盘越扩越大,别说鱼不在塘,就连水,都已经失去了作浪的空间。只是北边的一截,浅,夏天种过菱,得益于人的经营,这一块还算保住了鱼塘的面子。侥幸躲过劫难,却没躲过寒冷,已经好些天了,一层厚厚的冰,改变了它的容颜。
吹落的构树球,有着桑果一样的身材,在冰面上砸不出什么名堂,只好滚往一角。这样的瞬间,划过我的张望,那轻微的“啪”声在我心里震颤,仿佛结着冰的不是身外的水,不是淡出家常话的废塘子,而是在胸腔里鼓荡的心。
皲裂的感觉占据了脑海……已经好长时间没来光顾了!读书,遐想,然后歌唱,通常绕完鱼塘,一首诗或者一篇美文差不多也就诞生,灵感的爆发,像春夏平原上葳蕤的植物,让人踏实,亢奋。回忆催人衰老,其实,昨天还清晰地印在泥路上,却偏偏这般恍若隔世,为何?
反剪双手于背,像一个沉思者迈着他稳健的脚步,开始旷野的跋涉。塘中曾经倒映的天光云影全都在心。不过,芦苇的春色只得等上一段时光,这会儿,它们正形销骨立,守着冬天的残简。忽然,芜杂的苇丛里■■有声,VlHBLdARLRTcXLcL2i/Zu1PSH95JtUV3Cn3h16WNn9I=是野鸭吧,我太了解它的动静了,在不小心趔趄的时候,吼一嗓子的时候,它准会附和,以表明自己的存在。现在它依然健在,在悄悄走动……
就像惶惑中的人,唯恐自己蹉跎了岁月,于是坚韧地没有声色地活着,甚至,还活得挺好!哎呀,在小桥里的鱼塘边,我居然闪现如此念头,几天中,就这么地无所事事。
砍发记
磨刀石是细砂的,取自岩层的底部,密实得很;端过一盆水,盆是木盆,水是山水,清洌得淡淡地散发着甜香;天光白晃晃的,洒在刀口上,发寒,就格外亮,倘使正好折了一道艳阳在眯缝的眼上,那就很有形容里常说的“白刃”感觉了。
刀照例是要磨的,蹲着,右手紧把着青■木刀柄,左手撒开成扇,往水盆里一捞,磨刀石上就滚过一瀑水帘,于是刀和石头就发出一种磨砺声,闷闷的,舒舒的,爽!
刀是弯刀,专割巴地草喂牛用。羊没有这优待,光吃不干活,福利自然被免了,就满山钻,得名山羊。磨刀不误砍柴工,时间长是长点,通常要磨完一盆水,最后,连刀背都青白一线,若不是刀弯得太夸张,那就很有理由疑惑是关公遗失的那把大刀了……实木凳子上端坐,蓝色围裙紧了脖子,打一些肥皂水,也有是用洗衣粉水的……下刀了,像剥地瓜一样利索,几乎是一个段子还没有讲完,人就站起来了,雪白的脑皮被热水一冲,肉肉的光泽顷刻活泛起来,可以蓬筚生辉了。
我小时候总觉得自己长得酷毙帅呆,始终没有彻底砍过一次发,即便是父母认为发缝里的虱子都快掉碗里了,软硬兼施,最多也就肯剃个大圆头,而我的头本身就大,很快就被安了个抗日影片里的日本侵略者“龟田”的绰号。这样我可不甘了!一直保留四方头,前面梳出“一块瓦”,刘海一边倒,走几步就甩一下,潇洒得有些飘飘然,与当时的干部模样保持高度一致。电视剧《上海滩》澎湃那几年,索性就让头发长到包住耳朵,从后面看完全是个大姑子,正面呢,都说赛“陈真”几分,天哪,那还了得,陶醉得不得了,只要醒着,不是吼“昏睡百年”,就是在挥舞拳脚……于是,砍发这门手艺没能在我的头上撑下来,而那些比我生得周正的后生,更有理由自信满满得洋气十足,长发披肩得直让艺术家也黯然。也是,年纪轻轻的,干嘛整个“蒋光头”?“砍发”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那遥远的地方不得不“寿终正寝”了!
真正有将头发砍掉的勇气是过了而立之年,用同事的俏皮话说是“为艺术献身”。单位搞辞旧迎新联欢,部门演杂剧,有一个角色需要他或她的头颅慷慨地艺术一回。我自认是一堆子里长得最对不起观众的,就自告奋勇,欣喜若狂地把一头呵护了半辈子却越护越不见起色的“秀发”斩草除根!
当时那个痛快,是不曾见一丝杂念的。只是妻子反得厉害,但她是个组织观念超强的人,知道是集体为了演出需要,就说只此一次,下不为例。节目得了个头名,有奖,也享受了吃喝,听到不少恭维,就琢磨,就顿悟,名所名,非常名,八成派头上的标新立异也很重要,敢情这奇头怪脑功不可没!就按捺不住心里的许多小九九:不是有人冠以“诗人”么,这回算是逮着机会了,就让自己一直闪烁吧;不是一直都不够e时代么,这回算是粉墨登场了,就让自己一直彩铃声声吧;不是多年生无风烟么,这回算是开端有势了,就让自己一直形象招摇吧……见我头上没有动静,妻子就火,喝令貌复俊样!心被虚荣酵化着,我哪里听得进忠言:连知丑之心也不复有。于是,这头发自然就被“砍”了个精光。坚持就是胜利,一年过去,妻子看顺眼了,有时比我还着急:“你头发又得剃了!”
只是去讲座,每次都会有学生“怜香惜玉”地齐喊:“芦叔,多长点头发!”还有就是我儿子,有时会眨巴着眼睛,拍打我的脑门子问:“爸爸,为什么你的头光光的呀?”而我呢,在出过了“风头”之后,已归于生理:发之不砍,头皮不安!砍发又不是砍头,有啥子要紧?这丑陋的头,能闪烁就尽管闪烁吧!
水奇下渚湖
出德清县城东南不远,就是江南最大的湿地公园下渚湖。相传德清是“防风古国”所在,“防风”者,乃古酋长之名也。于是便有“地裂防风国,天开下渚湖”一说。“地裂”与“天开”,强调的是自然的造化,鬼斧神工,胜景全出。
天公作美,恣肆了一夜的雨,停了。下渚湖非湖,是一片湿地,整个水域达三十六平方公里,仅次于西湖,是浙江省首家湿地公园。进得园门,视野豁然,这下渚湖的美,隐藏在密匝匝的芦苇与蜿蜒的水道里。整个湿地,就是一个庞大的水网,网住了六百多座岛屿台墩,真可谓“湖中有墩、墩中有湖、港中有汊,汊中套港”。由于正值雨季,湖面漂满绿萍,船,游荡在满湖的苍翠中,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仿佛要让每一个游人披绿戴翠,收获一船好心情。船里的人,谈兴浓烈,不时欢声荡漾,笑语飞扬。导游说,下渚湖因为“原生态”而显得与众不同,大意是这里的一切都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神韵,好比村姑的纯朴之美。导游生得一副莺歌鹂嗓,提起方圆百里内的逸闻故事如数家珍,神话传说,龟鳖鱼鸟,苔藤树草,经她的编排,就趣味无穷。讲到高兴处,她索性搁下话筒,声情并茂,抑扬顿挫,从容地调节着船里的气氛。这一分本色,与下渚湖一脉,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下渚湖是鱼虾的乐园,更是鸟的天堂。船行芦苇荡,常有珍禽伫立岸畔,以鹭为最多,白鹭、灰鹭、牛背鹭,或栖或翔,优雅而自在,惹得几人窜至船尾,举起相机,咔嚓不停,以致船体失衡,惊得舵手一通忙乱,惊起一湖鸥鹭……
到了心脏一样的湖心,众人朝着导游手指方向,见前方一座葱郁的小山上,佳木秀而繁荫,上万只白鹭安详地栖息着,几如钻石嵌入翡翠。这时候,船晃动剧烈,再没有一个人老实,都在寻找最佳角度,观赏远处那壮观的风景,恨不能将之打包。览胜悟性,突然想起唐人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此时此刻,这样的意境,在下渚湖上,诗意呈现。于是,心里又多了一分陶醉!
“寻幽下渚共驱车,苇密舟轻远酒家。小憩茶楼傍水坐,一湖烟雨一湖花。”行毕上岸,自然不肯放过品尝此地美食的机会,在湿地酒家入座,喝着特制的烘豆茶,把着渔竿,看渔舟晚归,夫妻首尾相对,男子双手操橹,女人一脚控舵,桨声■乃,咿呀而过。湖面波痕一线,深入黄昏,绵延梦里……
翠涌莫干山
探访德清,不可缺席莫干山!莫干山属天目山支脉,主峰塔山海拔七百五十八米,风景秀丽。素有“清凉世界”之美誉,被誉为“江南第一山”,与北戴河、庐山、鸡公山并称为中国四大避暑胜地。
莫干山山名,来自干将、莫邪夫妇二人铸剑于此的古代传说。早在春秋末期,干将、莫邪采山间之铜精,铸剑于山中。时冶炉不沸,妻子莫邪剪指甲、断头发,用黄土拌揉,作为人状,投之炉中。炉腾红焰锻锤成雌雄宝剑。雌号莫邪,雄称干将,合则为一,分则为二,蘸山泉,磨山石,剑锋利倍常。山中有“剑池”,池盈清冽。翠绿采天露为水,飞泻而下,终日淙淙,亘古流韵。想那干将、莫邪蛰伏瀑涧,以恒心为铁,胆勇为火,淬翠磨砺,裹挟豪气,铸就宝剑。所谓“剑池”,不及方丈,何以盛名天下,非德不以为本,清心增美,白虹倒影,演绎千古绝唱!
莫干山的美,全在一个“翠”字。漫山遍野,茂林修竹,层峦叠嶂,真可谓“布地幂天皆竹影,翻江倒海是松涛”。如果绿色是一台大戏,那么翠竹永远都是主角。深绿、浅绿、灰绿、墨绿……放眼望去,各种绿色编织的绸缎在每一座山峰绵延不绝,如梦似幻,生机盎然,昭示着生命的无限魅力。“翻身复入七人房,四首峰峦入莽苍。”恰如毛泽东所吟,莫干山的翠绿具有莽苍的气韵,翠得神奇,翠得震撼人心。上得山顶,迎面一处峭壁上,赫然刻着一个硕大的“翠”字,字高九米,绿漆勾勒,光彩夺目。人们争相留影,似要与翠永恒。
昨日游览下渚湖,归途中导游给大家指认湖边的一对“水凤凰”,一时引得全船惊呼,可我因位置不佳,错过了一饱眼福的机会。俗话说:“凤凰美,美在头和尾。”遂想那“水凤凰”该是何等惊艳,众人的“奇遇”加深了我的遗憾,带着遗憾上山,期待“山凤凰”显灵。果然不虚此行,莫干山“凤凰”遍野,无论山脊山坳,背阴向阳,它们美丽的大尾无处不在。这就是今年新生的竹子,在清风中摇曳着翠绿色的娇嫩身姿,静静凝视,那向上伸展的柔韧枝叶酷似凤凰长长的尾巴。我为这发现暗自激动,仿佛觉得满心都在涌动翠绿,荡漾着无边的翠色。
悠远湖山,秀美德清。游程虽短,但收获颇丰,无论在新市访古,还是在杨墩农庄休闲,这孟郊故里,像一本线装书,包含了无限的欣喜与憧憬……
责任编辑 林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