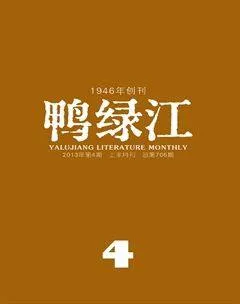青春纪事(三题)
肖克凡,天津文学院院长,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著有长篇小说《鼠年》《原址》《机器》等七部、小说集《赌者》《人间城郭》《你为谁守身如玉》等九部、散文随笔集《镜中的你和我》《我的少年王朝》等,总计八百万字。作品数次在国内获奖。其中长篇小说《机器》获中宣部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并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少年春节
公元1961年冬天,父亲从新疆回来了,他是公差给单位购买仪器的。当年他报名参加建设祖国大西北的行列离开天津,我并不记事。这是具有记忆以来我首次见到父亲。
我家住旧日租界宁夏路,日文叫须磨街。说是街其实是巷子。记得腊月三十的上午,我走出院子看到一个中年男子蹲在小街口,操着外埠口音大声说话,如今我懂了那是叫卖。
他说,他这挂炮仗打算带回雄县老家过年,可是路上遇到卡子检查肯定没收,只好卖了回家。那时我七岁却从来没有正经放过炮仗。我太小,往年家长是不给我买炮仗的。我想起今年春节不同以往,因为爸爸回来了。
我就跑去跟爸爸说外面蹲着个卖炮仗的。爸爸听罢立即走出家门。我追在后面看到他掏钱买了那一挂炮仗,然后转身递给我。
那是一挂用红纸包着的炮仗,接在手里沉甸甸的。我喜出望外如获至宝,急忙奔回家去。当天下午我坐在桌前,小心翼翼将一挂鞭炮拆成一颗颗炮仗。那时候的孩子是舍不得放鞭的。
就这样,除夕夜我家小院里响起了零星的爆竹声,那是一个七岁的男孩儿有生以来首次发出那么大响动。当时的欣喜心情,至今难以忘怀。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父亲的形象。他穿一件蓝色呢子上衣走出家门,掏出钱夹不问价钱就给我买了人生第一挂炮仗。
父亲返回新疆的第二年,我家搬到山西路居住。这里也属日租界,旧称明石街。临近过年我生病了,发烧呕吐。一年一度的春节是孩子们三百六十五天的企盼。穿新衣、吃好饭,尽情玩耍。如此大好时节我却病了,心情很是沮丧。
表哥来了,他从唐山胥各庄带来几样好吃的东西,有花生瓜子什么的。当时城市限量供应春节食品,记得每人只给二两瓜子儿。除夕夜我发热,迷迷糊糊特别希望清凉。正月初一热度稍减,外祖母端来一小盘吃食,有京糕条儿果仁什么的,还有几颗水果糖。不知何故我家竟然拥有两只褐色花斑塑料碗,平时舍不得使用。由于发烧,我想起夏季的冰棍儿,心中萌生一个极富创意的念头,固执地动手实施起来。
我将京糕条儿和果仁儿放进碗里,又剥了两颗水果糖投进去。端来一杯热水沏开,耐心等待冷却。外祖母看到我如此暴殄天物,问我做什么。我如实回答了。外祖母告诫我说,这都是好东西,你不要后悔啊。
我是年末生人。西方星座理论称这种人往往一意孤行,主观武断。我家住房是双层窗。我拉开窗子小心翼翼将塑料碗摆在外面窗台上,幻想着明天就能吃到又凉又甜的自制“冰棍儿”了。
夜里,我做了一个清凉的美梦。第二天一大早儿爬起来奔向窗前,打开窗子迎着冷风从外面取回冻成冰坨的塑料碗,准备大快朵颐。
我的美好创意惨遭失败。冰坨上落了一层灰尘,脏兮兮的。我试图去除这层灰尘,那么只能等待融化了。然而融化后我得到的是一碗浑汤。
外祖母走过来叫着我的乳名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我的春节美食全部投入这项“创意”,这很像当今炒股不惜血本的“满仓运作”。从那时候我就懂得什么叫作“全部泡汤”。屈指一算,这是四十八年前的事情了。如今回忆备感温暖。那毕竟是一个傻小子的少年春节——尽管如今我仍然很傻。
平民茶道
我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生人,住的地方是旧时天津日租界。大约九岁光景家庭变故,我只能去跟祖母一起生活。她老人家住在南市,就是早世年间人称“华界”的地方。我与祖母的住所距离玉壶春茶楼不远。民国初年玉壶春是天津出名的茶楼,坐落在南市的荣吉大街(平安大街)与大兴街的交口,为二层建筑并有临街长廓。玉壶春茶楼南边的建物大街上有华楼旧址。华楼乃是当年逊帝溥仪的舅父良揆投资兴建的娱乐场所。说是茶楼,其实还有台球房和西餐厅,后来失火烧成一座废墟。
天津不比成都有着众多市井茶馆。但只要是真正天津卫家庭,接待客人必然奉以热茶。若以清汤白水待客那是慢怠。老天津人热情好客的习性,可能源于船来车往的码头文化。
我九岁从“租界”迁居“华界”,首先接触的新鲜事物就是“水铺”。水铺是专门出售开水的店铺(当然最早也出售凉水和苇子)。水铺出售开水,似乎主要用于家庭沏茶。天津人无论春夏秋冬,清早睁眼头一件事儿就是喝茶。我祖母也是这样。因此我要说的是天津平民“茶道”。
每天清早儿,祖母便将那只白瓷茶壶刷洗干净,打开茶叶盒将一撮花茶倒在盒盖儿上,然后投入茶壶里。天津人沏茶不许用手抓茶叶,以示清洁。于是茶叶盒的盖儿便成了容器。天津人大多喝花茶也称香片。祖母将一撮子花茶投入茶壶里,然后递给我二分钱硬币说,沏茶去吧。我拎着茶壶就奔水铺了。
一般来说一个街区便有一个水铺。水铺的主要设备是一口大灶,大灶上安装着烧水的大锅。水铺的主要燃料是木屑和锯末。天津有俗话:水铺的锅盖——两拿着。一大早儿,大锅里的水尚未烧开,我将茶壶摆在锅台上等候着。据说有个别不守本分的水铺掌柜为了节约燃料,故意在锅里扣一只大碗,这样锅里泛起的气泡嘟咕嘟咕显得很大,以此冒充开水。
我沏了茶,将二分硬币放在锅台上,拎起茶壶转身快步回家。走进家门,祖母已经拉开了准备喝茶的架势,一张小桌上摆着两只茶碗(绝对不是茶杯),表情严肃地等待着我和茶壶的归来。
我将沏满香片的茶壶摆在桌上,平民的茶道便开始了。祖母亲自动手,抓起茶壶黄铜提梁儿斟满一碗热茶,然后掀起壶盖儿原封不动将这碗热茶倒回壶内,谓之“砸茶”。这种“砸一砸”的做法道理何在,至今不得而知。可能为了沏得更充分吧。多年后我在梨园史料里读到回忆花脸演员侯喜瑞先生的文章,也提到“砸茶”之说。看来,京津两地饮茶共通。
砸茶之后,我跟祖母一对一碗喝了起来。喝下一碗热茶开始吃早点,内容不外烧饼油条。早点之后祖母就去捅炉子了。
花茶沏二例儿时,味道最佳。只有第四五次续水才谓之“涮卤儿”。这是平民茶道的基本常识。涮卤儿意味着没滋没味,市俗生活不能没滋没味。
早餐后往茶壶里续水喝“第二例儿”。这时候的热水则是自家炉子烧开的。早餐后的舒适感随着茶香洋溢于胸腹,令人气定神足。这是高潮,也是平民茶道的最佳享受。祖母这时往往专心专意坐在桌前,静心品味着。花茶的香气,深深地浸透在生活深处,令人忘却油盐柴米的烦恼。
这几年我总在想,祖母为什么不等自家炉火烧得开水沏茶呢?渐渐我想明白了,祖母她等不及。早起必须喝茶——这是城市平民的日常生活。这是城市平民的茶道。祖母的“茶道”无疑告诉我,市俗生活具有多么巨大的魅力。
那时候的花茶,确实货真价实。即使普通花茶也要窨上七道花儿,因此香味持久。我去茶庄买花茶,有时售货员给包上两朵鲜茉莉花儿,以示热情厚道。如今奸商们只窨上两道花儿就敢号称高级花茶四处销售,甚至以玉兰代替茉莉,以秋茶冒充春茶。祖母若在世肯定要骂的。人心不古,居然污染了清洁的茶叶。
然而,茶永远是高雅清香的,它一如既往丰富着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
回忆“民园”
公元1963年,我从鞍山道小学转到西藏路小学读书。学校成立了小足球队。我报了名,每天清早参加跑步训练。我母亲在学生时代是体育好手,田赛径赛无所不能。她听说我参加了小足球队便看了看我的脚弓说,当运动员要有弹跳力啊。
一天,体育吴老师组织我们去看球,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民园体育场。我坐在空空旷旷的看台上,一下就喜欢上了这座体育场。那场比赛是空军小学生队对实验小学队,零比零打平。
如果我没记错,1965年我在民园看过陈家全的“百米”,手工记时。好像是全运会之前热身。当播音器报出成绩九秒九时,全场欢声雷动。后来我懂得了,那次九秒九国际田联是一定不会承认的,陈家全也不会当真,却令我终生难忘。从此我越发喜欢体育。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新体育》复刊,我立即订阅了。每逢邮递员送来杂志时,他总用异样目光看着我。当时自费订阅《新体育》那是一笔挑费啊,何况我同时还订了《光明日报》和《学习与批判》什么的。那时候我已经打篮球了,一派英气勃发的样子。我想,我的热爱体育一定与我早早就走进了民园体育场有着直接关系。马约翰先生认为体育是培养优秀公民的最有效最适当最有趣的方法,说得真好。民园体育场所包含的体育精神,影响了我的性格与气质。
我频频走进民园体育场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尤其当时天津足球队的比赛,只要能混进去我从不放过,我甚至还爬过民园大墙。记得刚果红魔、塞拉力昂、三菱重工来民园比赛,没赢过。那时的天津队,多好啊。记得金昌吉领队的朝鲜鸭绿江队访问民园,出现赛后风波,轰动全国。我敢说当时中国只有天津民园体育场出现那样的风波。那时的天津人多棒啊。这些年我多次与朋友回忆当年天津队夜战三比二反扳北京队那场比赛,山春季的一脚惊世吊射。我以为天津人津津乐道的正是“民园情结”。假若多年之后民园体育场不复存在,它肯定进入了天津人的记忆深层,终生难以磨灭。
如果我们具有城市文化意识,天津应当推选城市标志性建筑,那时候我肯定会投民园体育场一票的。因为它影响了我的生活,使我激动,使我暗暗立志,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竞技场上真正的男人。我以为,一座城市的体育场能够达到民园体育场这种影响力的,在中国并不多。如今各大城市不乏十万人体育场。然而一座体育场不光要大,还要有历史文化积淀,譬如英国的老特拉福德球场。民园体育场就是这样。它代表着我们昔日的殊荣,无疑是一笔宝贵的城市文化遗产。
责任编辑 林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