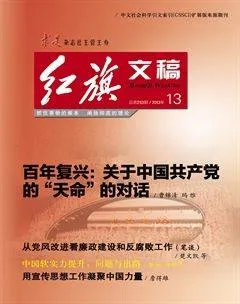道德治理的学理辨析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论述“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时,作出“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的重大工作部署。过去学术理论界很少谈论道德治理,也鲜有涉论道德治理的学术话题。因此,辨析道德治理的学理问题,以明确道德治理的思想认识基础是很有必要的。
一、何为道德治理
所谓道德治理,指的是道德承担“扬善”和“抑恶”两个方面的社会职能,用“应当——必须”和“不应当——不准”的命令方式,发挥调整社会生活和人们行为的社会作用。
对道德这种社会职能与作用的认识和把握,长期存在一种片面性的误读,以为道德只是用“应当”和“不应当”的命令方式发挥社会作用,轻视以至忽视与“应当”关联的“必须”和与“不应当”关联的“不准”的命令方式。这种误读的问题在于:“扬善”的“应当”命令缺乏“必须”的命令支持,“抑恶”的“不应当”命令缺乏“不准”的命令支持,致使道德所能发挥的社会作用很有限,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形同虚设。不难理解,当社会处于变革、适应新制度和新体制的新道德观念与规则尚未形成社会共识的特定时期,如果将道德命令方式仅归于“应当”和“不应当”,道德就难以担当应有的社会职能、难以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
道德治理的实质内涵和关键所在是“治”,贵在遏止和矫正恶行,充分发挥道德“抑恶”的社会作用。它是针对当前我国社会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而提出的社会道德建设工程。道德治理的任务和目标,是要坚决纠正以权谋私、造假欺诈、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歪风邪气,引导人们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鞭策人们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道德治理的对象和领域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凡是存在道德突出问题的部门、行业和公共生活场所,都要开展道德治理。道德治理的方法和途径,关涉道德作为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价值形态和精神活动的基本方面,不是简单地只用道德规范去说教人、说服人。总之,道德治理就是要运用道德的特殊命令方式充分发挥道德“抑恶”的社会作用。
道德治理与道德教育、道德建设,在内涵上是相互包容渗透、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从道德治理角度看,道德教育也是一种治理,“抑恶”不能离开道德教育;从道德教育角度看,道德治理本身也是一种教育,道德教育不能缺少“抑恶”。道德治理和道德教育都是道德建设的题中之义,都需要通过道德建设的各种方式和途径来展开和推进。
二、道德治理是社会道德发展进步的必要条件
为什么要有道德治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涉及道德的根源与本质。对此,历史上大体有两种学说。历史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将道德的根源与本质归结于人之外的神秘力量或人与生俱来的 “人性”。先验论的人性论关于道德根源与本质的学说大体有两种:以孔孟为代表主张“性善论”,以荀子和西方近代哲学史上的霍布斯为代表主张“性恶论”。孟子认为人之初性本善,道德是因人“扬善”的需要而发生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认为人之初性本恶,道德是因社会“抑恶”之必要而产生的:“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我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荀子·礼论》)霍布斯认为,人性本恶(自私)使得人与人之间是“狼”的关系,处于“战争”状态,所以社会必须要有“一个使所有人都敬畏的权力”,这就是政治、法律和道德。(参见霍布斯:《利维坦》,刘胜军、胡婷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之初性本无所谓善或恶,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观念上层建筑,根源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并受整个上层建筑的深刻影响。恩格斯说:“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经济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页)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关系表现出来的,利益关系总是需要调整,这种客观事实是道德生成和发展进步的内在要求,也是道德价值的功能和目标所在,道德治理因此而成为社会和人的道德发展进步的必要条件。
这里有必要特别指出,人“生而有欲”的“本性”并无善恶之分。这种“本性”既可能使人走向善,也可能使人走向恶。“人性”的善恶与否,是人后天是否接受道德教育和道德治理的结果。历史唯心主义道德本质观把“生而有欲”的“本性”归于“人性恶”,其实是无视道德职能与作用的一种误读。
由上可知,道德本来就有“抑恶”和“治恶”的职能和作用,“扬善” 和“劝善”的职能和作用是必要的,因而是“应当”的。在社会处于变革、道德领域存在突出问题需要治理的情况下,应当高度重视“抑恶” 和“治恶”,视“劝善”和“扬善”为对“抑恶”和“治恶”的必要补充。
三、道德治理的基本路径
首先,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法律是维护社会基本道义的,道德治理“抑恶”的根本宗旨也是为了维护社会基本道义。当前,我国社会道德领域的突出问题既有悖伦理也有悖法理,对此实行道德治理离不开法治。孔子说:“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而败俗,于是乎用刑矣。”([魏]王肃:《孔子家语·刑政》,王国轩、王秀梅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45页)意思是说:对经过教化和教导还不改变、听从,损害基本道义的人,就得用刑罚来惩处。这种传统思想反映了社会治理的一种客观要求。良知的培育离不开法治的强制手段,法治的实行离不开德治的良知基础,把两“治”结合起来,同时促使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理念深入人心,是实行道德治理的首选路径。
其次,创建道德制度,并将此融进社会管理的制度体系。道德制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管理制度。它是介于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之间的约束和惩戒制度,既保障道德规范得以推行、为人们普遍遵守,又为遵守法律提供广泛的制度支持。现代社会人们崇尚自由,正因如此更要尊重制度。我国目前社会生活普遍缺乏道德制度的调控,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处于可以“自由选择”的伦理窘境,难以发挥应有的道德价值。创建普遍的道德制度,使道德规范特别是那些基本的道德规范能够得到切实的推行,是道德治理的一种必然选择。
再次,把道德教育与道德治理有机统一起来,将关于道德治理的教育融进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培养和学校道德教育体系。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道德规范本也是规矩,其“方圆”的首要功用就是“抑恶”。“抑恶”离不开道德教育中的“反面教育”。当前道德领域的突出问题多属于“明知故犯”,不能说这与当事者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没有关系。行业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的道德教育,需要在实施“正面教育”的同时进行“反面教育”。道德教育的目标和内容要有关于“抑恶” 的知识和理论,道德教育的实际过程要有“抑恶”的训诫方式,从而从正反两方面促使受教育者养成尊重、遵守道德规范的敬畏心理和行为习惯。
(作者:安徽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李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