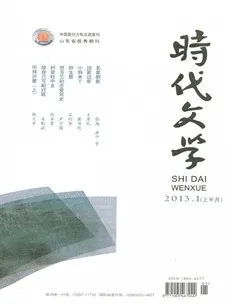东紫访谈录
问:在《梦里桃花源》中您用近乎恐怖的方式揭露了貌似繁华的社会里人吃人的悲剧,以及上层是怎样蒙蔽人们的眼睛、愚弄人们的灵魂,并对清醒者进行压制和迫害。这与鲁迅《狂人日记》“吃人”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解剖社会的黑暗,笔法犀利。同时您又是鲁迅文学院第九届高研班学员,您认为鲁迅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答:我本人真是无知无识的,没有受过专业的阅读指导,你们的阅读会深入到文学作品的内部,关注它的语言结构、故事寓意和所谓的中心思想等等。对于鲁迅的作品如《闰土》、《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我仅仅是曾经读过,他具体的对你创作上的影响是一些无法言说的东西,但它肯定是留下过一些印记的。鲁迅的深刻、尖利、正直、民族性以及那种博大的对人性的悲悯在写作过程中会影响到你。我自己的写作是摸着石头过河,开始不知道怎么写,记得一个朋友曾指着余华小说中的一段文字告诉我说,你看,小说不就是这么写的吗?我对这件事印象特别深刻,但具体到余华对我有什么影响,我还真说不上来。直到2008年在鲁院进修时,我才知道评论者是怎样来阅读你写的文章的,所以我觉得搞文学评论的人对于作家本人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他们是拿着放大镜在阅读的。
问:您前期的作品如《我被大鸟绑架》、《梦里桃花源》(原名《饥荒年间的肉》)等可以说是先锋意味的作品,后来的创作转向写实风格,请问促使您创作转向的原因是什么?
答:我原来的一些作品如《梦里桃花源》(原名《饥荒年间的肉》)、《我被大鸟绑架》、《白杨树村的老四》都是在《人民文学》发表《珍珠树上》之前的作品,带有一些先锋色彩。《珍珠树上》确是一个分界线,但我并不是去故意迎合《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这些刊物,我认为真正的先锋是源于对生命的真切体验,同时我的转折也是源于自己的生命体验,尤其是我儿子出生之后的改变。之前的作品将一些黑暗的东西挖得很深,那是出于年轻时的一种激情,把社会上的丑恶和不公充分展现出来,让那些有能力改变社会的人们有所触动。直到儿子出生以后,我意识到原来的那种写作中并没有温暖和光亮的东西,我儿子看到了会怎样呢?现代社会越来越浮躁,总是去挖掘社会的邪恶、黑暗和不公会影响到那些没有积淀的读者对社会的认知,因为语言的的魅惑力和影响和影视传媒等相比是巨大的,文学应该坚守和承担一些道义与责任,所以我觉得文字中应该有一些温暖的东西,这也是我为什么不那么先锋了,为什么不写让人看着是美丽的桃花源而实际是吃人的社会了。
问:您转向后的作品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这些大刊打开了局面,同时也获得了“人民文学奖”和“中国作家奖”。有人曾说,您是被所谓的权威刊物塑造的,您认同这种说法吗?您怎么看待市场和刊物对作家作品的影响?
答:这种说法虽然比较尖锐,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对于被刊物塑造,坦诚地说多多少少也是有的。因为你毕竟不是神仙,没有那种高度认知的特质,你会对自己的写作生发一些质疑,你能说你自己就是高明的,所有刊物就不高明吗?你的内心会希望自己的作品会被大家认可。
问: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您认为女性作家与男性相比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
答:总体来说,我觉得女性更适合写作。女性的直觉、敏感、想象和天性中的悲悯会强于男性,尤其是女性所扮演的母亲的角色也是男性体会不到的。我们能写男作家写的,但男性可能写不了女性写的。男作家更善于宏大叙事,但作品最终进入的是人的个体的生命体验。况且人的情感是共通的,与性别无关。《白猫》中展现的50岁离异男人的细腻情感会让读者意识到这是一个女作家写的,但他不能说一个男人不可能这样细腻。
问:近两年的作品中,您较多的关注女性,如《春茶》、《漏雨》、《被复习的爱情》、《赏心乐事谁家院》等作品中写女性所面对婚姻问题、情感危机。你是否在探索某种女性的情感和生存的出路?
答:我的写作是所谓的无意识写作,是没有明确计划性的,仅仅是在工作和生活之余将心里一直盘绕的人物故事写出来。作品中相对来说对女性情感关注的要多一些。比如《春茶》的人物故事也是源于生活和工作。我的好友,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女人打给我电话,她斩钉截铁地表示要出轨,而让我无语的是她并没有出轨的对象,只有出轨的决心。就像我在创作谈中所说的,她的决心实际上仅仅是她对平庸又充满矛盾的生活、对消亡的爱情、对自身沉睡的激情的愤怒。朋友哭着重新回到令她愤怒的生活和情感里继续充当好女人的角色。我就在小说里让梅云替她完成了反抗,将人物内心隐秘的疼痛、情感、秉性和现实利益结合起来写成了《春茶》。
问:您在医院工作,医务工作者的身份除了为您的写作提供一些题材之外,还有哪些方优势?
答:我觉得挺遗憾的,我虽然在医院工作但不是做临床。优势在于我工作的环境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作品中的环境和人物身份有陌生感就会有一定的吸引力。但遗憾的是到现在也没能写出一个真正的关于医院题材的作品,仅仅是背景性的。因为对医院的环境熟悉,写作时会不由自主的将人物设置在这个场景中。如当时写《穿堂风》,其中人物原型我在医院见过一面,那种“爱的伤害”的疼痛感促使我写了这个作品。谈到这,我觉得我们都需要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还是温暖的,相信活下去是必要的,相信人与人之间还是有真情的。
问:您往往会改动一些小说的标题,比如将《白杨树村的老四》改为《相互温暖》,将《我和弹弓》改为后来的《我被大鸟绑架》。您是怎么看待小说的标题问题的?
答:小说标题是很关键的,起好了可以为作品加分。我认为越简单、越笨拙的题目越好,所以我当年写了《大圆》、《春茶》等。但遗憾的是题目往往很难涵盖整篇小说的内容,除非像《战争与和平》那种宏大的标题。
问:您创作《大圆》的时候是想表达什么?
答:《大圆》是写一个孩子对世界的观察,他眼中的现实世界是由很多大大小小的圆圈组成的。我是想表达父母对这个孩子职责的缺失,虽然他智力不像常人那样,但他们将他关在家里,剥夺了孩子与社会接触的机会和认知世界的权利。
问:您作品中为什么会反复出现“堂吉诃德”的意象?
答:我觉得这与我个人的认识和意念有关。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哪怕有人像堂吉诃德一样,虽然他也许改变不了世界,但他的行动却是一个例证。所以在创作想象过程中,就会不自觉的反复用到这一意象,因为一个作家对生命的感知、对事物的认知毕竟是有限的。
问:您的小说往往采用多重故事线索,情节左右交错、时断时续而又不断裂,形成结构的张力。您是怎么把握这样的情节结构安排的?
答:这个问题太专业了,我真是说不出来。也正因为这,我特别害怕对作品的那种专业性的阅读。一部作品集中两篇作品用到的一个相同的比喻,都让我感到作品集的可怕和作者的尴尬。很抱歉无法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