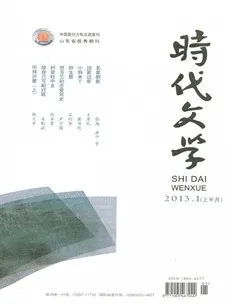时代大潮里的守望者和探寻者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急剧的变化,尤其是经济飞速发展导致城市化进程越来越明显。人们的生活条件、生存环境焕然一新,本就在历史长河中微小如沙的人们必然会受到时代大潮的冲击、席卷甚至淹没。那么人们内心是否能跟上时代的脚步,做一个合格的弄潮儿?刘玉栋作为一个七十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就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进行着创作。他是一位时代大潮里的守望者和探寻者,在文学的国度里坚守着最重要的精神,向人物内心深处探寻,试图用自己的笔,为人类的幸福寻找一条更为理想的道路。
一、 城市——时代迷茫中的疑惑与虚无
刘玉栋的作品,题材上可以分为城市和农村两类,不过作者仿佛对农村生活更为偏爱。如大多数评论所言,70年代出生于农村的青年作家刘玉栋来到济南已20余载,但都市生活并没有占据他创作的半边天,他对城市采取的是否定、怀疑的态度,在他的作品里城市是被异化和扭曲了的欲望的集合,是污垢的泥潭,人类常常在城市中迷失方向。在以往的作品中,他乡土情节依旧,对于记忆中的故乡“齐周雾村”总是带着孩提时的迷恋,常常回望和安放自己的精神寄托。然而在回首的过程中他痛心地发现中国古老的生存环境和传统文化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他看到市场经济如一阵狂风暴雨势不可挡地袭击了乡土社会的精神腹地,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开放、文明与低俗整体上融合消化但有时冲突不断,很多坚固如铁的美好品质也开始慢慢腐朽、变质,作者不由得流露出对乡村淳朴、优良传统消失的遗憾与叹息。
尽管刘玉栋对城市采取的是犹疑回避的态度,但如果统观他的创作,是可以把城市题材的作品看作急速变化世界的大背景的,而乡村题材,也可以看作所有中国人,乃至人类面临浩浩荡荡的时代冲击波如何应对和能否保留自身淳朴人性的故事。
不论何种题材,不论人生活在哪里,作品都暗含着同一主题:当生存环境由熟悉变得陌生,由顺境遭遇逆境,人类应该如何立足,人性之本又该如何坚守?正如刘玉栋所说摆在世人面前的是“寻找之苦和融入之难”。
市场经济蓬勃辉煌的发展,自然给人们生活带来诸多便利。但刘玉栋用敏锐的视角感悟到人们的生存状态呈现的仅仅是表面的虚假繁荣,背后其实是生存状态的更加恶化。正如他小说里那些热切渴望进城的农村人,愿望实现以后,是否真的有梦寐以求的快乐满足,并和谐地融入进去是一个难解的谜题。刘玉栋在《给马兰姑姑押车》一文中对此有着沉重的回答:或许“这些令人向往的事情,结果并不都是那么令人高兴”。
刘玉栋的小说,尤其是城市题材,往往在一种灰暗的色调中,传递出人与人之间情感流失、沟通贫乏、道德伦理丧失、物质与精神冲突的信息。这些都暗示了现代文明带来的负面效应。《蛇》可以看作是整个城市生活的大背景,也可以看作整个人类目前境遇的基调:一个高龄女人因为小产落下了忧郁症的病根,丈夫为了平复她的情绪带她去海边疗养院。刚去的时候女人心情愉悦,似乎忘记了失子之痛,生活有了光明的迹象。不料一个客人提醒说海边的山上有蛇,女人陡然变得神经兮兮,心中一直被蛇的阴影纠缠,直至仓皇回家。不过一直到故事结尾,也没有一条真正的蛇出现。小说就是用一条虚拟的蛇引发的话题和触发的惊悚来隐喻现代人对城市生活的惶恐不安、疑神疑鬼的复杂心绪。
而对于面包和爱情的选择,人们也同样有着深深的迷惑。《后来》里郭明的前妻选择了面包,带着儿子跟了一个玩具商。而他似乎也不再信任新女友唐棣的安定,只是浅浅的恋爱。终于在他带唐棣回故乡探视母亲时,濒临下岗的唐棣乘机推销饰品并因疲累而睡倒在别人的肩头,目睹这一幕的郭明果断地下车离去。小说没有过多描写郭明心理的纠结,却让他在一瞥中触动了深埋在内心的暗疾:妻儿为了更舒适的生活离他而去,而现在的女友也为了生活的体面疲于应对,虽然他们还没有正式结合,可轮回的迹象已有迹可循。小说开篇写到:“后来,郭明就认识了唐棣。”不过“后来”的故事没有给郭明曙光,反让他尝到了又一层的跌落。即使有无数的“后来”,对郭明来说却是重复昨日的故事。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写出了现代人生存之艰辛。为了生计有些人不得不放下自己的尊严,放弃自己的爱情,寻找物质的满足,在这种追求中,精神层面的东西慢慢消失殆尽。“后来”之后是否还是重复这种恶性循环,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现实的疲乏让人更加渴求心灵的慰藉、灵魂的呵护,刘玉栋却不动声色的把当前社会人情稀薄、爱情无法终老的悲哀展示给人们看。《向北》小说写一对准备登记结婚的恋人:“我”和刘萍在一个春天的早晨去婚姻登记处,却发现登记处早已搬迁。“我们”一路往北寻找,发现的却是一条漂浮着白色泡沫的污水沟和一片开阔的拆迁地。日常生活场景的裁剪,昭示了作者存在主义式的命意,与其说是登记目的地不明,毋宁说婚姻列车的方向盘本身就是混乱的,它指向的不是诗意和甜蜜,而是迷茫与荒唐。即使有着牢固婚姻支撑的夫妻,也还是会面临各种诱惑与背叛。《堆砌》里杨珂与田冲用仿梦的形式对两人超越伦理的情感背叛开脱,虽然这种解释那么蹩脚和不合情理,但这毕竟让他们既摆脱了各自心中的道德谴负,又化解了对杨柯妻子的精神伤害。
总之,在刘玉栋看来,城市除了会模糊人们正常的情感认知外,还处处隐伏着种种不安稳元素,在它们的觊觎之下,人们整个心灵经常处在一种迷惑茫然,不知所措的混乱躁动之中。物质和精神都无所依附的城市群体,昭示了所有人类都处在一种精神虚无的境地。
二、乡村——生存困境下的无奈转变
城市工业文明大潮一浪高过一浪,曾经淳朴的乡村社会也正遭遇着被物质化、机械化的悲哀。人类最原始的情感渐渐隐退,城市里特有的麻木、冷漠在农村上演的时候,更是给人一种彻骨的悲凉感。
刘玉栋这个有着十几年乡土经历的作家,在作品中恰到好处地运用了鲁西北大平原上那个叫做“齐周雾村”的村庄生活经验和成长记忆。这是一个普通的乡村,但她却是整个中国农民乡土生活的缩影,乡土中国在滞重的进步与落后并存的现实境况中缓慢前进。千百年来沉淀而成的伦理秩序虽然还在繁衍生息,但新的阳光正照耀在这片厚重的土地上,新鲜的血液掺杂着外部世界的精彩和潜在的细菌开始注入沉寂迟钝的农村人的生命,人类的灵魂受到欲望膨胀的考验和煎熬。在晚近的乡土题材作品如《芝麻开门》、《乡村夜》、《火色马》、《早春图》、《给你说说话》等中,刘玉栋带着温暖的同情和惋惜的无奈,书写了记忆中的故乡。
刘玉栋的写作意图非常清晰:虽然他对生之养之的精神圣土有着无限的眷恋和崇拜,但他还是勇敢地揭开了被诗性和灵光笼罩的乡土,裸露出在现代化进程威压之下,乡土之美、乡土道德必然遭逢崩散的残酷命运。不过在这些作品里,刘玉栋的叙述还是维持了自己习惯的节奏,依然选择从小处着眼,从家庭着眼,在家庭成员命运的变迁中来折射出醇正温静的乡土氛围正在消逝的现实。
正如《给你说说话》,用个人回溯性的视角对中国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内心深处的情感震颤进行了细致描绘和深入挖掘,绘就了一幅幅撼动心灵的抒情画卷,引导人们思索自身生存之难、精神裂变、道德崩溃、价值失衡的原因。一个原本美满祥和的农村大家庭,男耕女织,长幼相携,代表了人类在进入科技时代之前的那种纯朴。然而人类不断进步,现实生活不断发展,黄土地不再是被人们热情歌颂的圣母,不再是财富之源,人类的生存开始遭到威胁。此时飘在城市上空的诱人香气蛊惑了很多农村人的心智,所以很多人开始出走,闯进城市寻找新的机遇,而这或许正是一切丑闻的根源。文中的每个人物都是世人角色的典型缩影,在他们身上烙印着时代转变带来的外在压力和内在愁苦。男性,这个人类力量和勇气的象征,此刻变得如此脆弱不堪。文中的父亲,家族的顶梁柱,因躲避计划生育而被罚款,还被命运捉弄,手被砖厂的机器轧掉。此时的农村已经不似往昔,一个青壮年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普通人应有的权利和生活,现实的胁迫,外界的诱惑及周围人的怂恿,最终引导着父亲加入了盗牛团伙,终致牢狱之灾。温柔和善的女性也像男人一般挑起生活的重担。“有很长时间,我娘都为自己成为镇上第一个女牲口经纪而骄傲。”可是有谁能知道这背后的辛酸?大手的母亲和男人们一样混在牲口市里,起早贪黑,为了高价钱而和男人们争执不下。终于因为一百块的假钱被人家扒光了衣服。这里不仅仅是女性经济独立道路上充满坎坷的揭示,人们道德浅薄的谴责,更是一个劳苦大众生存尊严的困境。孩子们也不再单纯,姐姐现在总是很累的样子,大手看到的也总是“疲惫的脸和那双像蒙着塑料薄膜的眼睛”,“她一个人呆在屋子里时,就点着一根根长长的细细的黑皮烟卷。烟雾在她面前升起来。她只比我大八岁”。姐姐疲惫的脸容正是城市无序混乱生活的写照。青春活力的生命成为生活的重担的牺牲品,这是年轻一代的哀乐。曾经质朴无华的乡村爱情也开始变质。叔叔进城后遗弃了二婶导致她伤心自杀,血淋淋的上演了一场现代人的婚姻悲剧。人类的情感伦理遭到了花花世界的挑战和魅惑。
刘玉栋在童年叙述的视角中展开了历史化的回忆,中国乡村政治、经济的变动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伦理道德的嬗变在一家人起起落落的生活中留给世人评说。这样写实的情节谈不上新鲜,但在他充满瞩望然后浸透失落的叙述笔锋下,显得分外忧伤。
在《幸福的一天》中,作者更是通过菜农马全的鬼魂视角描叙了一个进城打工的当代人,尤其是当代农民在现实困境中压抑许久的委屈和辛酸。早出晚归,难得和媳妇温存,日常生活庸俗忙碌。一些简单的生活方式,不坐公交车选择出租车、到凤都楼吃早点、买新衣皮鞋、泡天河池澡堂子、到滴雨美发厅都视为一种地位、体面、尊严的行为。在这种琐屑的片段里现代人的卑微和低贱显露无遗。更深刻的是,作者不仅写出了马全一个人的“幸福性想象”生活冷冰冰的残忍,更是借马全所见所闻揭示了其他人生活严酷的一面:在城里工作的下层人物的生活处境和遭遇。擦澡工遍身疤痕累累;面对埋在煤井死亡的工友,亲人不悲哀反而为了拿到赔偿费激动与兴奋;美发厅小姐的伤疤都不经意间撕痛了一系列人的伤口,引发了一连串创伤性记忆,这些侧面展现了新世纪乡土中国转型过程中社会底层的不公正遭遇。这种时刻相伴的“创伤性记忆”无疑使灵魂出窍的马全所感受的“幸福”大打折扣。联系小说开篇马全所做的“古怪”的梦,断剑、荒野、呜咽之声、打了败仗的散兵,这些当代转型中乡土中国整体性衰败的精神喻象,与马全“虚幻梦游”中的随处可以碰触的“创伤性记忆”相互映照,达到了小说文本内在逻辑性结构的一致性。而小说的结尾竟是会飞的马全看到家中门板上躺着与自己穿戴的一样的肉身时瞬间栽倒在门板上,生前生活之重与死后生活之轻,虚幻中自身生命之欢愉与他者生命之隐痛,亡灵不能承受之轻与尸身依旧承担生命之重,既互相接续,又能对比映照,既显现出了作者高超的审美技巧和生命哲学理念,又把疲于奔命的劳苦大众形象展现的淋漓尽致。
每个人都要经历生活的艰辛与欢乐,承担个人的责任与负累,体验生命的坚韧与脆弱,尤其是这样一个外在世界看似精彩实则无奈的年代,在城市和农村都难以获得肉体安稳,精神慰藉时,我们该用何种态度对待光明和阴影?城市化又不可避免地带来阴霾和潜伏的危险,让人不仅要发问:这就是每一个从农村转入城市和城市“土著人”最终难以摆脱的宿命吗?刘玉栋有本书命名为《天黑前回家》,那么究竟是“天黑前回家”,继续在农村这块土地寻找往昔的温存,还是“义无反顾”地“离去”,在城市里跌跌撞撞地拼搏奋斗?这也是个难以回答的命题,所以作者在童年乡土叙事的真醇和现实乡土境遇里的痛感下的矛盾是必然的。而这些矛盾在其作品中不同面貌不同性格的人身上也有所流露。
《芝麻开门》中奶奶在祖屋被迫典当、搬离故土之际,宁愿割弃亲情、放弃天伦之乐,也要守着土地直至猝死。她代表了老一辈们对于土地即旧有生活习惯的固守和坚持。虽有些固执,但那是一种令人心酸的执着,显示了人心和人性的丰厚。《火化》中的连根爷爷认为新兴的火化政策让人不能入土为安,便以死抗争这种恐惧。他对待新生活就像对待新生事物那般惶恐,小说从一个极小的视角切入,透视出了守土者眷顾土地的赤子之爱。那么年轻一辈的人,面临分岔路,该何去何从?像《年日如草》里的曹大屯一直梦想有城镇户口,可一旦他真正脱离了“土地”的根成为飘荡在城市的“草”,遭遇各种挫折终于适应繁华生活的同时也消耗掉了纯真的质朴,被世俗同化。在“文明”的进程中,盲目的城市化把人固有的善良、诚实、同情、怜悯等美好本质都打磨掉了,徒留邪恶、欺诈的另一面。难道必须牺牲本色来迎合世俗,改变自身最美好的东西才能顺应瞬息万变的环境,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弄潮儿?我想这并不是作者的本意。
虽然刘玉栋本人未给出明确的答案,但他还是把自己的态度寄托在了对某些人物的赞美和肯定中。正如他所说,一个智慧的人,不仅能看到事物本身的光明和阴影,还能在正确认识光明的同时,勇于面对阴影。《芝麻开门》中的刘天真,为了子女呕心沥血,生活回报他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的变故——母亲和妻子死亡、长子精神分裂,女儿离家出走,然而在这些毁灭的希望面前,他没有倒下。相反,他就像《活着》里的福贵那般,依旧保持平静宽厚的胸怀,坚毅地生活下去。《火色马》中的妻子,忍受亡夫的彻骨疼痛,还要拉扯两个孩子,应对菜贩的刁难。生活重担之下,她并没有绝望和退缩,而是让伟岸的丈夫不断地在心中复活成一匹火色马,激励着自己顽强面对,勇敢的承担起整个家庭生活的重压。在残酷无情的人生长河里,人类应该像那匹火色马一样,坦然接受磨砺和挫折,用熊熊的生命力表达人之顽强。《葬马头》中背负历史问题的瘸子刘长贵,更是承受着来自乡村社会中的伦理歧视,但他在一匹残疾的滚蹄子马身上找到了生存的勇气和心灵的慰藉,虽然人畜异类,但相似的命运成为彼此默契和和谐的纽带。所以在马死后,他远离吃马肉的全村人抱着马头来到村外,进行着自己内心的祭奠,那是对苦难人生中另一个相濡以沫心灵抚慰的纪念。《干燥的季节》中的王喜祥面对村长之子刘全的猖狂和霸气,在饱受了一番人格的凌辱之后,终于举起手中的刀,以一种十分夸张的磨刀方式向众人展示自己的复仇意愿,希冀借此挽回在强权势力盘压下失去的尊严。
在这些人看似夸张怪诞的宣泄方式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执着于生的顽强抗争,一种不屈于命的反抗绝望之力。《我们分到了土地》之中,爷爷虽然因为没有分到好的土地而遗憾死去,但在孩子面前还是保持坐着的姿势,把坚毅的背影留给了后代,告诉他们在困难面前不能脆弱,即使毁灭也应保持自尊。刘玉栋在对乡村生活的真实描摹和对人性洞若观火的体察中,表达了对“沉默的大多数”民众的深刻同情和人文关怀。他也总是能够在这些苦涩的生存际遇中发现许多可贵的人性品质,并赋予它们以特有的温情之光,把自己应对时代浪潮的态度透过这些刚毅之躯深切的传达给读者,让人们在迷茫的路口不至于走进黑暗,看不到光明。
三、温情脉脉的力量与局限
当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物质财富的积累正潜移默化的改变文学的状况。当物成为这个时代的价值基础的时候,人的内心却是相对匮乏的。人人惶惑不安、冷漠浮躁,渴望沟通却又怯于给予,盼望理解又懒于交流。刘玉栋始终保持责任性,坚守作家的道德底线,不看重事功,而是始终不渝地思考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关注着人类灵魂世界的基本走向。他用自己的笔,描写命运无常,讲述处在各种变化和可能性之中的人情世故,关注在这变化巨浪中手足无措,难以应对的疲惫人群,更加侧重描写精神和物质中双重沦陷的边缘人物。
刘玉栋在农村出生长大,仁厚的土地和淳朴的乡情赋予了他温柔敦厚的性格,他把这种对故乡的浓浓情感融入到了作品当中,始终秉着诚挚、细腻、仁爱的态度进行创作。也正是这种的成长经历,让他更加关注底层人民和弱势群体的生活,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他没有迎合商业化趣味,笔墨不着重商界的尔虞我诈、官场的风云变幻,而是默默的坚守淳朴的文学特色,关注底层人民和弱势群体的生活,在琐碎却饱含生命情态的故事中真切的临摹出芸芸众生的凡俗,寻常百姓的甘苦。他的作品没有凌厉的气势,正因为他知道时代浪尖上的旅客需要温柔的呵护,需要静静的抚慰,所以在刻画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时,没有拘囿于对外在苦难的详尽描述,而是从人性和情感出发,试图把“温情”作为个体克服生存苦难、宽慰灵魂的另一条途径,他把所有的反抗和爆发力内化,让人物用自我承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也试图在塑造齐周雾村一系列形象中给人们设置一所精神家园,用这所乌托邦给人们带来心灵上的慰藉,唤起人们遥远的沉寂许久的柔软温情,洗去浮尘,裸露原本的纯真善良。他的很多小说最终都是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化解了人生中的种种缺憾,使人性的美好得到艺术的张扬,这也体现了作者诚挚、细腻、仁爱的创作态度与独特的审美原则。比如《葬马头》中的刘长贵在面对他人的嘲笑和欺辱时却依然能够保持乐观的心态,他健全的人格散发出的人性光辉让人感动;《幸福的一天》中一个底层人民对城市幸福生活的向往能让读者品苦生情,体会到绝望之后的希望,燃起人性不屈的力量。还有《我们分到了土地》中的爷爷刘小鸥、《干燥的季节》中的王喜祥、《公鸡的寓言》里的陈大宝,他们都是现实生存中完全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但刘玉栋却以内化的温情为我们展示了柔弱者的生存意志和精神秉赋,让我们看到了温情背后的张力。他的小说宛如润物无声的绵绵春雨,点点滴滴都浸润到人的心底,让那些被现实人生重负挤压得扭曲、干枯、冷漠、丑陋的心灵重新变得健康、滋润、柔和、美丽,同时也让作品在批判现实的同时有了积极的建构作用。
刘玉栋通过这种略带温情的疼痛,把时代发展中乡土中国的历史进程、情感记忆,以及现代化转型中的焦灼、尴尬和无奈表达出来。看到了人类生存之艰辛,情感之脆弱,并透过温情的话语,蕴藏强劲的道德律令,折射明确的伦理准则。这正是温情脉脉的力量所在,但正因为有时过于强调叙事的温情基调,令他的语言缺少了某些穿透力,笔触少了些历史厚重感。作者很多作品描写了人物周遭环境的变化,城市化的大趋势,也写到了城市化不仅仅是高楼林立,农民进城,商业成熟,应该注重人内心的建设,但是作者对于导致时代巨变中人性犹疑甚至黯淡的因素不够深入,好像有意回避了一些激烈的东西,只能在读者思绪里隐隐约约地点到我们民族心理和文化传统面临和遭遇的戗害。刘玉栋对于自己的记忆还是有所保留,没有不管不顾地颠覆自己的经历,只是点到为止罢了。能否用一种审美的角度来呈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巨大历史变迁,思考这一时代这一代人甚或几代人的命运,进一步揭露民族苦难的精神疾病,从而写出揭示时代真相的作品,足够的精神穿透力来凿破生活的幕墙去发现和展示那些更为深刻、更为潜在的生命情态,在叙事上也应超越经验甚至理念层面,对人的存在性给予更为深远的探索和表达。这是需要作者努力的。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