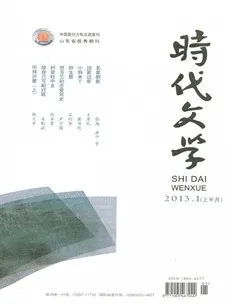马尔克斯的调子
在一定程度上,小说就是讲故事,大概多数人都会同意这种说法。同时我们也知道,小说又不只是讲故事。在故事与小说之间,似乎还有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距离。好的小说家首先应该是故事高手,但故事篓子未必是够格的小说家。阿凡提的故事即便再精彩,也无法称其为小说。伊索寓言即便充满智慧,也还是些小故事。再比如,明末清初山东安丘(今广饶)有一秀才邱二斋,相传他口才极好,擅讲鬼狐神怪,然而他只是在当地留下了一些逸闻趣事,反倒是他的好友蒲松龄将那些鬼狐故事写成了传世名著《聊斋志异》。也许,蒲松龄和邱二斋的区别就在于,他不再是一个贩售故事的说书人,而是一个创设故事的小说家。作为小说家的蒲松龄虽是公然地制假售假,写出的尽是些绝无可能之事,但是我们不会批评他的小说太假,反而会心甘情愿地沉醉在他假设的故事圈套中,对所谓狐怪花妖牛鬼蛇神视信以为真。然而现在一些直写“现实”的作品,却又常给人不真实的感觉——作者分明是在刻意地编故事,而不是自觉地写小说。
一般来说,以“现实”为模版的小说只要严格地遵循现实就够了,它不要作家太费周折地去自圆其说,比如《红与黑》、《包法利夫人》、《阿Q正传》这一类作品,只要情理上说得过去,大概不会有人吹毛求疵地对阿Q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这类小说让马尔克斯来看或许可称为“新闻式的文学”—如此,作家的任务就是用小说的形式虚构一种事实。然而现代小说往往并不满足于描摹事实,它还要突破事实的限制寻求一种言说的自由,从而尽可能地接近莫言所称的“朦胧地带”。常言道:画鬼容易,画犬马难。对作家而言,有时候虚构确比写实容易。所谓驰骋想象,天马行空,好像一经进入虚化状态,就可以随心所欲,不受任何约束了。不过事实上,任何虚构最终都是写实,不管你怎样夸张变形,怎样变幻时空,其目的仍不外乎传达一种真相—一种能与读者达成默契的真相。所以,我们可能都会讲一个有想象力的故事,但未必能写好一篇有想象力的小说。像后羿射日、女娲补天这样的神话故事,如果有人非要信以为真,就要对后羿的臂力、女娲的臂长给以合理的解释,否则这样的故事就无法成立。再如,在民间传说或童话故事里,梁山伯和祝英台可以变成蝴蝶,狼外婆能把小红帽一口吞下肚子,匹诺曹一说谎话鼻子就会变长,这一类有悖于现实的情节只有放在相应的故事里才是成立的,而且是毫不含糊不容置疑的成立,这种不讲理的成立往往是经不起推敲的破绽,但恰恰确保了故事的圆满。这种不讲理的逻辑便是故事的逻辑,只要故事需要,你可以把一只苍蝇变成王子,也可以让一个人长出三头六臂,前提只是故事需要。现在的一些小说之所以让人不满,其症结亦在于此:它所写的,只是一类自欺欺人的故事,它只是遵循了故事的逻辑制造了精彩的假相。
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说中称自己为讲故事的人,但是他所说的讲故事,又非纯然地“说书”,他认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所以莫言对小说的要求是“发端于事件但超越事件”。而要达到这个目的,除了“必须虚构,必须想象”,还要找到讲故事的“正确方法”。莫言的小说总是讲究“方法”的,因此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有不可复制的独特性,同时,又能以这种独特性直指他所看重的“朦胧地带”。尽管莫言以《生死疲劳》为例说明了他找到的“方法”,但“六道轮回”这个方法恐怕不会有人再用第二次。一个作家要想写出不同于凡俗的作品,就必须发明属于自己的方法。像曹雪芹、卡夫卡、乔伊斯、萧红、卡尔维诺、罗伯·格里耶,应该都是有“发明”的作家,他们不光发明了自己的故事,还发明了讲述故事的方法。
马尔克斯以“魔幻现实”著称,但是他却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写的也是他所认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所以,他说作家面临的问题是“可信性”,作家的职责便是使其所写的东西变得可信。魔幻与可信,似乎是两个极端,马尔克斯却能把它们完美地统一起来,这当然需要一种正确的方法—马尔克斯称之为“正确的调子”,即最终用在《百年孤独》中的那种调子。马尔克斯采用的是他的祖母过去讲故事的方式:“她讲的那种东西听起来是超自然的,是奇幻的,但是她用十足的自然性来讲述。”所以,马尔克斯并不是信马由缰不加节制地魔幻,而是有板有眼地将每一个细节都纳入现实,他的小说如此奇幻却不乏“新闻的品质”。比如,他在写到俏姑娘蕾梅苔丝升天这个插曲时,曾经花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让它变得可信的办法,直到后来看到有人晾的床单被风吹走,他才受到启发:让俏姑娘拽着床单飞走了。要让读者相信,自己先去相信。或许这也是把小说写好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所以,小说家最终要遵循小说的逻辑,他必须让自己的故事具备“合法性”。即便像卡夫卡的《变形记》这样的准寓言小说,也不是说变就变的,葛利高里之所以变成大甲虫,不只因为他把人的身份丢失了,更重要的是他要以大甲虫的形象承载卡夫卡的自己的故事。卡夫卡的作品充满荒诞,但他一直试图把荒诞写成可以信的现实。
本期新势力发表的三篇小说,应该说都有出色的想象力。唐女的《神书〈得语录〉》写了由一本“神书”引出的奇人异事,虽其故事离奇,却有令有信服的合理性,从这个小说本身,倒可以让我们看出语言的力量:有时候不是我们不会言说,而是我们的书写未能触及人心。郭帅虽还是一位在读研究生,但是他的小说已显出自觉的文本意识。《遗照》通篇基本以对话构成,读来并不刻板单调,在二奶奶前后不搭、自相矛盾的讲述中,历史和现实叠加交错,显示出别样的反讽意味。《简写康叔往事》写了康叔异样的一生—虽他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特异功能,仍要像常人一样接受无常的命运。
可以说,唐女和郭帅都在小说中找到了自己的“方法”—或说“调子”,他们的小说由此拥有了值得赏誉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