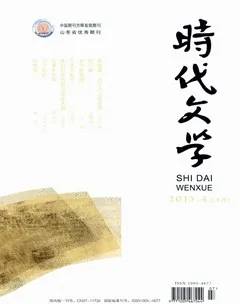地窝子·戈壁红柳·绿洲白杨
摘 要:兵团题材电视连续剧《戈壁母亲》以莽莽大戈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为创作背景,刻画了一个胸怀宽广、善良、坚韧、豁达、乐观、自立自强的“戈壁母亲”形象。本文以新疆兵团特有的意象:地窝子、戈壁红柳、绿洲白杨来分别诠释她的女性的三个身份:母亲、妻子、女人,使其成为一种精神象征般的存在。
关键词:戈壁母亲;母性;妻性;女性
影视剧中的母亲形象,一直是文艺工作者讴歌的对象。人们对于母亲的敬仰是发自内心的。在中外影视艺术长廊上,令人铭记难忘的母亲有很多。2007年,一部反映中国西部屯垦戍边伟大创举的30集电视连续剧《戈壁母亲》在荧屏母亲形象长廊上给我们绘制了一幅具有兵团革命精神的母亲形象。在这部作品里,刘月季这个“戈壁母亲”除了具有中国传统优秀母亲的美德外,更突出的是她深深地打上了兵团烙印,她是“献了青春献子孙”的无数支边兵团母亲的一个缩影。地窝子、戈壁红柳、绿洲白杨构成了戈壁母亲刘月季的典型意象特征,与粗犷苍凉的时代氛围和豪迈激荡的人物情感相辅相成。
一、地窝子:母性的温馨
在《戈壁母亲》中,“地窝子”作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战士生存的环境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地窝子”是兵团特有的简陋的“家”。1949年,王震将军率领三五九旅促成了新疆的和平解放后,为保卫边疆,绝大多数官兵就地转业,成为不戴领章帽徽的垦荒大军,驻守在渺无人烟的戈壁荒滩。刚解放时的新疆,满目疮痍、遍地贫困,到处都是戈壁,走几十公里看不到一个房子。军用帐篷既不抗暑耐寒又常被大风掀起,无奈之下,战士们就想到了挖地窝子的土办法。他们在地面以下挖一个约一米深的坑,形状四方,面积约两三米,四周用土坯或砖瓦垒起约半米的矮墙,顶上放几根椽子,再搭上树枝编成的筏子,最后用草叶、泥巴盖顶,1家就建好了。地窝子虽简陋,但在当时却可以抵御新疆沙漠化地区常见的风沙,并且冬暖夏凉。可以说,地窝子给了当时的兵团建设者一个温暖的栖息之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电视剧《戈壁母亲》的母亲刘月季就像戈壁滩上的地窝子一样温馨,在冬天,她遮挡风雪,在夏季似火的骄阳下,她又能提供荫凉。谁有了委屈尽可以在她这里倾诉,谁遭到厄运都可以到她这里避难。这种大地一样的地窝子母爱是一种朴实的母爱,她让所有人都感到亲切和温暖,体现了一位母亲对身边所有人的宽容和接纳。威廉·福克纳说过:“人类之所以永存,不在于万物之中唯有他可以连绵不绝地发出声音,而在于他有灵魂,有一种同情、奉献和忍耐的精神。2”《戈壁母亲》里把母亲与地窝子意象联系起来,让观众从这个人物身上看到了地窝子的精神和力量,让人想起家的温暖、亲情的可贵与爱的意义。于是刘月季的形象就具有了多重意味,她既是一个普通母亲的形象,又是大地母亲、祖国母亲的一个隐喻与象征。
我们看到,刘月季首先是一个普通的母亲。作为三个孩子的妈妈,她要保护自己的孩子。可以说,这部剧里,孩子是一切故事发生的根源。为了孩子,她千里迢迢从山东老家赶往新疆军垦区,一路千辛万苦,目的就是要找到孩子的父亲,只是出于一种最朴实不过的理由“孩子不能没有爹,我不能离开孩子”。 在遭遇和丈夫钟框民离婚后,其慈母之心还见之于她坚持孩子既不能没有爹,也不能没有娘,因此她在兵团留下来当了伙夫。只要能让钟匡民这个爹能认孩子,一切她都可以承受。她留下来一直陪伴在孩子的身边,关注着他们的成长,在道义与规定允许下,最大限度地保护着孩子们。
其次,刘月季具有地窝子般的母性之光,还在于让钟匡民“长大”。 刘月季在年龄上比钟匡民大六岁,可以说,她是钟匡民的精神母亲。在刘月季的精神哺育下,钟匡民从只懂得打仗慢慢意识到自己应该怎样做爹,他懂得了人不仅要工作,还要关爱,因此他能够乘长途汽车去接妻子小孟,上山为独守哨所的儿子钟槐做两顿饭。故事结尾,当刘月季病重需要做手术时,只有长大了的钟匡民记住了她的生日。可以说,电视剧《戈壁母亲》中的刘月季以地窝子般博大而宽厚的胸怀,宽容了钟框民的“离婚”,并使钟匡民成长起来。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刘月季从一个普通的农村母亲成长为兵团几代人崇敬爱戴的伟大母亲。当传统意义的“小家”解体,刘月季将集体这个“大家”当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经营和珍惜,由此,刘月季的母亲形象完成了从“钟家的人”到“公家的人”的跨越,成为“戈壁母亲”。在电视剧中,兵团上上下下各种人物都曾受到她的恩惠。在困难时期,她照顾着钟匡民新娶的妻子孟苇婷,在艰难岁月,她照顾着钟匡民的战友郭文云和部下王朝刚,还有郭文云的对象向彩菊,工程师程世昌,卫生员小郑等等。兵团的这些人都得到她的关心与帮助,都为她的宽容,为她的好心肠所感动,都渐渐地把她当作贴心人。在团场,谁家的事她都操持,团长的婚事、老程因为阶级政策不能父女相认、王朝刚做错事,都是她去一一“解扣”。曾几何时,这个默默无闻一头扎进工作,一心照顾他人的刘月季,已经成了人们遇到困难时的主心骨,她所管理的机关食堂,也成了人们诉说内心委屈,让人感受到温暖的“家”。她是大家的母亲,是一个“戈壁母亲”。
可以看到,《戈壁母亲》中的母亲不是一个单纯的普通的母亲,从片名就可以看出,它讲述的是茫茫戈壁这块神奇土地上以刘月季为代表的“母亲”, 像地窝子一样具有宽广与深邃胸怀的“戈壁母亲”形象, 在她身上,集朴实、善良、坚韧、豁达、乐观、热情这些优秀的品质于一身。我们在这个“戈壁母亲”身上仿佛看到了一个大地母亲的女神的影子,事实上,《戈壁母亲》的导演陈好放说过,“刘月季要像高尔基的《母亲》,表现那种像天空一样的爱,能爱自己的孩子,同时也能爱别人的孩子,这样的母亲真的就像一个神一样,这个母亲的形象,是那个火红年代里的一个丰碑。”3
二、戈壁红柳:妻性的智慧
红柳是北方常见的一种灌木植物,枝干是浅绿色的,干了就会变成红色的,花儿是红色的,叶子不是很绿,绿中带着些粉色或灰色。在新疆广袤的戈壁滩上,到处能看到她的身影。在电视剧《戈壁母亲》中,我们看到,在沙滩上、水渠边、道路旁,一簇簇、一丛丛红柳你推我、我搡你,挨挨挤挤地生长着。她能耐寂寞、不慕虚荣、无论富贵、无论贫瘠、无论涝洼、无论干旱,随处都有,默默无闻地、深深沉沉地生长着。我们看到,在电视剧中,当戈壁滩上的大风暴袭来时,狂风肆虐,石走沙飞,直刮得遮天蔽日,天昏地暗,就在这可怕的环境下,沙丘下的红柳,却没有被风暴吓倒。她们把根扎得更深,把触须伸得更长。她们把被流沙掩埋的枝干变成根须,再从沙层的表面冒出来,伸出一丛丛细枝,去接受阳光雨露的滋润。我们看到,她们顽强地开出淡红色的小花,向着太阳微笑。大风暴一次又一次地袭击,红柳的根却越扎越深,花儿也开得一次比一次更鲜艳、美丽。她们在戈壁上顽强地昂扬地生长着,那盛开的红柳花绽放出的生命的色彩,在荒无人烟的沙漠中异常美。清朝大学士纪晓岚流放西北时曾赞美红柳:“依依红柳满滩沙,颜色何曾似絳霞。”矛盾先生更把新疆低矮的红柳比作树中的“奇女子”。
刘月季就是这样一个普通而特殊的奇女人。全剧从一个风雨交加之日,她接到丈夫的一封要求离婚的家书开始。作为一个朴实、贤慧的农村妇女,刘月季为包办婚姻的丈夫钟匡民上养老下养小,无怨无悔16年已属难得;而16年后丈夫有了消息,却是一封要求离婚的家书。“离婚”这个现实,对一个“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的农村妇女来说可谓是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刘月季的智慧和理智使她从个人的屈辱中挣脱出来,少妇所有的思念、期盼、依靠,一夜之间化为母亲的责任。她带着两个儿子和途中捡的女儿千里寻夫到新疆,找到身为军官的丈夫。当看到丈夫对她已没有感情时,她没有纠缠,通情达理地主动向丈夫提出离婚。一句“当不成夫妻,何必还担着这个名份”的话,化繁为简,汪洋大义中蕴含坚强自持。刘月季主动与钟匡民结束了长达十六年的婚姻关系。
刘月季作为钟匡民的妻子身份就这样结束了,她怎么办?她的孩子怎么办?如何生活下去?为了维护孩子与爹的关系,刘月季跟随着兵团挺进了大西北,成为第一代拓荒者中的一员。她要像一颗戈壁红柳一样顽强、坚韧地生存下来。
刘月季在兵团这个大家庭里生存下来,更重要的是情感的处理,这是比艰苦的自然环境更大的考验。我们看到,在《戈壁母亲》中,刘月季并没有沉溺在一般的情感争斗与恩怨中,而是用她的智慧化解了生活中的诸多矛盾。其实,从新婚第一夜起,刘月季就爱上了钟匡民这个男人,但她知道钟匡民并不爱她。因此,刘月季的一生始终把对钟匡民的爱埋藏在心底,并转化为巨大的能量,默默地帮助这个开始讨厌她,后来敬重她的男人,从容地将年少的爱情转化为宽容的爱。钟匡民离婚后有了新的生活,与相爱的孟苇婷结婚。当两个儿子为母亲被父亲抛弃鸣不平而大闹父亲的婚礼现场、给孟苇婷难堪时,刘月季却亲临钟匡民的婚礼为他们解围,并用尽一切办法让孩子们了解钟匡民,同时也唤起钟匡民作为父亲的责任和情感。刘月季不计个人的委屈,真诚帮助前夫钟匡民年轻貌美的新妻孟苇婷,一次次为她雪中送炭,使这对感情上的仇敌,有了姐妹般的亲情。在孟苇婷去世后,她又照料起前夫后妻的孩子钟桃、孟少凡。当钟匡民对她越来越敬佩,很希望她能住到自己身边来时,刘月季却自尊地认识到:“他在困难需要帮衬时,觉得你有用;可当他日子顺溜了,你再戳在他跟前,他就会嫌弃你,你就是个多余的人。”自爱的刘月季毅然选择了离去,并说:“你需要我做的事我会去做,但我刘月季决不会住进你家,不会再去丢那个脸的!”她对钟桃说过:“你妈妈在世时,娘去住两天没关系,但现在娘去住,人家会有闲话的。”这就是一个普通女人的自尊与自重。钟匡民也与她建立了超越于爱情之上的,如姐弟、如同志、如挚友般的深厚感情。
最终,刘月季以红柳般的智慧在兵团扎下了根,其在传统和现代的交汇点上升华出一种新的伦理和新的道德风范。她是一个奇女子。
三、绿洲白杨:女性的言说
《戈壁母亲》中刘月季的身份不仅是一个母亲,一个妻子,更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女性而存在。她从一名普通的山东农村妇女,历经几十年风风雨雨,成长为一名军垦战士,成为绿洲里一株挺立的白杨,以她自强、自立,深明大义,不屈不挠的精神书写了一个崭新的女性形象。
绿洲白杨,在新疆的一种最普通的树。白杨树出身寒微,有草的地方,就有白杨树的影子。有黄土的地方,就有她的生存。她不追逐雨水不贪恋阳光,只要能够在哪怕板结的土地上,给一点水分,白杨树的一截枝条就会生根、抽芽。她也不需要人去施肥,也不需要像娇嫩的草坪那样去浇灌,她从来不对生长的土地说不。白杨树的性情是平民化的,但却是最讲究生存质量的。土壤里还透着冰碴,春风中还夹着寒意,她的枝头已经冒出翠绿的嫩芽,在沉重的压力下,她的每一片嫩芽,每一片叶子都是努力向上的,而绝不弯腰乞求,更没有媚俗的面孔。秋风里,虽然脱尽了叶子,单薄的枝条依然透着精气,枝干向上,高昂着头。严冬里,她迎着刀霜雪剑,依然伫立在寒冷的黄土地,枝枝傲骨,树树无字,树树有声。对于荒寒贫困的黄土地而言,她是一个伟岸的大丈夫。
在《戈壁母亲》中,我们看到,刘月季人生的起点并不高,她是被烙上了浓重的封建礼教的印记的。她原本是山东穷苦农家的女儿,身不由己地被陷于一桩包办婚姻而进了钟家的门,婚后,比她小六岁的丈夫钟匡民一直拒绝和她圆房。因公爹的哀求,刘月季不得不给钟匡民下跪说:“看在爹的份上,你就让我给你生个娃吧。不会生娃的女人谁都看不起!”可以说,此时的刘月季只是一个旧时代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并没有独立的人格。但当包办婚姻关系解除后,反而促成了她女性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觉醒。找到钟匡民后,她主动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在兵团这个火热的战斗队伍和大家庭中,刘月季接受了革命精神的洗礼,唤醒了独立的人格,思想上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在兵团,一个新的世界在她眼前打开。剧中,我们看到从小农经济条件下走出来的农村妇女刘月季,来到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人民解放军大集体中。刘月季看到了一群干大事业有大志向的铁铮铮的汉子,他们脱下军装,扛起锄头,向着沉睡多年的茫茫戈壁进军。她亲眼见到了这些钢筋铁骨的英雄汉(她的前夫钟匡民就是这群人的代表)怎样没昼没夜、不畏艰苦地奋战,使荒凉的戈壁滩变成这样富饶的地方。她马上被这个大事业、被这群人吸引,不止一次地感叹过:如果自己早一些参加革命那该多好。人民军队的无私奉献精神对她的影响,开阔了她的眼界和胸襟,提高了她的思想境界。时代的营养很快注射到这位母亲的身上,刘月季积极参加那些悲壮的进军戈壁、抗洪抢险、开荒等活动。她的身上孕育了时代的新质,与当初那个善良、勤劳、明事理的农妇相比,她的生活有了新的目标,她的爱憎是非更加鲜明,温情中又添了几分果决与敢作敢当的豪气。这一切与兵团这个历史环境十分和谐,也因此她很快成为这个革命大家庭中的一位大姐,成为戈壁滩上一位有觉悟的革命母亲。
故事的最后、前夫钟匡民衷心地称赞刘月季是自己“平生所见过胸怀最宽广的女人”,但刘月季坚决拒绝了钟匡民请她去他家里住的请求。因为,她早已经融入了兵团这个大家庭,成为了一个具有独立主体意识的人。她在“组织(兵团)”里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不需要依附于任何男性。全剧的最后一个镜头:在鲜艳的党旗下,刘月季坚定的神情,含泪的双眼,紧握拳头,宣誓入党,片尾曲响起……至此,本剧已完成了一个有独立人格的、有尊严的女性形象的塑造。刘月季从一个身披封建传统枷锁的农村妇女成长为一名新时代的独立女性,成长为民族先锋队里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这是最值得赞美的人生轨迹和精神之旅。自此,刘月季的生命历程、生命价值和意义被完整地展示给观众,一颗绿洲白杨傲然挺立于观众心中。
刘月季,这个阅遍沧桑、“没有传奇,只有人生”的戈壁母亲,以她的女性的三个身份:母亲、妻子、女人的兵团式的诠释,凝炼成一部纪念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创业英雄们的史诗性作品。在兵团半个多世纪的创业历程中,像刘月季一样的伟大母亲,何止千万? “我们兵团是一个由五湖四海的优秀中华儿女组成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组建初期,像刘月季一样‘千里寻夫’的山东大妈数不尽数,而在兵团这个大家庭里,更有不计其数的山东大妈、江苏大嫂、湖南妹子,完成了她们从农村妇女到军垦战士的转化。正因为她们来自五湖四海,兵团的母亲们比别的地域的母亲多了些人情味,多了一些大度,多了几分宽容,她们与屯垦戍边的战士们一同把屯垦戍边的事业发展壮大到今天的规模”。4可以说,刘月季这个戈壁母亲的命运与当代在新疆的250 多万兵团军垦人甘苦与共,与我们年轻共和国半个世纪风风雨雨的历程休戚相关、交融无间。此时的刘月季已经超越了个人,而作为一种戈壁母亲的精神象征。刘月季形象的概括意义在这里,刘月季形象的美学价值也在这里。
参考文献:
[1]参见“互动百科”, http://www.baike.com/wiki/%E5%9C%B0%E7%AA%9D%E5%AD%90。
[2]威廉·福克纳:《人类的精神》,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福克纳获奖时发表的著名演说。
[3] 刘玮,专访刘佳、巫刚:“《戈壁母亲》不是苦情戏”,新京报文化,2007,12,12(文化新闻版)。
[4] 《我的根在兵团——《戈壁母亲》编剧韩天航访谈录》,《兵团建设》,2008年第1期,P5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当代中国影视作品中的新疆形象研究”(12XJJCZH002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新疆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