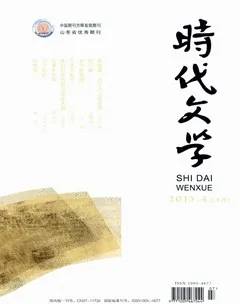评《我爱比尔》中的叙事策略
摘 要:在小说《我爱比尔》中,王安忆通过不同的叙述策略成功地表现了主人公阿三因为追求异国恋情而堕落这一主题。她使用倒叙增加了小说的悬念,插叙控制了小说的节奏,第三人称叙述,多视角地呈现出主要人物的心理活动。标题中,“我” 的使用,混淆了主人公阿三和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界限,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
关键词:《我爱比尔》;叙述时间;叙述视角
小说的主题
王安忆是中国当代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家,她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而且不断变更小说格局和叙述策略。本文着重讨论她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创作的上海故事小说《我爱比尔》的叙述策略,来揭示作者如何成功地表现主人公阿三因为追求异国恋情而堕落这一主题的。小说中的主人公阿三是一位平凡而又特别的上海女性,她曾经就读于上海某师范大学艺术系。她的爱恋和堕落的成长经历,反映了上海生活的一个侧面, 上海的崇洋媚外的一面,以及富有势利气的一面。王安忆敏锐地捕捉到上海人和上海的酒店和宾馆是有着势利气的。
这种地方,是有着势力气的。有一回,比尔去洗手间,阿三一个人先去落座,一个小姐过来送饮料单,很不情愿的表情,说了句:要收兑换券。阿三不回答他,矜持地坐着。等比尔回来,在她对面坐下,小姐再过来时,便是躲着阿三眼睛的。阿三心里就有些好笑。[5]p3
还有,一位著名的女作家,举止粗鄙,却受到众星捧月般的欢迎。只因为能进她家客厅的,都能拿到外国签证。阿三的一位朋友在马路上结识了一个向他问路的法国老太,恰好是个画廊老板,很赏识他的才华,将他办去了法国。“其余的人也似乎看到好运在向他们招手。大马路上走来走去的外国老少,不知哪一个可做衣食父母的。”[5]p26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阿三们希望能嫁给老外,提升自己的身份,实现出国留洋的梦想。
文学的主题即中心思想,是指整部文学作品中描绘的社会生活与人情事态所透视出的主题思想与意义。就这部小说标题而言,主题似乎是有关异国爱情故事的。就它的内容而言,主题应该是主人公阿三因为渴望异国恋情而不可得,最终堕落成劳改犯,并从拘留所逃跑的故事。小说的主题不同于一般的爱情故事,也不同于一般的忏悔录。小说中阿三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她一直认为自己不同于那些以性为职业的女孩。在法庭上她为自己辩护说:我不收钱的。为了得到一段异国恋情,她在宾馆里制造与形形色色的外国人的邂逅。她的心中似乎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高尚的信念:爱情。直到小说的结尾处,阿三还认为她对比尔的爱是不同寻常的。在她从拘留所逃跑后,她还用比尔鼓舞自己的信心,并且相信,她的这一切经历都是不平凡的,决不会落入平凡的结局。
最后,她又累又饿,来到一家农舍的屋檐下,在麦秸垛的旁边,找到一个鸡蛋。她看到鸡蛋壳上染着一抹血迹,就猜想这是一个处女蛋。她的心被刺痛了,流下了眼泪。阿三此时的眼泪很可能是悔恨之泪,但作者却没有任何道德评判。那个“处女”也许象征着阿三对自己初恋的珍视和怀念,这是阿三成长的动力之一。
王安忆在谈到男人和女人的差异时,说道:男人更多的是社会的人,他们的关注面很宽,感情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女人更多的是感性化的人,比较关注感情,感情生活几乎是她们的全部。女性的感情生活更加跌宕起伏。这是她选择女性作为主人公的重要原因。
阿三对异国恋情的追求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东西方文化如何接触的问题,这也是改革开放后我们遇到的问题。改革开放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比尔是(西方)现代化的象征,马丁是西方传统的象征,他根深叶长。在这方面他和阿三很像,但是,阿三将自己的文化放弃了要向马丁靠拢,而马丁不能接受没有根的阿三,有根的阿三与他有相隔甚远,所以阿三也不能和马丁在一起。这是一个女孩子在身体与精神都向西方靠拢的过程中毁灭,自毁的故事。[1]p166
它是一个象征性的故事,这和爱情、和性完全没有关系,我想写的就是我们的第三界的处境。比尔对阿三来讲就是一个象征,西方的象征,所以她和比尔的接触里面优一个最大的矛盾, 就是她必须用她的中国特性去吸引比尔, 但是她又希望自己不是中国人她希望自己成为和比尔同样的人,所以她一方面强调自己的中国特性, 一方面又想取消自己的中国特性……她是永远不能和比尔在一起的。[7]p166
阿三堕落的原因是,阿三虽然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但并未意识到中西方价值观念的差异。她跟西方的异性没有思想层面的沟通,就盲目地与他们发生性关系,
对爱情报有不实际的幻想。她并不了解中西文化各自的优缺点。就像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把西方文化美化,忘了自己的文化身份,梦想嫁给老外,最后只能导致自己的悲剧下场。这是王安忆对上海市民这种心里的绝好的讽刺。不同文化的吸引并不是男女婚姻的基础。阿三在向西方文化学习中,成了一个边缘人。中国的男人不会追求她,西方的男人不会与她结婚。
小说的叙述时间
叙事作品中的时间有两种表现形式:一个是故事时间,就是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状态;一个是文本时间,就是叙述故事时所呈现出来的时间状态,也叫叙述时间。前者只能由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根据日常生活的逻辑重新想象出来,后者则已经由作者在故事的叙述中提供给读者了叙述时间可以从时序、时距和频率三个方面来探讨。
叙述时序是文本展开的叙事的先后次序,从开端到结尾的排列顺序,是叙述者讲述故事的时序。王安忆在这部小说中采用了两种时序,来体现她的主题。在叙述过程中,如果叙述时序是按照故事时序的顺序叙述的,通常就叫“顺叙”。更多的时候,叙述时序和故事时序不一致,就是 “逆时序”。逆时序叙述传统上分为倒叙和插叙两种类型,前者是把顺叙序列的结尾放在前边,后者是在顺叙中插入若干此前事件的片段。逆时序往往可以使作品产生某种特殊的艺术效果。这部小说的开头先写阿三坐在前往劳改农场的长途客车上,开始了对于十年前与比尔相识的回忆。接着插入几段阿三在客车上的情况。随后,接着写阿三在比尔离开后的生活。然后,又插入一段阿三在客车上的情景。再继续写阿三和马丁的关系进展以及阿三在酒店的走马灯似的邂逅生活,直到她出事被抓。车子终于到了,阿三开始了在拘留所的生活。从此处到结尾阿三逃跑,都是顺叙。这样做的效果,使得故事富有悬念,更加引人入胜。插入的几段,增加了故事的节奏感,起到了起承转合的作用。另一方面,全书的三分之二都是阿三在车上的回忆,说明了去往拘留所之路漫长,反映出拘留所所在之处的荒凉和人烟稀少,反衬出上海都市的繁华和喧闹。
时距是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长短的比较。通过对时距地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叙事性作品的叙述速度及节奏。在时距方面,主要有四种运动形式:省略、概要、场景和停顿。这四种时距形式往往在作品中交替出现,形成了叙事作品疏密有致的叙述节奏。这部小说的时间跨度大约十年多一些,其中阿三和比尔的交往只有一年多,却是详细叙述的部分,约占全文的四分之一篇幅。对于阿三和比尔交往的场景尽量详细描写。阿三个人的生活状态多用概要的形式。“这段日子,阿三缺课很多。她的时间不够,要绘丝巾挣钱。”“现在,她的白天几乎都是用来睡觉的。”[5]p15比尔走后,阿三的生活多用概要,直到马丁的出现。他俩之间的关系只有短短的几天,却用详细的场景来描叙。后来,阿三的各种邂逅关系之间更多的是省略。这样,阿三的情感发展历程,起于爱上比尔,失望于马丁,结束于搭讪艾克。她的成长曲线就出现跌宕起伏。
叙述频率指的是一个事件在故事中出现的次数与该事件在文本中叙述的次数之间的关系。严格地讲,生活中不会有完全重复的事件,但在叙述话语中却可以反复叙述一个事件或一类事件。通过这种不断重复,从而产生一种特殊的叙述效果。其叙述效果,比叙述者站出来对这件事发表一通评论或感慨要含蓄得多。作品中,“我爱比尔”仅仅出现了两次。阿三把她与比尔的关系不断地跟人讲述,给那位女作家讲述,给她所邂逅的人讲她的男朋友比尔。这就加深了爱比尔的主题。
小说的叙述视角
这部小说标题“我爱比尔”似乎是第一人称叙述,而内容则是第三人称叙述。为什么作者要混用这两种叙述方式呢?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两者各有所长,各有所用,各有自己的特点。
叙事视角,是作品对故事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传统叙事性作品比较多的是采用旁观者的口吻,即第三人称叙述的方法。第三人称叙述是一种全知叙述,叙述者如同上帝一样,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可以了解过去也可以预知未来,甚至还可以知晓任何一个人物心灵深处的想法,根本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此,也称之为无焦点叙述。这种叙述方式由于没有视角限制,使得作者具有充分的叙述自由。第一人称叙述是到了稍晚的作品中才逐渐开始出现的。在第一人称叙述作品中,叙述者同时又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因此使得叙述具有明晰的主观色彩,由于叙述的故事是叙述者亲身经历的事情,还能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逼真感觉。叙事作品中有时候也出现第二人称代词,但从聚焦的意义上讲,这种叙述方式仍然是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的变体。如果作者不仅叙述了别人, 也叙述了自己,那就是第一人称叙述;如果作者仅仅是客观地向接受者叙述“你”、“你们”的故事,自己并没有作为角色在作品中出现,则是第三人称叙述。[4]p88
用第一人称叙述,叙述人“我”是作品中的一个角色,叙述角度是固定的,叙述语言受“我”的年龄、身份、性格等多种条件的影响和限制,带着鲜明的感情色彩,具有人物语言的某些特点。用第三人称叙述,叙述人不在作品中露面,叙述角度可以随时变换。叙述人可以居高临下,也可以与作品中人物取同一角度可以时而取这个人物的角度,时而又取那个人物的角度。[3]p195
王安忆用主人公阿三的一句话“我爱比尔”作为题目。而全文采取了第三人称叙述,称阿三为“她”。正是有意让叙述者更多地进入阿三的心理,让人觉得阿三的心理活动是真实的,又能方便地改变焦点,进入比尔、马丁和阳春面的心理,更好地体现出阿三和其他人的冲突和隔膜。例如,在阿三和马丁即将分开时,他们动情地拥抱,心理活动却大相径庭。
他抱着阿三,阿三也抱着他, 两人都十分动情,所为的理由却不同。马丁是抱着他的一瞬间,阿三却是抱着她的一生。马丁想, 这个中国女孩给了他如此巨大的感动,虽然她画得一点也不对头。阿三想这个法国男孩能使她重新做人,尽管他摧毁了她对绘画得看法,她可以不再画画。一个是知道一切终于要结束, 一个是不知道一切是不是能开始, 心中的凄惶是同等的。马丁看阿三, 觉得她离他越来越远,如同幻觉一样,捉也捉不住了。阿三看马丁,却将他越看越近,看进她的生活, 没有他真的不行。 [5]p49
在绝大多数现代叙事作品中,正是叙事视点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巴鲍尔德认为:第三人称叙述能够创造一个多变的虚构的世界,但缺乏真实性,第一人称叙述自称是真实的,因此达到了对于心理细节的可信表现,但是却是通过将自身局限于回忆录或自传的形式而做到这一点的。从叙事理论的角度来看,想要成为现实主义者的人面临的问题既包括内容也包括形式。所需要的是一种方法,能把第三人称叙述的方便之处与第一人称所保证的真实性结合起来。小说家通过结合各种叙事方法而做到这一点的。叙述者与人物之间、外在看法与内在看法之间的障碍消解了。
亨利·詹姆斯指出作者叙述者(一个不在行动中扮演任何角色的叙述者)讲故事,但并不纵情于评论或代词“我” 的使用;读者并未被提醒去注意,作者创作的实际上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且,叙述者假定自己只能进入一个人物的内心,这样就重复了我们在第一人称小说中所见的那种真实性的一个方面:在第一人称小说里面,像在生活中一样,我们并不知道他人心中所发生的一切。这种 “有限视点”常常既含有心理上的也含有视觉上的限制:叙述者表现的仅仅是这个人物所看到的,好像他是通过这个人物的眼睛看的,或者是作为 “不可见的目击者” 站在他身边。[2]p130
在小说中,阿三对比尔表白:我爱比尔。比尔回答:作为我们国家的一名外交官员,我们不允许和共产主义国家的女孩子恋爱。“要是换了中国的外交官,就会离开阿三了,可比尔的思路不是这样的。他觉得他和阿三都是很需要,都很快乐,这是美国人在性上的平等观念。”[5] p19
这段话中包含了隐含作者的评论和比尔的内心活动,这是第三人称叙述的优势之一。这段叙述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了解阿三和比尔对于性与爱情的理解不同,而这种差异正是文化不同所引起的。比尔和阿三的关系有着深深地隔膜,这是语言所无法传达的。他俩表面上有某种联系,实质上却没有关系。文化的隔膜就像一块玻璃,隔着两个世界。
故事中说阿三之所以叫阿三是因为在家排行老三,其实我们隐隐也能感到阿三就是第三世界的代表。她企图得到来自第一世界的比尔和第二世界的马克的接纳,然而一切都是徒劳。[6]p193
这就意味着,第三世界的国家在与第一和第二世界的国家交往的过程中,失去了很多东西。我们被侵略的不仅是我们的资源,我们的经济生活,还有我们的感情方式。一旦失去自己的文化身份,我们就会向阿三一样走向毁灭。
总而言之,在《我爱比尔》这部象征性的小说中,王安忆使用倒叙增加了小说的悬念,插叙控制了小说的节奏,第三人称叙述,多视角地呈现出主要人物的心理活动。标题中,“我” 的使用,混淆了主人公阿三和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界限,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通过这些不同的叙事策略,展现出阿三因为追求异国恋情而逐渐堕落的情感历程。
参考文献:
[1] 冯维娜. 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分析《我爱比尔》[J].西安:唐都学刊,2009年第6期,p166。
[2] 华莱士.马丁著. 伍晓明译. 当代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p130-133。
[3] 马振方. 小说艺术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 欧阳友权主编. 文学理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王安忆. 我爱比尔[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
[6] 王娜. 多元文化中的《我爱比尔》的解读[J]. 石家庄: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
[7]薛健编. 王安忆说[C].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该论文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12年基本科研项目(72123734)“中国形象的塑造和传播”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