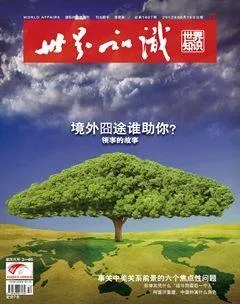条文很“枯燥”,实践很生动

相比环境、核不扩散等领域的国际公约,调整领事关系的《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下称《维约》)在国内受关注度并不高。这可能与历史上声名狼藉的“领事裁判权”有关,许多国人对“领事”二字天然反感。还可能与另一部维约——《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存在有关,许多人往往不加区分地捆绑提及“两维约”。再有就是《维约》中的特权豁免章节有些扎眼,当年笔者在国内法学院读本科学到这一条约时,和很多同学一样,认为这只是一部“各国领事官员俱乐部福利章程”,与百姓生活无关。
实际上,领事并不是外交的“穷亲戚”,有自己的滥觞,与商业仲裁、海事制度密切相关的领事制度甚至比政治外交的历史更为久远。领事与外交确有概念竞合的趋势,但领事制度更贴近普通民众的气质却始终突出。常驻国外,从事过一线外交、领事工作后,再看《维约》,通篇早已是为人民服务的“义务”,那些诸如保障“与派遣国国民通讯及联络”、“执行领事职务不受接受国司法或行政机关管辖”的“福利”只是对履行“义务”的基本保障。
外交部领事司是国内应用《维约》最集中、最直接的部门。作为领事人,结合日常工作的大量案例,查阅中外学者的论述注释,再与传统外交加以比较,仔细玩味,还是品出不少“领事《维约》”不同于“外交《维约》”的桀骜之处、“接地气”和“惠民生”的亲切之处以及趣味盎然的生动之处。
“国与国间领事关系之建立,以协议为之;除另有声明外,两国同意建立外交关系亦即谓同意建立领事关系;断绝外交关系并不当然断绝领事关系。”
由于与生俱来的“务实性”和“民间性”,领事关系自近代以来常与外交关系分开使用,同时也成为反映外交关系的晴雨表。有拿领事关系“开刀”的,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分别与印度、越南关系恶化时,将关闭驻对方国家领馆和撤走领事官员作为一项政策宣示。有拿领事关系“养刀”的,比如美国断绝与伊朗正式外交和领事关系后,通过在瑞士驻伊使馆设立“利益处”来维持两国间实际存在的领事交往。有拿领事关系“问路”的,比如前苏联与以色列曾将互派领事代表团作为恢复官方关系的第一步。也有拿领事关系“带路”的,比如英国通过业已存在的领事渠道向新中国递交了承认中国政府的法律文书。《维约》开篇便力图用简练的语言总结关于领事关系的丰富实践,以期规范国际行为准则,但实际上对于建立和断绝领事关系的形式要件,至今各国仍有不同理解。
“本公约并不禁止各国间另订国际协定以确认、或补充、或推广、或引申本公约之各项规定。”
二战后关于领事关系出现了许多的双边条约范本,最有代表性的是英美模式和苏联模式,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明确承认领事官员的政治任务、对名誉领事制度的态度、领馆馆舍的绝对豁免权等。1963年制定的《维约》在老牌国家与新兴独立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达成了最广泛的合意,并赋予各国另立协议确认或微调公约的权利,成为国际法编纂史上的重要成果和范例。《维约》是一部“活着”的法,是中国政府办理领事事务的重要依据,对一些没有通过双边协议固定下来的领事关系,《维约》的条文更被直接在谈判中引用。
“领馆须经接受国同意始得在该国境内设立。”
虽然领事关系不以设立领馆为必要条件,但领馆的建立乃至数量却是反映两国关系的重要表现。《维约》关于设领程序的表述看似清晰明了,但“经授权国同意”几个字背后却留足玄机,将裁量权留给了接受国。美国曾通告各国政府其接受设领的标准,要求书面提供经济商业关联度、签证护照量、领区规模等方面的信息。我国也对申请国与其拟设领地区的经济、文化、人员交往程度、领区划分的科学性等各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在国际领事实践中,一般以互换照会、协议等方式就设领达成一致。根据对等原则,各国一般还会提出在对方国家设领或保留设领权利。早期苏联坚定奉行对等原则,曾主动关闭在外领馆,以创造对等关闭外国在苏领馆的前提。由于一些国家的反对,《维约》没有明示确立设领对等的原则。
“领事官员不得予以逮捕候审或羁押候审,但遇犯严重罪行之情形,依主管司法机关之裁判执行者不在此列……领馆人员得被请在司法或行政程序中到场作证。”
外交和领事官员的特权与豁免被人羡慕,但也经常被媒体和影视作品讽刺揶揄。实际上,享受特权豁免的限定条件很多,而领事特权豁免的范围、层级更明显低于外交特权豁免。根据《维约》,领事官犯有重罪时可以被逮捕,而外交官则绝对不可侵犯;外交官无作证义务,但领事官一定程度上确有作证义务;前苏联曾主张领馆馆舍的绝对不可侵犯,但《维约》则认为在火灾等情况下,即使馆长没有同意,也可以视为同意而进入馆舍救灾。另一方面,随着外交、领事工作的发展,不少国家通过签订双边领事条约的方式,对领事特权与豁免进行延伸,向外交特权豁免看齐。美国在批准《维约》前,曾基于这一理念裁决阿根廷驻纽约总领事享有一定外交免税特权。
“各国可自由决定是否委派或接受名誉领事官员。”
古希腊城邦政治创造了选派本国人作为“外国人代表”为其所代表的国家的国民提供服务的制度,学者将其看做名誉领事制度的起源。近代以来,北欧、荷兰、西班牙等国家出于海事和商业的发展,热衷在他国港口城市委派名誉领事,甚至有时几个国家共同委派同一个当地人同时代表多国利益。但这一制度在全球范围远未形成共识,许多国家对当地或第三国人担任名誉领事心存疑虑。于是《维约》不避冗繁,专设章节突出这一制度的任选性。我国内地原则上不派遣也不接受名誉领事,对变相的名誉领事要求同样不予接受。例如欧洲某大国曾提出希委派其中国籍雇员担任内地一省的“总代表”,此议自然难获批准。
“遇有领馆辖区内有派遣国国民受逮捕或监禁或羁押候审、或受任何其他方式之拘禁之情事,经本人请求时,接受国主管当局应迅即通知派遣国领馆。”
据记载,缔约谈判时,关于领事通报和探视制度的权责划分谈判非常艰难,差点阻碍整部《维约》的达成。最后《维约》确立了接受国政府“通知当事人拥有相关权益”和“经当事人请求时通报当事国”的双重义务。《维约》没有规定最晚通报时间、探视频率等,对当事人拒绝通报的权利和拒绝探视的表示方式等也言之不详,许多国家各有侧重地通过双边条约做出明确规定。比如,中澳(大利亚)领事协定中规定了最多三天的通报期限;中俄领事条约规定当事人必须以书面形式明示反对其所属国领事官员探视等。但在实践中,许多国家基层执法意识不足、通讯条件有限,很难做到严格按约定期限和形式进行通报和安排探视,需要坚持不懈地进行普法教育和能力建设加以改进。领事通报不及时是双边领事关系中的“热点”问题,美国还曾因此被德国、墨西哥等告上国际法院。
维也纳并不只有音乐。《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等一系列著名公约的缔结使这座城市在国际法学界扬名,并从另一角度诠释了维也纳的独特气质。《维约》诞生50来,为规范各国间领事关系,推动国际法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立法往往滞后于实践,丰富多彩的领事实践不断向《维约》发出与时俱进的信号,许多国家提出修订《维约》的建议。法律的生命力需要遵循、注释、引申乃至挑战来维持。值得自豪的是,国际法的勃勃生机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中国印迹,中国以自己的实践丰富着国际法律体系。笔者曾在中国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切身感受过条约谈判的艰苦以及中国外交成就的来之不易。小文一篇,谨以此向《维约》50年致敬,向几代外交和领事人的智慧与汗水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