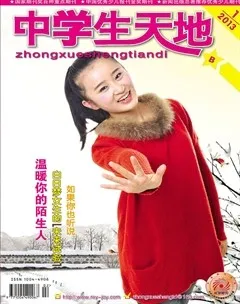刘震云:做自己喜欢的事
刘震云是当代中国第一流的作家,王朔曾这样评价他——刘震云是当代小说家里对我真正能够构成威胁的一位。他的作品很早就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和导演冯小刚的合作更是珠联璧合。他是中国最早被明星化的作家,人气一点不亚于娱乐明星。
见到刘震云这天,他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下午刚为“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做完评委,便马不停蹄地赶往下沙大学城为杭州师范大学的学子们演讲。期间他只在车上闭目养神了一小会儿,在大学食堂匆忙地扒拉了几口晚餐。
然而,晚上刘震云仍旧激情慷慨,睿智幽默地连续讲了两个多小时,对学生的提问、签名要求来者不拒,亲善有加。活动结束已是晚上10点多,但当听说有位博士生特意从南京赶来,想请教刘震云一些与他作品相关的问题时,刘震云还是微笑着一一给予耐心解答。
跟随采访了一整天的我,看到的刘震云丝毫没有明星的“霸气外漏”,他就是一位有见识、幽默且慈祥的长者。
我妈不识字。我却以此为生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刘震云(以下简称刘):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厨子、乡村剧团敲梆子的人或小学老师。这样就可以不离开故乡,可以生活在外祖母的身边。
记:这么看来,外祖母对您的影响很深。
刘:我的世界观、方法论的形成很多来自于我的外祖母。外祖母当时在村里的名气很大,因为她割麦子割得比谁都快。她的秘诀是,只要弯下腰就不再直起来。人家歇她不歇,所以就比别人快。我很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这也是我在日后文学创作上取得一点成绩的原因。
记:您曾是个叛逆的孩子吗?
刘:念大学的时候,从我进北大中文系的第一天起,每一个老师都告诉我,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我有悖老师的教诲。我妈不识字,我外祖母更不识字,而到我这儿,却以此谋生,有点“薄积厚发”的意思。我从事文学创作,从传承的角度来讲,确实有点儿叛逆。
记:您母亲养出个作家儿子,是不是特别自豪?
刘:当我母亲知道她的儿子从事的工作是文学创作,她曾经跟我有个“炉边谈话”。她说,听说你从事的行业跟鲁迅的是一个手艺?鲁迅这个人在你们这个行业算是个大个儿?我读过鲁迅的书。我在小卖部卖酱油,闲来无事想学学认字,就翻了一本鲁迅的书,我给你念念:后院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亏我不识字,我要识字,就可以这样写:供销社后院有两口缸。一缸是酱油,另一缸还是酱油。
反正,我妈觉得我的工作挺容易的,还总爱问我,文学有什么用?不过,我妈爱看电视剧。她觉得中国这些年最好看的电视剧就两部,一部是老版《红楼梦》,还有一部就是电视剧版的《手机》(改编自她儿子的小说)。
记:那您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文学有什么用?
刘:文学除了表现生活,揭示生活之外,它还解决了所有学科都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死的问题。清朝的人都死了,但是还有几个人活着——他们是宝玉、黛玉、宝钗、袭人……他们不但不会死,而且永葆青春。文学能够把青春、记忆、情感在时间和空间的坐标上给凝固住,这是文学真正的魅力。除此之外,它的背后一定有另外的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去不断探寻。真正伟大的文学家都同时是思想家。
幽默的不是我。是生活本身
记:您的小说给人的感觉就是在城市和乡土之间肆意游走,一边,从早年的《故乡天下黄花》到后来的《一句顶一万句》,故土情愫很浓。另一边,您在北京生活很多年,从《一地鸡毛》《单位》到《手机》,城市生活百态也拿捏得相当好,《温故1942》又是另一种情怀,这些不同的题材怎么能够分别都驾驭得这么好,您是怎么做到的?
刘:写农村还是写城市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你怎么去看待作品里这些人物看待世界的方式。作品背后的哲学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我接下来特别想写一个作品,《一地鸡毛》的续篇。30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从过去单一的权力社会的社会结构,到现在权力社会、金钱社会双重的社会结构。这些变化,30年来是怎么压在小林的身上,让他从小林变成老林。一个有能力的作家,不可能一直用同一种模式创作,一定会想去创新。
记:能谈谈您和冯小刚导演合作的新电影《1942》吗?
刘:其实开始我觉得《温故1942》不适合拍电影,这是纪实体小说。但冯小刚导演却通过各种努力把它拍成了电影。《温故1942》最重要的不是苦难而是面对苦难的态度,不是改编的部分而是背后的态度。大家可以看到,这部电影和他之前几部电影的不同。冯小刚是个好导演。大家都说他是商业片导演,其实他的片子里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商业元素,没有暴力,没有性,可他的电影又确实有票房,这里面肯定有不一样的东西。他改编过我的一些作品,比如《一地鸡毛》《手机》《温故1942》,严格说,我的小说从来不讲故事,也没有完整的情节,是随着人的情感流淌的。这其实是不适合改编成影视作品的。但他为什么要改呢?他看到的是另外一部分,比如对生活的态度,作品里面人物的态度。他是与众不同的导演,是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级大师的一个人选。
记:您的书很畅销,改编的电影票房火爆,在作家财富排行榜上有名……您还在坚持写作,在这个浮华的时代,寂寞写作图个什么?
刘:选择以写作为生,是因为我喜欢。写作给我带来很多乐趣,它是我摸索世界的一种方式。每一个人对世界都是懂的少,不懂的多。每个人都会通过自己的方法来探索这个世界,我用这样的方式摸索得多一些。写作总是要面对一些说不清楚的东西,包括情感、情绪、往事、梦,这些说不清的东西,对想要了解他们的人而言显得特别难,文学不是要把他们说清楚,而是把世间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然后留下来。
记:您怎么评价自己?
刘:一个努力的人。
记:莫言这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您怎么看?
刘:莫言获奖,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问我的感受。我就开玩笑说,这好比我哥娶了个嫂子,你们来问我的感受。我的回答是,祝他愉快。还有人马上说,你也到了结婚的年龄了,我的回答是,我不急。有人说,莫言获奖说明中国文学走向了世界。中国走向世界,这个概念本身是存在问题的。许多中国人说这话的时候,把自己的位置忘了,别人的世界才是世界吗?一个民族总想被除了自己以外的民族承认,这是种弱小者的心态。我觉得莫言去申报诺奖的态度非常值得赞赏,他的得奖论证了,中国作家的水平一点不比别的国家的水平差!
记:您一直坚持的语言风格是平实、自然、明白如话。但是现在许多孩子一写就是重重的文艺腔,曾有些爱写的孩子跟我谈起他们的困惑,说似乎他们写东西一旦“明白如话”了,文章就显得特别没货、难看,显不出文学水平。您觉得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刘:同样一句话,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件事,20岁的你、30岁的你、40岁的你看法是不一样的。写作需要生活的积淀,需要见识的积淀,需要感悟的积淀。只有一个人胸怀越来越宽广,越来越宽容,越来越善良,你对世界的认识才会越来越深入,你的目光才会到达过去你没有到达的那些黑暗的地方。老有人说我的语言幽默。真正幽默的不是我,是生活本身,我就是个生活的搬运工,负责还原生活本身。所有悲剧都经不起推敲,仔细推敲全是喜剧。
记:其实,热爱文学,喜欢创作的中学生还是挺多的,但眼下文学创作有种被边缘化的态势。您想对这些文学少年们说点什么?
刘:一个作者写好一个故事,写好一个人物,包括语言能够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些是稍作努力就可以轻易达到的。但是比这些重要的是,你除了能写出宝玉、黛玉和袭人,你还能想到这是一块石头和一株草,能想到这是太虚幻境和人间,能想到清洁和肮脏的关系。这才是一个作者和一个伟大作家的区别。写作品不在写的时候,而在于不写的时候。不写的时候在干什么?在思想。
“功夫在诗外”是一句特别日常却含义深刻的话。一个人在生活中是什么样的人,他才能够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特别爱占人家便宜,这个人当官,他建的桥肯定撑不过20年,这个人当作家,一定会占笔下人物的便宜。所以在生活中,多请人吃饭,少占人便宜,这是干好任何事情的前提。
另外,这个世上本不存在事业,只存在琐碎,重复做一件事,做的时候坚持着每次往前一点点,你就会是优秀的,无论干什么都是这样。
我觉得这一代孩子很有希望
记:您觉得现在的90后与前几代人相比,有什么特点?
刘:我觉得这一代孩子很有希望。这些年我开讲座,跟许多年轻人交流,这一代人跟前一代人最大的区别是,提问的角度不一样了。他们问的比较多的是,我该怎么办,就业怎么办,裸婚怎么办,蜗居怎么办……都是关注“自我”比较多的问题,而上一代人提的问题往往是“中国该往何处去”……我认为,当每一个人都关心着“我往何处去”的时候,就是这个民族的崛起。
记:回忆您自己的成长经历,您觉得最得意的和遗憾的是什么?
刘:在成长的道路上,得意和遗憾每天都会发生。更重要的是,要允许自己在青少年时代犯错误。正确的认识是从不正确的认识来的,做得好是从做得不好演变而来的。要释然地去面对成长。中国的孩子是世界上最累的孩子。孩子十八般武艺都会,却没用。孩子就应该做自己,不要做家长喜欢的事,不要做别人喜欢的事,更不要做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的事。
记:听起来,您女儿肯定是在一个特别宽松的环境中长大的吧?
刘: 我给她宽松,但她把我弄得很不宽松。处处管,事事管,一点也不知道抓大放小。平常都是她教育我,最常说的就是让我做人要聪明点,为人处世、自理能力有待改进。她以前周末回家一扔书包,看到我就会问:小刘最近怎么样啊?在我们家,她管我叫小刘,我喊她老刘,我们俩关系特别铁。
记:您最想对《中学生天地》的读者们说的,一句顶一万句的话是——
刘:做自己喜欢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