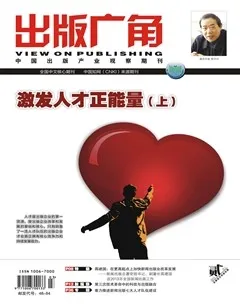看见自己,也就看见了人生
2013年,我读的第一本书,是柴静的《看见》。
我坦言这本书我读了好些天,一篇一字地都看了。我也坦言这篇文章我放下书后好几天都不知该如何下手,即便是现在,我仍有“思绪万千,不着一缕”的感觉。这一切,都是因了《看见》这本书给我的触点太过博杂的缘故。柴静在书中让我看到一些我曾见过却并未真正“看见”的事情和人物,让我想起了一些曾经想过却未真正想明白的问题——可关键的是,关于这些人和事,在书中柴静也并未结出什么答案——到底看见了什么?想明白了什么?
这并不是一本关于真相,关于真理的书。柴静写这本书,在我看来,就是要抓着你和她一起,不断推翻,不断疑问,不断重建,关于自己,关于自己看见的,经历的,生命中的那些人和事儿。作为一个调查记者,柴静以为,想如何报道一个国家,就要如何报道自己。而作为生活中普通一人呢?我想到,我们会看见怎样一个世界,怎样一种生活?前提是,我们会看见怎样一个自己。
自己,要看见自己是很难的。在书中,柴静坦陈自己做调查记者时,曾什么也问不出来,失魂落魄地出门下楼,甚至还“紧张”得将采访本落在了被访者的房间。这样一种不见硝烟的对峙,以及对峙后的溃败,不是只属调查记者一方的,对被访者来说,同样失去了言语的权利,失去了审视自己,及时矫正,回归正途的机会。对此,柴静有深深的挫败感,这样的挫败感仍在往后的调查中,在柴静或细密,或凌厉的询问后,屡屡出现。面对受访者的沉默,柴静最终发现,调查访问并非看似的“直面真相,直击万众期待的底层”。调查访问是生命与生命的交叠,心灵对心灵的探寻,身影对身影的回望。
当柴静放下既定的采访提纲,直视他人的眼睛,放下既有的道德判断,聆听他人的言语,她开始渐渐地看见了自己,体会自己身处的这样一个世界——这不是一个主观意念下的,有着真实细节,有着温度,有着脉动,有着无能,也有着力量的世界。我们与这个世界融为一体,难分彼此。阅读《看见》的同时,我也一边在网络上寻来柴静的节目看看。《命运的琴弦》给我留下同样深切的思考。
面对三个艺考学生的“不公”命运,柴静和受访者之一宋飞一起在镜头前探讨: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这一切呢?我想这也是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都期待的答案。然而,节目最后留给大家的,并不是所谓的真相,而是一个问题,一个引着大家共同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许有些残酷,但并不让人悲观,看见的,仍是改变的可能和希望。这个问题,是受访者宋飞提出来的,她问:“在一个大学里,如果看不到知识,只看到权力,这是不是洪水?”
柴静的《看见》,已然超越了简单的“揭示真相”和“道德评判”。柴静在多年的调查访问中收获的,是这样些许切身的体验:对人,对事,对自己,我们只有了解多深,才能呈现多深;有些事情,我们要聆听各方的声音,调查采访更多的是呈现,而非判断;而有些事情,是有人相信,并坚持,才会真的存在;在很多时候,我们和他人,和这个世界并无什么距离,并无什么不同,我们甚至彼此交融,无分一二,当我们毅然决然地将他者划入自己的对立面时,我们是否要反思,这是将无知当真理,把偏见当原则,把痛苦当绝望,把观火当建设,从而坠入一种普遍的,极端的,无用的情绪?d/68KuUhXKBgVabV6D2anw==
在新书发布会上,柴静曾笑谈自己的“青春日记”,满满的一大本,却只是弥漫的情绪,没有事件,没有细节,写下的全是情绪鲜明的判断。一个爱情故事的开始,是:“啊,你是我的白马王子!”结束,则是:“啊,你这人渣!”自莫言获奖演讲之后,大家都爱讲故事了,而我不得不承认,这同样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而又意味深长的故事。
看见。认识。呈现。
柴静的文字让我看到这样三个彼此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概念。在既定的,相对封闭的经验世界里,我们的“看见”是有限的,从而对“看见”的“认识”和“呈现”也是值得去推翻,质疑,甚至是重建的。在药家鑫的案件里边,既定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依法处置了一个应该处置的人。而在柴静的节目中,我们看到的药家鑫,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坏人,是一个“做了坏事的人”。然而,是什么让一个人做了不该做的事呢?这是柴静这一期节目的坚持。而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追问或忽略,其实是我们“看见”“认识”“呈现”状态的真切体现。现实中面对此类人事,我们的习惯做法往往是选择忽略,再贴上诸如“富二代”的标签,然后任意挥洒我们的情绪。我们就这样在对他人的迷失中,也迷失了自己。
如何看待自己?这几乎是柴静每做一次调查访问,都要直面的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将节目做得客观,不失于主观臆断,或不被情绪左右。“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多年来的调查经历让柴静深知:自我感动,感动先行是准确的最大敌人。自我的认知和触动不该理所当然地成为“看见”世界的依据。书中柴静谈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特区法院院长吴经熊,曾在自传中写道:……我只是在人生舞台上扮演一个法官的角色,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他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这是一个法官对“自己”的认知,因而他“看见”的不仅仅是坏人,是死囚,还是一个又一个的生命。对此,刑事法官何帆的成长及改变也颇让人一番琢磨:何帆学生时代读到吴经熊这番话时,在一边批上“伪善”二字,如今他再读这段话时,划去了先前的批语,在旁边郑重地写上:人性!
看见自己的确很难,因为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之中。柴静将对一个国家的报道,回归到对“自己”的报道,我以为是正确可行之道:一个调查记者,只有从“大多数”的群体中走出来,从既定的经验世界里走出来,从既有的道德评判中走出来,直面人事,尊重并坚持自己身在现场的发现和思考,这样的“看见”,才是真正的“看见”,这样的世界,也才是真切的世界。最后,我想到的是,柴静“调查记者”这样一个身份并无特殊之处,因为对每一个人来说,谁又不是自己人生的“调查记者”呢?这样,文字写到这里,文章的标题也就有了:
看见自己,也就看见了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