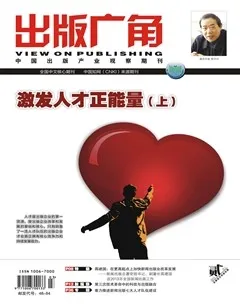关于数字图书实行书号管理的若干思考
数字图书实行书号管理有益于数字图书国际交流、图书馆管理、国家数字出版政策的制定、数字出版行业数据的统计与研究等,是一项势在必行的工作,国际社会也需要制定一套新的数字图书编码标准来适应当前数字图书书号管理的需要。
当前,“电子书”一词在我国的使用较为混乱,时而指数字图书阅读器,时而指数字图书本身。在英、美等国没有这一问题,电子书就是“e-book”,电子书阅读器是“e-reader”,很明了,不易混淆。为了不产生歧义,本文使用“数字图书”这一概念,专指以数字形式存储的、可以在多种终端发布的图书。
一、数字图书实行书号管理的必要性分析
实际上数字图书实行书号管理与纸质图书实行书号管理的原因有很多是相同的。
1.统计、管理的需要
如果数字图书实行书号管理,出版机构、出版数量、出版品种、出版总产值等等数据就一目了然了,给国家的管理带来很大的方便,为国家数字出版政策的制定提供可靠的依据,也会给研究者提供很大的方便,对整个行业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令人遗憾的是,笔者查阅很多资料,也见不到国家数字出版机构数量、数字图书数量等的统计数据。在《2010—2011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报告》中竟然没有网络出版单位数量及数字图书的出版数量统计。缺少这两个最关键的数据,其他数量就显得说服力不足。政府对互联网出版资质的认定处于一种尴尬状态,经过认定的颁发许可证的互联网出版企业只有300多家,而众多的互联网出版企业是没有颁发许可证的,但又不能不统计,而且很多未经认证的企业做得还很大,市场知名度很高,如果取缔,负面影响显然很大。即使要取缔,也不是仅仅新闻出版总署说了算,新闻出版总署没有执法权。一家互联网企业的生存还涉及工信部、广电部门、文化部、工商局、公安局等部门,而且这些部门好像对互联网企业的支配权更大一些。原来很多企业还在积极申领许可证,现在很多企业看到没有互联网许可证的企业并未受到查处,也不再积极申领。这样就使得要弄清楚数字出版企业的数量很困难,更别说弄清楚出版了多少数字图书了。另外,目前,数字出版也没有像传统出版一样建立一套数据采集系统。在这种条件下,如果建立书号管理系统,就会给统计带来极大便利,数字出版产业报告也不再尴尬。
数字图书实行书号管理会方便对出版者和图书质量进行管理,数字出版企业的情况就比较容易掌握。实行书号管理,就要求数字出版企业申领编码。哪家企业出版的图书出了问题,就可以对之进行相应的处理。对数字出版企业的内部质量控制、作业流程等也便于做出相应的规定。
数字图书实行书号管理还会方便读者辨识盗版书。有了数字图书书号,读者就能很容易查到数字图书是哪家出版机构出版的,便于买到正版数字图书。假设被人盗版了,书号也可以作为辅助认证手段,因为书号中包含出版机构代码。
除此之外,数字图书实行书号管理便于对数字图书的研究。如果实行书号管理,就很容易知道每年出版多少种数字图书、图书类别分布、总码洋书等宏观和微观数据,便于学者进行研究。现在数字出版平台很多,但是这些平台公布的数据,要么夸大数字图书存量,要么压低库存图书数量,使得国家难以准确地进行统计。
2.实行书号管理符合现行出版法规的需要
现在的数字图书大多数没有使用中国标准书号ISBN和条形码。中国标准书号ISBN和条形码是一本书的身份证,便于检索和识别。数字图书不使用ISBN是不符合国家关于电子出版物的管理规定的。《电子出版物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出版(包括再版)电子出版物,须按规定使用中国标准书号。网络数字图书属于电子出版物应该是无疑的,就应该严格按照《电子出版物管理条例》的规定,使用中国标准书号ISBN和条形码。现在,有些数字图书是由纸质书转换而来,使用的是纸质书书号,但是大多数数字图书是没有经过纸质出版的,直接在网络上发布,没有书号。应该说,纸质书号不能代替数字图书号,其定价和纸质书是不一样的,按照书号使用的管理规定,应该申领新的书号。笔者建议设置数字出版物专用书号,以区别于纸质书号。
3.避免同名异书带来的混乱,对数字图书销售有利
现在的图书书名为了简洁明了,易被人关注,往往字数很少。现在的书名以四字最多,据有人做的一项调查,四字书名占15.4%,五字书名占13.33%,其他字数书名占的比例都很低,这就很容易导致书名重复。现在市场上同名异书非常多见,甚至一名多书,比如2011年就出版了7本以“建党伟业”命名的书;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十万个为什么》之后,现在至少有500多种《十万个为什么》同名书,另外还有一些相近书名,比如《正者无敌》与《仁者无敌》等,都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混乱和麻烦。而数字图书数量更大,重名的几率会更高。书号具有唯一性,全球统一编号,不会重复,准确率高。数字图书如果实行书号管理,数字图书的身份更容易确定,不易混淆。
实行书号管理,尤其是国际统一管理,图书信息会向管理中心汇聚,管理中心与世界主要的图书馆都有连接,这些图书馆就会知道哪些图书已经出版,然后根据需要购买。这实际上等于是对图书的宣传,会增加图书在国际上的销量。
4.图书馆管理的需要
图书馆对入馆图书要进行大量的登记录入工作,包括书名、作者、出版者、开本、印张、印数、出版日期等等,还要进行分类。有了书号,尤其是实行条码或者二维码后,图书馆通过扫描系统很快就能够将上述信息输入计算机,因为这些编码中已经含有上述信息。尤其是数字图书,图书馆每年的购买量很大,图书馆图书信息录入工作量很大。实行书号管理可以大大降低图书管理人员的劳动强度,提高他们的办事效率。
5.国际交流的需要
图书之间的国际交流越来越频繁,各国都需要对图书信息进行确认,需要一个统一的编码系统。实行书号管理,便于国际数据交流,从而扩大图书影响。
数字图书书号像纸质书号一样是一个国际问题,而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现在因为没有国际规则可以遵循,亚马逊自己制定了一套规则。亚马逊为Kindle版数字图书、音频版数字图书配发数字图书书号ASIN,连字母和数字10位。不同于ISBN,因为字母是A~Z,是28个选择,而数字只有0~9,所以亚马逊的书号容量较大。亚马逊为J.K.罗琳2012年9月26日在Little Brown 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临时空缺》(The Casual Vacancy)除有纸质书号外,还配发了数字出版书号“ASIN: B007THA4FI”。在亚马逊网站,我们也能看到许多图书被配发了ASIN书号,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经过多方打听,也不明了ASIN的编码规则。
除此以外,实行书号管理也是图书信息标准化的必然要求。现在各单位自搞一套,使图书信息交流极为不便。台湾已开始实行数字图书书号管理,2010年8月已经颁发2000多个数字图书号,使用的仍然是ISBN。
二、数字图书实行书号管理的难题
1.对于未获得互联网出版资质的单位是否颁发数字图书号
面对众多未获互联网出版资质单位的客观事实,如不给这些单位书号,显然不符合出版现实,书号管理的目的就无法达到;如果给了,就等于宣布互联网出版许可证作废。这恐怕也是政府在这一问题上举棋不定的一个原因。
2.数字图书数量巨大
现在从事数字图书出版的机构很多,难以统计,一些大型数字图书出版机构的数字图书存量非常大。仅盛大网络文学每天上传的中文原创作品字数就达到1亿字以上,按每部30万字计算,就是333部作品,也就意味着每天要给盛大颁发333个数字图书书号,每年就是12万多种数字图书。截至2012年第一季度,盛大网络数字图书总量为600万部,这还仅仅是盛大一家。中国移动杭州阅读基地的数字图书数量也很大,保守估计也都在几十万册以上,而且每天都在迅速增加。全国的数字图书总量现在则很难说清楚。
据光明网的一名记者估计,现在全国互联网企业从事出版业务的网站占网站总数的50%以上,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 2012年1月公布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域名总数为775万个。照此推算,从事互联网出版业务的网站应该在380万家以上,而获得互联网出版许可证的单位则屈指可数,仅有300多家,万分之一都不到。这是一个极大的反差。以每家出版10种数字图书计算,每年就是3800万种,这更是一个海量数据。
3.现有ISBN难以容纳
ISBN是在20世纪60年代为解决图书国际交易中的识别问题和图书馆工作的需要而设计的一套编码系统。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在英国试用,1972年成为国际标准,并迅速在全球铺开。1986年中国引入国际标准书号系统,1987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代替“全国统一书号”。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那么近 那么远》为例,书号是ISBN 978-7-5302-1191-5,978是后加的,是欧洲商品货号,除此以外,共10位数字。其中第一组数据是国家或语言编码,国际书号组织配发给中国的是7;第二组数据是出版社编码,我国大多数出版社编码是4位数,也有部分是5位数;第三组数据是具体图书编码;最后一位是校验码。
如果对数字图书实行书号管理,现有ISBN容量有限,不足以承担数字图书书号的使用。前些年,就有报道说英国纸质书书号将要用尽,需改进书号编排办法。现在数字图书的数量远远大于纸质图书,书号肯定难以满足需求。10位数字中除了“7”和一位校验码,还有8位数可供为出版者和每本图书编码,出版社编号如果位数太少,容纳的出版社就少。现在我国有380多万家数字出版商,要想容纳这些数字出版机构就需要7位数,少于7位数就不能容下所有数字出版机构。7位数的出版社编码可以容纳1000万家出版社,这样的话,留给每本书具体的编号只有一位数,每家出版社只能出版10种图书,显然是没有意义的,基本可以排除7位数的出版社编码。以此类推,出版社编号6位数和出版社编号5位数也没意义,可排除。我国现在大多出版社采用4位编码,可以容纳1万家出版社,每家出版社最大出版量是1万种;部分出版社是3位编号,可容纳1000家出版社,每家出版社可出版图书总量10万种;还有少数是2位数,可以容纳100家出版社,能够出版图书100万种;如果开放1位出版社编码,可以容纳10家出版社,每家可以出版总量为1000万种。总体算下来,有效的出版社容量是11110家出版社,总的图书容量是4亿部。现在全国有380万家数字出版机构,11110家的容量显然不够。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数字图书实行书号管理必须探索新的图书编码制度,ISBN是容不下的,国际社会应该探讨一种新的书号编码方式,以适应数字出版的需要。
新闻出版总署在2009年4月就已经公布点读笔行业标准,采用的是深圳天朗科技公司的技术——MPR编码,采用16位编码制度,可以容纳1亿亿多个编码,完全可以作为数字图书的身份编码,其中也有出版者编码、具体图书编码等。新闻出版总署可以委托该公司对这项技术加以改造,专门用于数字图书书号编码。
4.数据库出版如何给号
现在数字出版中数据库出版是一个大项,盈利模式稳定,但是,数据库中很多内容是片段,有些是对整本书的碎片化,有些则是从一些档案等文件中摘录,本身已经不是作品,对这些片段颁发书号显然没有必要。数据库种类很多,有些数据库建成之后,就不需要更新,而有些数据库则是每时每刻都在更新,比如里德·爱思唯尔数据库、清华知网期刊数据库等。这些数据库往往有着海量的信息,对数据库颁发书号,显然违背书的定义。
5.开放式交流平台的数字图书如何颁发书号
百度文库等开放交流平台、博客中的数字图书都是由一些网友自发上传,不为盈利。那么,随便上传一本数字图书,是否也要给书号?这也是一个难题。
6.连载图书如何颁发书号
盛大等原创文学网站,很多作品是连载作品,每天都在上传新的内容,内容经常处于没完成的状态,等于是图书没有定稿,但是已经开始收费阅读。笔者以为,这些连载图书需要在刚开始就给书号,因为它需要售卖,需要识别,就需要身份证。
三、数字图书实行书号管理应注意的问题
1.实行书号管理不可能一步到位
对数字图书书号管理,不可能一步到位,这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能先要试点,然后逐步推广。即使是开始推广,一些出版单位开始实行,另一些出版单位可能仍要观望一些时间,数字图书书号管理要在全行业真正推广恐怕需要一段时间。
2.申领系统要方便快捷
在纸质书出版方面,因为总量控制、书号买卖等原因,一号多用情况较为多见,尤其是教辅出版,一号多用较为普遍,使得统计数据失真。为避免这种情况在数字图书号中出现,我们要为数字图书书号的申领者提供便利,使之没有必要一号多用。
3.互联网出版资质的审批要开放
近年来,尽管有人在媒体上呼吁对数字图书实行书号管理,但是始终难以推行。笔者建议对互联网出版许可证的申领实行放开政策,放宽审批条件,颁布政策鼓励企业申领许可证。
4.政府应该改变重管制的观念,改为重服务
我们实行书号管理,仅仅是为数字图书出版提供更好的服务,不能因此使大家不能自由地创作和发布作品。新闻出版总署早就对数字图书实行书号管理的问题做过考虑,也开过相关会议,来自网络出版界的人士更多的是对书号管理的担忧,担忧造成数字图书出版的不自由。这恐怕也是总署在数字图书书号管理方面迟迟没有出台政策的原因之一。同时,政府部门不宜抱着管理、控制的念头,而是应该出于服务的目的,打消数字出版单位的顾虑,数字图书书号的推广将变得不再困难。
总之,数字图书实行书号管理有益于数字图书国际交流、图书馆管理、国家数字出版政策的制定、数字出版行业数据的统计与研究等,是一项势在必行的工作。国际社会也需要制定一套新的数字图书编码标准来适应数字图书书号管理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