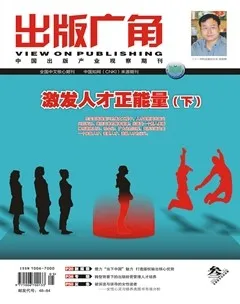《春润集》:吴福辉先生三十年的文学梦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言,20世纪80年代,“那即使算不上最辉煌的学术文化时代,也是一个其人物最富有魅力的时代”,对我而言,我始终迷恋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学人,也始终认为包括钱理群、吴福辉、王富仁、赵园等在内的这代学者是最富有魅力的。吴福辉老师经历了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涌现出来的新人”到“学科建设最为活跃的中坚力量”的嬗变,如今已经退出学术第一线,但他的学术研究还处在进行时状态。刚刚读完钱理群老师的《幸存者言》,赵园老师的《昔我往矣》,就收到了吴福辉老师的《春润集》。
单单这个书名就很有意思。“春”指的是他的导师王瑶先生生前的北大寓所镜春园,“润”指的是吴组缃先生生前的北大住所朗润园,于是他便将“镜春” “朗润”各取一字,成“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之意,表达他对两位老师的纪念。王瑶先生去世前,吴老师一直陪伴在老师的身旁,目击了王瑶先生逝世前的一段生活,这让他永远铭记难忘,为此他写下本集子里所收的纪念文《最后和最初的日子》。吴组缃先生虽然不是他的“亲”导师,但吴老师得到吴组缃先生的教益良多,特别是在吴先生的小说史课堂上突然获得的“北大意识”,也包括编张天翼的研究资料和年谱时的访谈,为此他写下本集子里所收的《一株遒劲独立的老树》表达对吴组缃先生的思念。无论是王瑶先生还是吴组缃先生,“他(们)又何曾真的走了呢,他(们)像一棵大树,你任何时候迈入他的浓荫下,最初会觉得森然,随即便会感到凉爽宜人,不忍离去”。
王瑶先生曾说“每个人如果能根据自己的精神素质和知识结构、思维特点和美学爱好等因素来选择自己特点的研究对象、角度和方法,那就能够比较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智,从而获得更好的成就”,他要求自己的学生“每写一文,必要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所推进,或提供新材料,或提倡新的观点、思路,必要有自己的发现,而所写的重要论著,则应成为所研究的课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别人的研究可能也必然超过你,但却不能绕开你的研究”。王瑶先生在给吴福辉老师的第一本集子《戴上枷锁的笑》作序时就看出吴老师自觉地“寻找自己”的努力:根据自己的特长“寻找适合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角度与方法,开拓自己的前进的道路,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由《春润集》这部编年体文集,不难看出吴老师的学术生命史的摸索期:从重新打量左翼讽刺到蓦然瞥见京派讽刺,直至海派作家进入全视界;发现期:提出“京海两难”和“京海冲突”的文化结构,深入探究海派,在中国城乡大环境下俯视都市文学,至市民文学;个别到综合期:有了三种现代文学形态或更多形态的多元共生文学史的观念,并从合力写作文学史到独立完成文学史,实现夙愿,等等,均清晰可见。套用赵园老师《昔我往矣》自序里的话,由《春润集》诸篇,不难窥见吴福辉老师的生命周期,尤其其间消磨、蜕变的痕迹。当然,收在这里的,只是生命史的若干痕迹,而“生命史”以至写作的历史要远为复杂曲折,这是不消说的。鲁迅先生曾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春润集》只收了吴老师的三十六篇文章,我们只有结合他的《带着枷锁的微笑》《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沙汀传》《且换一种眼光》《游走双城》《深化中的变异》《多棱镜下》《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以及他编选的刊物、书,以及他所有的人生阅历、他所处的时代、所在的学科、所在的单位才能真正走进吴福辉老师的学术园地。这也是不消说的。
这本集子吸引我的,不单是集子里的文章,还有集子的编排风格——按照代表性(将个人和学术纪年都计在内)、初刊状态(不予修改)、混合编组(长短论文兼搭配散文随笔)几项原则遴选。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三十年集”系列丛书的作者都是如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著名学者与知识分子,他们的文章在刊物、报纸上刊载时,因为各种原因,几乎都有过被删节、被修改的境遇,吴福辉老师的也不例外。但吴老师坚持初版本,不予修改,保持文章的原生态,“立此存照”,这是我非常欣赏的。比如本集子的第一篇文章《现代病态知识社会的机智讽刺——〈猫〉和钱钟书小说艺术的独特性》,原文是有注释的,但发表时被删去,收入《带着枷锁的笑》时恢复,但如今依然保留原状,显示文学刊物与学术刊物的区别。当然我最感兴趣的是吴老师为编集子写的每年纪事,这些最具有学术史的史料价值,也最吸引我。比如他在1982年的纪事中就提到他收在本集子里的评施蛰存《春阳》的《中国心理小说向现实主义的归依》一文的题目是《十月》的编辑修改的。他在1989年的纪事中回溯了他提出“京海冲突构造”概念的背景,“来源于长期对中国经济文化不平衡性的感受,是自少年时期冷丁离开繁华沪地到了严寒东北市镇就一直隐隐环绕我灵魂的实际生活体验,在强烈接触了京海派文学之后自然提升出来了。它使我终于找到了属于个人的学术领域——一块自己的园地”。他在1991年纪事中提到,“据陈子善说,张爱玲在大陆最早进入文学史,当属1987年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那里上海孤岛沦陷时期的文学一节是我写的,有评论张爱玲的七百多字一段话”。他在1992年的纪事中提到《我为沙汀作传》是因为“川人要我回答为什么第一种沙汀传记竟是我这种不会打抑扬顿挫唱歌一样川话、吃不了麻辣食品的人写的”。他在1995年的纪事中还提到了他的学术专著的阅读史和接受史,冯亦代先生自动为《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写书评,并建议吴老师扩大研究海派的散文,董鼎山先生访华过沪,在新民晚报写他们一群老朋友在上海聚餐会上传阅《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的场景如此等等,在此不一一列举,这些都为我们走近吴福辉老师的学术园地提供了扶手,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吴福辉老师的这本三十年集,我最关注的是他关于文学史编写的若干文字。1983年吴老师写了《文学史应提倡私人著述》,不过出版时题目改为“提倡个人编写文学史”。他在参与三人集体编写《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之后,仍念兹在兹,写了本集子中的《中国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其在当下的意义》《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主流型”的文学史写作是否走到了尽头?》等关于文学史观念的文章后,终于在他七十岁时由他母校的出版社出版了由他独立完成的《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当时他在给我的签名时写道“读做梦者的文学史,做文学史的新梦!”。的确如此,这部书的出版终于实践了他1983年的梦想,怎能不让他感慨系之呢!他对于文学史的看法并未到此止步,2010年他又写了本集子里的《农民大众文学与市民大众文学并存的新局面——谈1940年代文学全景中的重要一角》,2012年他又在《现代中文学刊》上写了《“平津文坛”漫议》,开启了他的新梦之路。
1991年吴福辉老师在出版《带着枷锁的笑》时,写到他当时的心情,真没有料到,“编自己第一个集子的心情会是沮丧多于兴奋”,“我感到自己的贫瘠、荒芜,如同一个零”,如今他编《春润集》时,又说,“掩卷想来,从内心最深的一个角落里禁不住发了一声叹”,这叹息有放松的意思,但随之这体味就加了分量,“沉重起来”,“三十年”会不会即是我的一世呢?
吴老师,你还记得你《游走双城》的最后一句话吗?“终点还没有到达,也许永远不会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