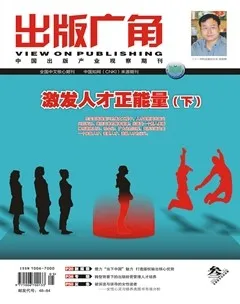卖不动的《海上花》
一向说好书不得好卖,但并不能因此断然说卖不动的,就一定是好书,这是一种遁词。好书或许卖不动,但卖不动的却未必好书。
一向说好书不得好卖,但并不能因此断然说卖不动的,就一定是好书,这是一种遁词。好书或许卖不动,但卖不动的却未必好书。说到“好书”不能得到大众的追捧,例子可以说俯拾皆是,为了更有说服力,我们不妨从一个更有权威定论的case说起。
清末小说《海上花列传》,又名《绘图青楼宝鉴》《绘图海上青楼奇缘》。书凡六十四回。是著名的吴语(苏州话)小说,也是中国第一部方言小说。作者署名花也怜侬,即松江(今属上海)人韩邦庆。韩字子云,生于1856年,曾在河南做过幕僚。他和蒲松龄、吴敬梓一样,也是个科举的失意者。他于光绪辛卯年(1891年)秋赴京应试,落第后返回上海,常为《申报》写稿,所得笔墨之资,悉数挥霍于花丛之中。《海上花列传》就是以娼妓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十里洋场中的妓院生活,涉及当时的官场、商界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层面。
一开始,大家甚至对本书作者的情况都不甚了了,还是胡适先生进行了一些搜集,才略有收获。胡适先生以为,《海上花列传》是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此书1894年初版,同年作者逝世,时年39岁。按照同时人孙玉声(海上漱石生)的回忆,“逮至两书相出版,韩书已易名《海上花列传》(按原题《花国春秋》),而吴语则悉仍其旧,致客省人几难卒读,遂令绝好笔墨竟不获风行于时。而《繁华梦》则年必再版,所销已不知几十万册”。《繁华梦》即孙氏所著《海上繁花梦》。即便从写作的题材乃至《青楼宝鉴》这样的书名而论,《海上花》似乎也没有不风行的道理。一般认为,用苏白写作是此书不能风行的原因,尽管依照胡适的说法,吴语因昆曲和上海的商业地位以及江南女儿的秀美而“最有势力又最有希望”。但所谓“鴃舌”,指的是伯劳鸟的叫声,原本便是譬喻语言的难懂。胡适的观点是:“然而苏白却不是《海上花》不风行的唯一原因。《海上花》是一部文学作品,富有文学的风格与文学的艺术,不是一般读者所能赏识的。《海上繁华梦》与《九尾龟》所以能风行一时,正因为他们都只刚刚够得上‘嫖界指南’的资格,而都没有文学的价值,都没有深沉的见解与深刻的描写。这些书都只是供一般读者消遣的书,读时无所用心,读过毫无余味。《海上花》便不然了。《海上花》的长处在于语言的传神,描写的细致,同每一故事的自然发展;读时耐人仔细玩味,读过之后令人感觉深刻的印象与悠然不尽的余韵。鲁迅先生称赞《海上花》‘平淡而近自然’。这是文学上很不容易做到的境界。但这种‘平淡而近自然’的风格是普通看小说的人所不能赏识的。《海上花》所以不能风行一时,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海上花》初版不够风行,1922年清华书局翻印,也是昙花一现。到1926年,胡适发掘出来,与刘半农合力推荐,由亚东书局出版,但依然风行不起来。张爱玲很喜欢此书,她说,“中国的小说发展到《红楼梦》是个高峰,而高峰成了断崖。但是一百年后倒居然又出了个《海上花》。”她还特意将吴语翻译过来,她说,“我等于做打捞工作,把书中吴语翻译出来,像译外文一样”,于1982年4月至1983年11月在台北皇冠杂志连载,1983年11月皇冠杂志出版单行本,算是第三次推介。情况如何呢,皇冠本我们无从知晓,2009年新经典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将其收入《张爱玲全集》,似乎卖得不错,但这并非《海上花》使然,而是借张爱玲的名气,“夹带”在一起形成的效应。喜欢它的固然喜欢,不喜欢它的依然不喜欢。正如胡适所云,“当日的不能畅销,是一切开山的作品应有的牺牲;少数人的欣赏赞叹,是一部第一流的文学作品应得的胜利”。好东西虽然有自己的命运,但它的不够大众也是必然。
胡适先生的话,或许可以作为“好书”问题的一个权威说法。正如胡适所说,一般大众,如果还看书的话,也不过是消遣,“读时无所用心,读过毫无余味”,当下的大众阅读甚至所谓有文化的人的阅读,已经不肯在意胡适所谓的玩味,以及“读过之后令人感觉深刻的印象与悠然不尽的余韵”,至于鲁迅先生提到的“平淡而近自然”,从来就是一种境界,如今更加不合时宜,阅读者不屑于此,写作者也不肯为此努力。这便是客观的实在,自然也便是“好书”不得好卖的纠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