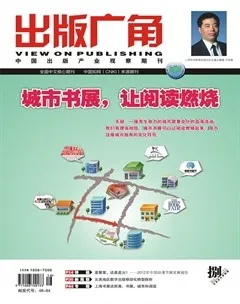上海书展近距离:书展、城市和阅读
在泛娱乐化和信息爆炸的今天,一个人如果只是单纯地希望消磨时光、获取信息,有太多手段和方式可以满足,而当一个读者走进书展打开一本书、坐下来倾听一场讲座,无疑是怀着陶冶自我、提升自我的真诚愿望,再加上整个城市的文化环境和人文素养,最终促成这样一场热烈的文化盛典。
上海书展像极了上海这座城市。既海纳百川,又坚持文化品格和品质;既一脉相承,又不断突破自我,推陈出新;既名家荟萃、大雅齐集,又百姓节日、倾城同欢。每年八月,热切的读者冒着炎炎酷暑,在上海展览中心门口排成长龙,购票入场,只为一年一度与心仪作者、作品重逢或相遇,这是多么让人感动的画面。在泛娱乐化和信息爆炸的今天,一个人如果只是单纯地希望消磨时光、获取信息,有太多手段和方式可以满足,而当一个读者走进书展打开一本书、坐下来倾听一场讲座,无疑是怀着陶冶自我、提升自我的真诚愿望,再加上整个城市的文化环境和人文素养,最终促成这样一场热烈的文化盛典。
2013上海书展十周年,参展出版社超过500家,各项文化活动超过600场,到场海内外知名嘉宾超过900人,多年打造的上海国际文学周、书香中国阅读论坛、学术出版上海论坛等文化品牌获得业界广泛认可,“我爱读书,我爱生活”日渐深入人心。书展十年,浸透着行业最优秀人才的智慧和心血,一路走来,迈过荆棘坎途,终见朗日荣光。虽然作为上海书展的亲历者,谈起书展有太多话可说,但本文无意为上海书展作总结,而是希望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浅谈网络化、信息化环境下为什么需要书展,需要什么样的书展,以及几点自己的思考,求教于前辈和同行。
一、今天为什么需要书展
书展究其形式,无非是物质产品的集中展示和销售。当年上海书城筹建,口号就是“永不落幕的书展”。然而,随着电商和网络快速发展,规模已经无法为书展带来稀缺性。上海书展受场地所限,能够容纳的品种数在15万种左右,而当当的SKU(Stock Keeping Unit,最小库存单位)超过百万,其中纸质图书约70万种,电子书约5万种;京东、亚马逊的SKU还要多于这个数量。从价格角度比较,上海书展提供全场八折的优惠,不仅无法和电商疯狂竞赛的活动价、血拼价相提并论,也不及一般时段电商的平均折扣促销力度。然而,上海书展却并未门庭冷落,反而持续激发市民参与热情。2013年书展期间全部开放夜场,周末更将开放时间延长到晚10点,展馆内仍然人潮如织,价格较高的出版物如定价近千元的《新版十万个为什么》日销超过500套,书展结束前,大量单品种图书售罄脱销。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上海书展如此火暴,或者说,在高度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市民为什么还需要书展?
从读者的角度看,上海书展的成功类似于iPhone——提供最佳用户体验。具体来说,仪式感、信息有效到达和精确投送、互动体验和文化认同,构成了书展相对于电商的稀缺性,成为书展的竞争力核心。
首先是仪式感和现场感。较短的排队购票时间和较低的票价设立了一个门槛,成功把真正关心阅读、热爱阅读的人群筛选出来,读者通过长长的、带有清凉喷雾的遮阳篷,步入具有鲜明苏联建筑风格、巍峨雄壮的上海展览中心,在高高的穹顶下置身漫漫书海和读者潮中,所有书籍随手可取、随卷可阅,从视觉、感觉和心理上同时带来强烈震动,自然触发读者正面情绪和感受。许多老读者把到上海书展的感受描述为“过节”,这从购票到入场的一段路,正是节日特有的仪式感。
其次是信息的有效到达和精确投送。虽然电商网站SKU以百万计,但受到屏幕分辨率和人类的视觉双重制约。人类没有昆虫那样精密的复眼,只能同时观察有限事物;一个网页的展示容量有限,通常一个屏幕内主要呈现的商品在12件左右,一个网页能呈现的商品在100种以内,而一个0.75米书架的上架图书品种数在48种左右,一个平方米展台的展示图书品种在26种左右,读者在一个展位内停留两三分钟时间,数百种图书涌入眼底,开本、纸张、色泽、质感一目了然,再花30秒钟取下中意的图书,看作者、看书前书后的推荐语、略翻一下内容,就能大致决定是否购买。行业内“报卖一个题,书卖一张皮”的俗语,准确描述了从信息投递到作出购买的“快速通道”。这就形成了一种有趣的现象:由于购书是典型的或然购买行为,大多数读者并不像逛超市一样对要买的商品有清晰精确的预见,而是一个搜寻到发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书展反而对以网页展示为主要销售手段(移动设备展示方面局限性更大)的电商形成信息优势。再辅以合适的信息传导,比如作者签名、编者讲座,甚至只是工作人员的几句推荐,都能让读者迅速得到有效指引。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有效指引对大多数专业并非文化行业的读者来说尤为重要,根据《上海市民阅读状况调查(2013)》,有约21.5%的受访者认为“缺少读书氛围”或“不知道该读什么”是影响阅读的主要原因,而书展上信息密集、有效、精确投送则完全解决了以上问题。
最后是作者、读者直接互动带来的愉快体验,折射出深度文化认同的强烈需求。上海书展海内外名人、嘉宾超过900人,既有年轻人热捧的演艺界明星,也有陈佳洱、欧阳自远、周忠和这样的两院院士、大科学家,既有儿童文学新秀,也有贾平凹、苏童、阿城这样的文学大师。和自己所崇拜的作家见面、倾听他们的讲座、得到他们的签名合影,无疑能让“粉丝”兴奋激动;当“韩粉”排在“一个”签售会的长长队伍中,当知青坐在梁晓声讲座的同龄人群里,谈论共同的话题、寻找共同记忆,得到的显然远比一本书、一个故事要多得多,这是深度文化认同需求的满足,是BBS、SNS等线上读书小组所不能取代的。
二、明天书展会怎样
上海书展物理空间有限、时间有限,在已经把“书”和“文化活动”做到近乎完美的基础上,讨论需要什么样的书展,其实仍然无法绕开网络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在《新闻周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这样名报刊都放弃出版纸质版的今天,很难想象,书展会在未来继续成为印刷品的盛宴和狂欢。我想,书展要继续发展、继续突破自我极限,应当突出“科技”“人”和“多元化”三个因素。
“科技”应当是今后书展乃至书业的首要关键词。即使笔者这样的深度纸质产品爱好者,也不得不承认数字阅读的确优势众多。Amazon创始人贝佐斯(Jeffrey Bezos)2.5亿美元买下《华盛顿邮报》以后,关于纸质报纸的命运又掀起新一轮口水。其实,报业将死已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专业媒体、专业出版的命运如何?互联网普及和新媒体兴起,挑战的并非传统新闻出版业如何转型,也不是如何运用新技术建立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正常社会对专业新闻、优质内容有永恒的需求,不正常的社会更加如此。有需求就有市场,专业人士终将创造出商业可持续的内容生产模式。真正的挑战来源于竞争图景的改变,首先是区域垄断被打破,书业开始全国竞争;然后是世界范围的优质内容资源争夺;互联网兴起,意味着专业人士以外的人也加入竞争,并且迅速成长为新的专业人士(比如已经成为文学新门类的网络文学),网络赋予了每一个人生产内容并传播的权力。这带来了最根本的挑战,每一个出版人都应当反思并且重建出版专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全体专业人士竞争,和全体非专业人士竞争,只有第一流竞争者能够生存,平庸就会消亡。作为书业的集中反映,书展理应体现数字阅读、数字出版的发展,尤其是出版人重塑自身竞争力的探索和实践。出版人尤其不能为纸质出版物的热销而陶醉,据说庞然大物如恐龙,踩到水桶那么大的东西,要几个小时感觉才能传导到大脑。我想,我们不应当作恐龙。
出版业并非关于书的行业,而是关于人的行业。书展要真正成为“百姓节日”,就应当更加重视“人”的因素,尤其是更加重视普通市民的因素。书展上人情味越浓、普通人的故事越多,就越容易被读者接受和认可。2012年起,上海书展全体工作人员送别最后一位读者,并颁发荣誉证书和纪念品,就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举措;同样2012年,译文出版社一名工作人员在书展现场向女友求婚,获得现场观众动情祝福,两人五年前在书展相识、相恋,终成眷属,成为当年书展的一大感人场景。出版人比较容易陷入单向传播的思维,即我掌握知识,想办法传授给别人,而不太容易主动寻求双向传播的局面。书展要能够真正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成为市民生活和记忆的一部分,就应当让市民的声音表达出来、让市民的故事讲述出来,要提供和创造一些这样的渠道、措施、平台,让书展不只是文化的传播授予,更是个人生活的坐标、成长的印记。
中国近代出版肇始于国家危亡、民族危难之际,出版人以启蒙民众、救国救民为己任,这种基于理想的出版理念和美国基于职业的出版理念形成鲜明对比。老一代出版人如张元济、王云五、陈原,不但是大出版家,也是大学问家;而瑟夫、西蒙、舒斯特几位美国出版家,则大多是富家公子。中国出版发展到现在,大部分出版人仍然秉持高尚的出版理想,对学术出版、专业出版更加看重,对一般大众出版则相对不那么重视。易中天先生曾表示,“读书无用”,即读书是为了提升自我,不是学手艺、学挣钱,不是为了现学现用。这样的观点当然有道理,但一方面实用类图书的的确确效用昭彰,对一个初为人父的读者来说,《育儿指南》要比《资治通鉴》重要得多;对一个家有宠物的读者来说,《宠物饲养》比任何其他书籍都紧要迫切;另一方面,能够看得懂专业著作、学术著作不仅需要读者有相当欣赏水平,更需要有较好的家庭和教育基础——也就是需要一些好运气。于是,一位读者如果读不了《四书章句集注》而读于丹女士的《论语心得》,仍然不失为了解传统文化的敲门砖。更何况,一些专业作品和学术作品粗制滥造,对社会的益处远不及一本《电工手册》。书展活动中,群众活动、普及活动数量不少,但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和支持,出于多元化、提升市民素质的需要,应当更多安排、更加重视一般群众活动和普及类的活动,眼光向上,姿态向下。
三、两点其他的思考
本次上海书展创设实景版书店展区,晓风书屋、季风书园、钟书阁、大众书局等民营书店都实景展示了自己店面的情况。站在实景书店区域,读者人潮汹汹,季风书园中几无落脚处,这和笔者几天前在季风华师大、上海图书馆两个店看到的情景大相径庭。季风华师大店由华东师大免费提供场地和水电费用,但由于门可罗雀,仍然亏损经营;新迁址后的上海图书馆店也不乐观,除了下班客流高峰期,晚上8点后读者也屈指可数。近年来,随着物业价格上涨和人工、运费等成本上升,实体书店经营出现困难,上海率先出台扶持实体书店配套政策,从资金、政策上对专精特、中小微实体书店进行扶持,但实体书店自身经营状况如何,仍然是决定书店生死存亡的核心要素。书展推出WIFI覆盖、导读导购、快递寄存、书香有礼、手机充电、餐饮便利等方便读者的举措,深受读者好评和欢迎。比如前文提到的《新版十万个为什么》,码洋高达1000元,重量超过30斤,超过一般读者体力所及。如果没有免费快递服务,很难想象其会成为热销品种。书展推出的种种服务举措,有多少实体书店能够借鉴,有多少能够进一步深化,成为实体书店吸引读者、改善经营的手段,值得认真思索。
另外,如何调动参展商积极性,也值得深入思考。上海书展展位免费提供,出版社无需支付场租费用,可谓已经十分优惠。但是,毕竟七天全夜场的高强度工作需要工作人员来维护、服务,一些工作人员因劳累而精神懈怠,甚至转化为不满。应该看到,书展倡导阅读氛围、引领阅读风气、培养阅读习惯,对全行业、全社会而言都是好事,为什么还会有不满意呢?那是因为,工作人员的工作不能直接体现为收益,参展商的努力没有直接体现为业绩。物不平则鸣。如何让工作人员、参展商的工作体现出来呢?这涉及国有企业考核、绩效评估和资产管理的问题。出版虽然是文化领域中改革最早、改革推进最快的领域,但和经济领域改革相比,资产关系、人员关系仍显僵化。通过改革和转制,市场开始在一些领域的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生产力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解放;但是,旧的行政管理模式和资产运作模式仍然大量存在,出版单位的经营自主权并未逐步放大,反而逆势缩小,市场信号被严重扭曲。反映到工作中,工作人员对各项工作缺乏热情和积极性,出版单位对转型突破、创新发展缺乏勇气和自主权,越来越成为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体制障碍。如何突破这些制度障碍、迎来新闻出版业生产力的更大解放,创造出更多、更优质的内容产品,值得全行业共同思索。
(作者单位:上海新闻出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