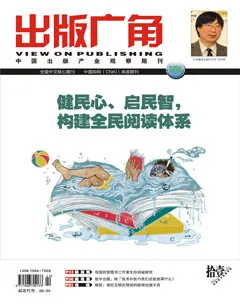衣服与影像
衣服和影像里蕴含着历史的玄机,有时甚至是乾坤性符号。看来,今后有必要留意一下那些注定史上留名的人物穿什么衣服,那是替历史多看两眼。
丁玲和王剑虹离开家乡后,就在上海、南京漂着。据沈从文《记丁玲》所载,在南京,“两人既同些名人来往,照流行解放女子的习气,则是头发剪得极短,衣服穿得十分简便,行动又洒脱不过(出门不穿裙子的时节次数一定也不少),在住处则一遇哀乐难于制驭时,一定也同男子一般大声地唱且大声地笑。两人既不像什么学生,又不像某一种女人……”因此,还遭到住处某一“同乡”的驱逐,她们自然是毫不客气地反击。这是青春叛逆期的丁玲形象。
王剑虹去世后,丁玲来到北京,认识了第一个丈夫胡也频及其朋友沈从文。沈从文第一次见到的丁玲,穿了一件灰布衣服,穿了一条短短的青色绸类裙子。未曾恋爱过的沈从文对于这个圆脸长眉的女孩子充满迷惑,但并不认为她有多大女性魅力。《记丁玲》写道:“她也许比别的女子不同一些,就因为她不知道如何去料理自己,即如女子所不可缺少的穿衣扑粉本行也不会,年青女子媚人处也没有,故比起旁的女人来,似乎更不足道了……她无时髦女人的风韵,也可以说她已无时间去装模作样的学习那种女性风韵。她容易使熟人忘掉她是个女人,不过因为她没有一般二九年华女人那分浮于眼眉形诸动止轻佻风情罢了。”这时候丁玲已经是一个“凝静看百样人生”的女孩子。
丁玲写的莎菲像黛玉,而且莎菲有她的自我投射,实际她本人至少外在上并非如此。丁玲年轻时有一张明星照,是去上海电影公司试当演员的产物,这段经历她已写在处女作《梦珂》中。沈从文记述:(导演)为她恳切说明“一个明星所必需的天分与忍耐”,又曾为她换过一套照她自己说来“做梦也不会穿上身”的华丽丝绸明星长袍,在摄影架前扮成人所习见又俗气又轻佻的海上明星姿势,照了一个六寸单身相片。电影梦当然破灭,原因从沈从文说她的“不能如贵妇人那么适宜于在客厅中应对酬酢”,可以想见。
这是莎菲时代的少女丁玲。
结婚后,为了生计,胡也频到济南教书,丁玲去找他。当年见过她的人回忆:“她的身材不很高也不很矮,有点肥胖,穿一件宽大的蓝布长衫,但从衣衩中,领口外,可以看出,她里面穿着西式衣裙。她粗眉大眼,圆脸孔,微笑得甜蜜。”(吴似鸿:《怀念我们时代姊妹——丁玲大姐》)可见,初为人妇的丁玲还是洋气的。
胡也频成为左联烈士,1931年4月,新寡的丁玲由沈从文陪同,将几个月大的儿子送回湖南老家,由母亲照料。看这时候丁玲跟母亲和儿子的合影,穿的还是不错的,皮鞋、丝袜、西式连衣裙。胡也频的去世是瞒着丁玲母亲的,为防露馅,丁玲只在家待了三天。这三天中,丁玲夜夜咬着被角默默流泪;白天却穿了她母亲喜欢的衣服,极力学做一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子。
回到上海的丁玲踏上了胡也频未竟的道路,她参加了左联,除了主编《北斗》,还参加左联的群众活动。此时的丁玲穿起布旗袍、平底鞋,到工人中开展通讯运动,到旧书摊做社会调查。这是到女中讲课的丁玲:穿着虽然较洋气、时髦,但并不华丽、庸俗。旗袍的颜色素淡,穿高跟皮鞋,外套一件素色秋大衣。这种打扮,跟社会上普通的知识妇女差不多,但她没有搽脂抹粉。之所以比较讲究,是因为这所女中是外国人管理的。丁玲打扮为阔太太是为了掩护身份,她参加左联活动的形象应该更贴近女工。
丁玲与冯达生活到了一起。沈从文从外地到上海,丁玲来看他:“有人拍我的门,门开后,一个胖胖的女人,穿了一件淡蓝薄洋纱的长袍,一双黄色方头皮鞋,在门边向我瞅着。如非预先约好,我真想不起就是她。若这人在大街粗粗的一眼瞥过,我是不会认识的。我们还只分手一年,好像变得已太多了……看看她那身装扮,我有点儿难过,说了一句笑话:‘一切记忆还很年青,人也不应当比印象老得太早!’她便苦笑着说:‘我什么时候年青过?’”(沈从文:《记丁玲·续集》)丁玲当时虽投身于伟大事业,并不多么注重女性美,但沈从文的反应显然还是令她发窘。这是左联时代的丁玲,也是丁玲的少妇形象。
真正成为革命女性是丁玲到陕北红色根据地之后。尽管丁玲的女性意识并未消泯,她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可以佐证,但从外在上看,她的女性指数正在退化,她已经不再是穿西式裙子的女士形象了。这一变化既是战士化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又是内在精神为革命所“改造”后的外化,她被视为“克服了母性的中国新女子”。
一张1938年春丁玲与萧红、夏革非在西安的合影,令我感慨颇多。萧红还是淑女形象——包括中式棉袍、皮鞋、长筒袜、围巾、齐齐的头发以及表情气质,而丁玲给人的感觉是气质变了,一副乐观的大老粗的表情,着装更不用说,身披黄大衣,头戴棉军帽,大衣不仅过大,而且披得相当随意,软软的棉帽不知是小了戴不进去,还是随便往头上一丢的结果,松懈地扣在头上,看起来很外在于她的样子。看起来,萧红还有女孩子的典雅气息,而那个沈从文笔下“凝静看百样人生”的丁玲完全不见踪影了。身穿日本军呢大衣的丁玲还把八路军缴获的战利品,一幅皮裹腿,送给萧红作纪念。当时的丁玲就是经常打着裹腿的,她与萧红不一样。而萧红代表着过去的丁玲,从萧红身上可以看见丁玲的来处,那个来处是一类人——原本的丁玲萧红们的所在。裹腿是战士的装束,丁玲把这幅裹腿看得弥足珍贵,但萧红却未必以为然,以萧红那样的装束,这幅裹腿往哪打呢?
当时见过丁玲的人,很多都提到她的日本黄呢军大衣,这件军大衣,似乎是那一时期的丁玲的符号。这件大衣是有来历的:1937年11月,西北战地服务团慰问参加过平型关战斗的八路军115师685团时,杨得志团长送给每人一件日军黄呢大衣。革命的中心在江西时,丁玲就向往到红区去,这是她不变的梦想,到陕北,穿上革命的军装,对她来说意味着梦想的实现,所以她格外看重这身军装。军装,可以使“武将军”的封号更加名副其实,这可能也会强化她对戎装的热情。军装是革命身份的象征,杨得志团缴获的日军黄呢子大衣,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得到的,它是革命队伍内部一个较高段位的象征。那时的延安同志穿的,一般都是打补丁的灰布军装。黄呢子大衣与打补丁的灰布军装相比,当然是一件好衣服,而且这件好衣服的象征意味又如此之好,丁玲怎么能不自豪地穿在身上呢?即便不是御寒的需要,也可能不舍得让它离身。
那一身穿着的丁玲在萧红面前,简直像一个村支书,尤其那顶棉帽,让现在的人很容易想起赵本山式的软帽盖。可是,丁玲丝毫没有自惭形秽,相反,她很自豪。固然,当时陕北物质上的匮乏,可能使丁玲顾不上好看不好看了,但从主观上来说,丁玲会觉得这样好看吗?很可能,她真的觉得穿戎装的自己很美。美和好看是两个概念。革命本身就是有底气的,革命美(或曰政治美)胜过一切时尚,所以丁玲自信是美的,这一点,只要想想江青“文革”中的穿着,想想新中国前三十年军装的吃香,就可以了然。丁玲在萧红面前的自信和对自我形象的满不在乎,源于她是革命的主人、革命之地的主人,而萧红是客人;源于革命美超越于一切美之上,一旦拥有它,女性美就是等而下之了。或许,萧红的装束在丁玲看来,是有些资产阶级的,需要嘲讽的,正如资产阶级太太冬妮娅在无产阶级的筑路工人保尔面前一样。《风雨中忆萧红》一文中,对于此时苍白脆弱的萧红,饱满强健的丁玲是隐含悲悯的,她遗憾萧红没有如自己一样加入到革命洪流中来,并含蓄地将其解释为萧红苍白脆弱的原因。丁玲对于历史、对于革命、对于自己和他人,误解实在是太深了。
变的不仅是丁玲的形象气质,她的文学感觉同样在变,变得粗糙。是外在带动了内在,还是内在带动了内在?
到了土改的时候,丁玲已经可以坦然地和一些邋里邋遢、身上长虱子的老太婆睡在一个炕头上了。随着自身生活的工农化,丁玲看待女性美也是另一种眼光了。固然,她原本就不喜欢涂脂抹粉,但还没到视为丑恶的地步,而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当中,她写涂脂抹粉的地主的老婆,采用了漫画化手法,将女性美完全写成了丑态,甚至直接用“妖精一样的女人”这样的措辞来将其妖魔化。这个丁玲,已经变得让莎菲认不出来了。如若莎菲和梦珂拿到此时此地,一定会成为她改造的对象。她对长虱子的老太婆越是认同,对涂脂抹粉的地主老婆就越是不以为然,而这两种情感态度对于她来说,都是非常美的阶级感情,她可能很满意自己有这样的审美倾向。
被丁玲尊为师的叶圣陶在《悼丁玲》中回忆道:“再见面是1949年,我到北平以后。相隔十六个年头,她还是老样子,热情、健谈,只是服装改了,穿的灰布解放装;先前在上海经常穿的是西式裙子。”叶圣陶的印象是直接从上海到北京的,缺失了延安的过渡环节,所以会感到一丝突兀和诧异。这可能是国统区文人与解放区文人在1949年的北平照面时的典型感受。这一身灰布解放装会给沈从文这样的文人造成怎样的压抑感,也是可想而知的。这无疑是新中国主人的服装,它在向那些坐享其成的文人们发出这样的强烈暗示:我们,是革命胜利的缔造者。很快,连叶圣陶这样的文人都要自觉并自豪地穿起灰布解放装了。
此时的丁玲对于自己从前所属的小资产阶级面目有着足够的敏感和反感,这种感受与灰布解放装正好合拍。
到了北大荒和山西长治嶂头村,丁玲不单是认同农村老大娘了,干脆自己就变成了一副不折不扣的农村老大娘形象。痛楚的是,即便改造成这幅模样,丁玲仍然得不到农村老大娘们的认同和肯定,群众仍然表示不满意。
谈了丁玲这么多照片,真正让我惊呆的是丁玲1966年“文革”中被揪斗的照片。先是看到丁玲当时住的草棚的照片,心里就像被一堆草塞住,接着又看到这张被揪斗的照片,那令人恐惧的难堪,简直使我内心坍塌。照片中的丁玲头上好像扎着白布,也许是造反派做的高帽子,穿着老棉袄,胸前挂着一块牌子,牌子上书:大右派分子丁玲。她的脸被墨水画成了小丑,两颊挂下来,很难看。更难以面对的是她的眼神,那是倒了霉的人的空洞眼神,显示出内心的颓势和雾数,说明着落难的丑陋。如果莎菲看到这样一个丁玲,该怎样愕然,如何消受?无法想象!这张照片居然是陈明在文化宫楼上偷拍的!可见大浪淘沙的运动,给他们练就了多么顽强的抵御和消化羞辱的能力,以及多么无厘头的自嘲精神,使他们能够把自我游离出来,变成旁观者,看着自己的肉身受辱,仿佛在看别人受辱。
新时期终于到来了,丁玲终于回到了北京,却又成了“红衣主教”。如延安时期的黄呢子大衣成为丁玲的符号频见记载一样,晚年丁玲的一件红毛衣也成了丁玲的符号。
这件红毛衣最早出现时,丁玲曾穿起来让秘书王增如看。王增如是一个比较正统的人,但她接受老太太出格的穿着,并且佩服老太太“心里始终是年轻的”。丁玲晚年政治思想保守,但在生活观念尤其是穿衣打扮上,却一点都不保守。丁玲是身体力行的,她的红毛衣俨然铁凝笔下那件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宣言一般存在着,引起周围的喧哗与骚动。这个红色的符号有时衍化为枣红毛衣或红围巾,被他人频频提起。丁玲不会不知道这有多么扎眼,会引起怎样的议论,但她依然“臭美”、张扬,毫不在意。拿到当下,这不算什么,当下的潮流就是越是老太太越穿红着绿,年轻人反而要深沉,但丁玲超前了不止一步。
1984年10月4日中午,朋友们提前为丁玲庆贺八十大寿,丁玲穿了一件枣红色毛衣,外罩黑丝绒马甲。四代会期间,丁玲延续了这一装束。这身装束注定要写进历史,据王增如记载:1984年12月29日下午,张光年作《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主题报告……主席台上寥寥无几,丁玲穿着件枣红色毛衣,格外显眼……第二天,香港的一本杂志就刊登了一篇对会内作家的访谈录,讥讽坐在主席台上的丁玲是“红衣主教”,是“左”王。这当然是借红毛衣之“红”,说丁玲之“左”。这个“左”王封号,从“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运动就开始了。终于,红毛衣符号与“左”王封号搭在了一起。
从莎菲女士到老年丁玲,从形象到气质的改变,足以说明丁玲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最佳范例。最后的一抹夕阳红,本可以在形象上来点突破,不意却被演绎成了“左”王符码,反而更加坐实了原有的形象认定。
丁玲一生的着装,从中式到西式,再到军装、工农装,基本上是一个性别泯灭、文人气质泯灭的过程,最后那件解放思想的红毛衣,也没能使她的形象真正解放出来。延安时期的戎装照,成为丁玲流传最广的照片之一。在丁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礼堂侧门旁,竖立着丁玲的一幅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丁玲在抗战时身穿八路军军装,打着绑腿的英姿。这张照片的选择隐含着革命的强调,说明女作家愿意用“革命女战士”来定位自己、总结一生?当然,这照片可能是别人选定的,那就反映了选定者的意愿。
我喜欢丁玲灵堂使用的那张照片,出自一位法国摄影师之手,它比较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丁玲老年的风华,不失女性意味,也不失作家气质。一生左左右右打转,一次次矫枉过正之后,最后是这个正本清源的样子,滤去了一切偏颇与误会,令人感到安适。
衣服和影像里蕴含着历史的玄机,有时甚至是乾坤性符号。看来,今后有必要留意一下那些注定史上留名的人物穿什么衣服,那是替历史多看两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