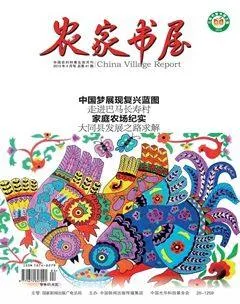何伟:用第三只眼看中国
1996年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第一次到中国,参与美国和平队在中国的一个支教项目, “坐着慢船”来到涪陵。在涪陵支教两年后,他于1998年冬回到美国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的海斯勒,找到了一份500美金的工作,当上华尔街日报北京办公室的办事员。1999年春,30岁的海斯勒又来到了中国,在中国一直生活了10年,由于对中国的深入细致的观察和记录,他在美国成了名,被誉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海斯勒为自己起了一个好记的中文名字——何伟,最初来中国时,他不是记者,也不是作家,只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诚然,《寻路中国》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游记。他说:“因为以前没有研究过中国,我对这里的人和物反而没有什么强烈的态度或意见。有时候你缺乏相关知识不是坏事,中国变化太快了,如果我1980年代真学了什么有关中国的东西,到1996年它也早已过时——中国已经变成另一个国家了。”
何伟曾回到美国后,在小学校里讲起中国的事情。小孩子问:“中国父母杀女婴吗?”“中国人吃狗吗?”他感觉很糟糕,“怎么两个问题都是这样子的?”他在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涪陵教书时,课本上对于美国宗教的介绍是有什么样的邪教,对于学校的介绍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凶杀案。他对学生解释,“这些事是真的发生的事,但它不能代表真正的美国社会。”他希望人们描述一个国家时,要讲清楚哪些背景,用时间去长期采访,“而不是简单告诉他们什么是最不好和最好的事情”。
在书中,何伟为我们讲述了他在中国寻路的点点滴滴的见闻,其中有一个章节是,他沿着长城一路向西,细致记录那边最后的村庄的故事。村庄里的许多人,已经明白更美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们想得到更多的、在外面或者电视上看见的那些实际利益,但却无法在时常变动的政策和环境下从容辨明方向。在向别的地方学习的过程中,与他们最亲近的环境已经失去了联系。在那些禾苗、灌溉水管和老年人的浅蓝色棉布衣服之UHgnHaCANwHZpEpJvsdJIuYDyQpdyZz3FYhh1BPwYcc=间,在“质朴而简单的美感”的贫瘠之地,人们要么跟自然较劲,要么离家外出打工,除此别无选择。
他越开车往前走,就越不明白,那些村庄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无法想象二十年之后,谁还会住在那个地方。现在的孩子,可能是那个地方的最后一代人。
“对于农村生活的艰辛,我并未心存幻想。不能把贫穷想得太美。不过,在驾车穿越这些即将消失的村镇的途中,我还是感受到了些许酸楚。那是我瞥见的最后一线生机——最后的小镇,最后的乡村少年,也许还有最后的家庭,兄弟姐妹俱全的大家庭。乡下人特有的诚实与信任,不会随着迁居入城而继续存在。在世界上,陌生人受到毫不迟疑的欢迎,赢得孩子们的信任,这样的地方并不多见。驾车离开安寺村的时候,我有些伤心。”
何伟曾在长城脚下一个偏远小村子的魏家租住过,老魏的孩子是一个精瘦的农村男孩,精力无穷,喜欢跟他打闹,叫他“魔鬼叔叔”。孩子上学之后,学校里没有零食,也吃不太饱,但一回到家,看到的是来旅游的城市人带来的方便面和薯片,每天写完作业,吃着垃圾食品看着电视,但母亲并不觉得怎样,她说,“孩子能吃永远是好事,电视不看就浪费了。”孩子肚子已经滚圆,腿上长出赘肉,稍跑几步就气喘吁吁。何伟希望他能多吃水果,但妈妈说,冬天不要吃水果,“不顺气”。她打量着儿子,挺满意:“他现在有点像城里孩子了。”
何伟说:“他们同时过着现代生活和传统生活,但他们同时抓住了这两种生活里最糟糕的部分。我并不反对进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摆脱贫困,也对这种适应变化的努力保持崇敬。但这个过程如果太快,是要付出代价的。”
中国的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着,没有几个人敢自夸自己的知识够用。大概是因为身在其中,反而熟视无睹,抑或自顾不暇根本懒于深究,身处这个急速前进时代中的大多数人,像熟悉了亲人的鼾声一样,坦然接受了城镇的巨变与喧嚣、工厂的繁荣和衰败,没有(来得及)发问事情的缘起,也错过了最好的记录时机。
所以,我们要感谢何伟。这个“向来喜欢应对在中国生活时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的美国作者,开着租来的City Special和Santana汽车,以可口可乐、奥利奥和佳得乐充饥,露宿荒野之间星空之下,常年居住在城郊小村,他用我们大多数人早已忘却的方式来亲近这片土地,帮助我们追根溯源,探究个人对这个年代变革所做出的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