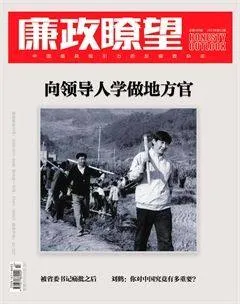出入教科书,也要讲政治
“任何一种语文教材,要想不体现国家意志,不体现时代精神,不体现民族文化,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次是鲁迅的《风筝》。
9月,新学期开学之际,众人发现人教版新编初一语文教材删除了《风筝》一文,舆论热议。
早在几年前,《药》、《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等多篇鲁迅的作品已被删除,被网友称之为“鲁迅大撤退”。
当然被删除文章的不止是鲁迅。曾任四川省乐山市教科所副所长的唐建新多年来一直是人教版课程标准初高中语文教材编组成员,他告诉《廉政瞭望》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1963年、1988年、1992年、2000年都进行了教材修订,增删文章。其中涉及的作者众多,只是“这次是比较大的调整。”
每次调整,谁进谁出绝不简单。
鲁迅一直做减法
上世纪20年代,鲁迅的《故乡》、《风波》、《风筝》等就已经被一些学校用作教材。
新中国成立后到1966年入选教材的鲁迅作品有31篇;到80年代减少为28篇;到90年代中期以后,维持在15篇左右。
但目前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中,鲁迅的文章只有6篇。
进进出出教材的并非鲁迅一人。国家并没有关于修改教科书期限的规定。但一般来说,教材每隔一个周期都要进行一次大的调整,一来吸收新的文学成果,二来紧跟社会变化。
此次人教版语文教材删掉的文章就有9篇,除了鲁迅之外,还有郭沫若的两首诗:《天上的街市》、《静夜》,以及流沙河、张晓风、玛丽·居里、梁衡、周国平等人文章。
新增的文章则有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魏巍的《我的老师》、贾平凹的《风雨》等。
入选教材是一种荣誉。+Ui1W4EFPdtjH7fADzivtA==马及时的《王几何》入选后,每天致电他通报好消息的,要求请客的,预约合影的,数也数不过来。这让马及时不禁感叹:“教科书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
当然,“任何一种语文教材,要想不体现国家意志,不体现时代精神,不体现民族文化,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唐建新称。
谁来决定进出?
正因如此,每次修订,谁进谁出都有一个复杂的过程。
纪昀的《河中石兽》此次入选教材,属于“新课标要求的,应该编入”,唐建新称。当然并不是每篇文章都是如此。
更常见的情况是增删一篇文章,首先要过出版社这关。
“教材修订要经过编辑室小组讨论、社内讨论和外部审议。”编辑了“文革”后所有人教版中学语文教科书的顾振彪称。
现在大多数出版社实行的是主编负责制,但有时他们的意见并不总是起决定作用。
1992年和1997年,人教社两次修定教材,《春末闲谈》、《阿长与山海经》等入选。时任编委温立三就认为这些文章“有一半存在问题,或背景过于复杂、或过于艰深、或语言过于晦涩,但另一半却富有现实意义。”
教材修订完成后,需要上交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这是一个由教育部聘请的专家、教师和教育行政领导干部组成的专门机构,在谁进谁出的问题上,它拥有极大的决定权。
2002年,审定委员会对语文出版社递交的八年级(下)教材就大加赞赏,称增加《苏珊·安东尼》一文,是对教材克服“性别歧视问题”的重大突破。
当然,也有否定的时候。“审定委员会有时会提出很大的修改意见,但对于鲁迅的文章却从来没有提出异议。”顾振彪称。
2001年之后,随着国家允许各地方自编教材,审定委员会不再只有教育部一家,大部分省市都成立了各自的审定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权力相对较小,审定通过的教材只能在当地使用,不能全国流通。
审定委员会之后,还需要教育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谁进谁出才最终定下来。
有时教育部也没有最终决定权。据媒体报道,人教社编写的第四套教材在使用半年后,被毛泽东批判为“压得太重,摧残人”,要求“课程砍掉一半”。但未及修改,文革爆发。
1953年,苏联教育专家普希金娜到中国后,对当时的语文课题提出批评:不重视语言因素和文学因素,“政治说教”太多。由此,1956年“语文”课借鉴苏联语文课分为俄语和文学的做法,一份为二,收录了国内外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
标准何在?
1987年,当时的国家教委曾就教科书文章选择专门制定了标准,从思想性、科学性以及国情等角度进行了规定。
这些规定被现在各省市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沿用,但文章选择的标准从来都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
1935年,毛泽东在演讲中称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并给予“三家五最”的最高政治定位。此后,解放区的语文教材开始大量增选鲁迅的“战斗杂文”。
对出生于1950年的唐建新而言,自己当年学的初中课文至今保留下来的已经寥寥无几,他只能点出杜甫的《石壕吏》和鲁迅的《故乡》。
他曾经系统梳理了建国60周年以来的语文教材经典名篇,发现其中蕴含着强烈的时代特征和政治色彩。
建国初期的教材主要选用体现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解放区作品,如《小二黑结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进入60年代,课文选编主要体现战天斗地建设祖国的豪情壮志,如《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龙须沟》等;古代诗文则侧重在以阶级斗争角度挖掘的《窦娥冤》等,以及《愚公移山》之类适合当时改天换地战斗的文章。
“文革中的语文课就是学习背诵语录、老三篇,写大批判文章;到后期一些学校复课就上毛选、马恩列斯文章选、两报一刊社论、鲁迅作品选读等。”唐建新回忆。
据媒体报道,人教社第五套教材的编制更是来自邓小平直接命令,时当1977年,邓小平要求尽快编出一套统一的中小学教科书,从1978年秋季起供应全国。该套教科书确立的指导思想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
在90年代语文教材中,一些世界文学经典名篇开始入选,如《罗密欧与朱丽叶》、《门槛》等,而《等待戈多》、《变形记》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黑色幽默作品,第一次进入中学生视野。
由于政治见解或创作风格一直被拒之课本外的作者也开始出现,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何满子的《剃光头发微》等。
21世纪以来,初中语文教材基本删除了纯政治说教的政论文以及领袖讲话文章,吸纳了许多海外作家作品,以前由于某些原因未能入选的胡适的《我的母亲》和戴望舒的《我用我残损的手掌》等作品,也进入了课标语文实验教科书。
北京太阳村周末的喧嚣让张德龙很不自在,在没有被安排任务的时候,他更愿意躲在房间的最深处。
周一至周五,他生活在一群和他有着同样身份的孩子中间,在彼此眼中,他们与正常人无异。但周末,他们则会被冠以“罪犯的子女”这一标签,与来到太阳村的爱心人士们“相处”,这让他感觉很不自在。
孤独少年们
16岁的张德龙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河南洛阳。每年暑假,太阳村的老师会带他去一趟洛阳,看望在监狱中服刑的爸爸。探亲之旅,是他一年中难得走出太阳村的时候。
张德龙并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送到太阳村的,从太阳村自办的报纸上看到,自己来此的年龄是5岁。儿时的记忆便是这些有着彩色屋顶的简易房,以及和他有着同样身份的伙伴们。
太阳村有着严格的生活规律,早上6点起床、6点半吃饭、7点上学,中午12点吃饭、1点半上学……工作人员的哨声是最严格的指令,10多年的时间内,张德龙在哨声中数着日子。
生长环境的闭塞,让张德龙沉默寡言。他的室友,18岁的周晓前不久离开了太阳村,到北京昌平一所技校学习。这让原本宽敞的寝室更显空旷。
在寝室的时候,张德龙大部分时间都是盯着窗外的菜地发呆。寝室的周围种满了蔬菜和低矮的灌木。
当有爱心人士突然“闯进”时,张德龙会随即端坐好,之后手脚拘谨、不知所措。
不止张德龙,不善沟通是太阳村大多数孩子的共性。
在太阳村,孩子们说得最多的两句话是“叔叔好”和“阿姨好”。太阳村的工作人员承认这两句话是他们要求孩子们说的,“来这儿的人都是来帮助他们的,见到以后向这些爱心人士问好是必须的。”
但问好后,孩子们的目光会不自然地躲闪。
13岁的康旭东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床上摆弄着一个发夹,神情专注,全然不顾来来往往的陌生人。这个18平方米的寝室中有三张铁制的上下床,除康旭东外,还有另外5个女孩在这居住。6个女孩的床铺非常相似,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被子旁边统一放着一个由爱心人士捐赠的毛绒玩具。
由于害怕孩子在太阳村以外的地方发生意外,儿童部的老师严禁任何人和团体将这些孩子带离太阳村,所以和张德龙一样,康旭东的记忆里只有太阳村。当爱心人士来到她的寝室并试图对她的生活进行更多了解时,点头、摇头和几句简单的“是”“不是”“喜欢”便是她所有的表达方式。
对于孩子们现在的状态,太阳村接待处的负责人张正祥表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孩子们现在还小,等长大了有些事情自然而然就学会了” 。
被遗忘的群体
周末,来自北京市区和其他省市的爱心人士和团体会带着大米、衣物等物资奔赴位于顺义的太阳村。将捐赠的物品在特定位置摆放好后,剩下的搬运工作则交给太阳村的孩子们来完成。
14岁的李林熟练驾驶着电动三轮车将这些物品搬运到工作人员指定的仓库,几个来回下来,他的额头和鼻子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有点累,但和去农场(农场是太阳村为了保证孩子们生存所创建的经济实体)干活比起来,这算比较轻松的了”。
去农场干活是太阳村孩子的“梦魇”,李林说完后,他身边的一位同伴立即附和:“一想到去农场干活,我就害怕。”
李林的说法得到了农场场长刘海晨的证实,“夏天活比较多,工人们忙不过来,就让小孩们也来农场干活,反正他们在暑假也没事做”。
为了快速将获赠的物资装进仓库,张德龙也被太阳村的工作人员安排到了搬运物资的队伍中。肥大的校服套在本就瘦小的张德龙身上,使他看起来愈发弱小,而将50斤一袋的大米搬到电动三轮车上,对他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2岁的张燕燕这周被安排的任务是卖鞋垫。
张燕燕所卖的鞋垫是太阳村的工人利用获赠的窗帘、床单之类的物品缝制而成的,有精美的花色和图案,5元一双,这在前来的爱心人士眼中很有新鲜感。
爱心人士们纷纷慷慨解囊,张燕燕忙乱地收钱、找钱。钱越来越多,手里拿不下了,张燕燕索性将他们放在了摊位的最里侧,闲暇的时候再一张一张地整理好,交给生活老师清点。
摊位前没人的时候,张燕燕会自顾自地低头轻声哼几句歌,当被问及是否愿意在太阳村生活时,歌声停止,继而沉默。
但除了在太阳村生活,他们是否还有别的选择?
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对父母服刑期间无人照管的未成年子女,并没有明确规定相关的监护办法、程序、监护主体及其责任。父母一旦进入监狱服刑,他们的未成年子女将陷入无人照看的境地。
“父母一旦被送进监狱服刑,孩子会变得非常可怜,政府又不管,最后只能流落街头。”原河南省女子监狱狱警王密说到。
这种现象在偏僻和比较穷困的农村地区更加明显,受困于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孩子的亲属根本没有能力抚养他们。
司法部统计的数据显示,我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高达60多万人,在太阳村生活的孩子算是这其中的“幸运儿”。
明天在哪里?
张德龙正在读初二,在他眼里,太阳村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有两条出路,第一是回到户口所在地参加中考、读高中,学费、生活费继续由太阳村支付;第二则是继续留在太阳村,初中毕业后去读技校。
在太阳村生活的孩子大多数是外地户口,有些甚至没有户口,按照规定他们不能在北京参加中考。而独自回到空无一人的家,在陌生的故乡备战一个人的中考,对他们的身心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年幼的他们还没有勇气去独自面对生活。
而且多年没有回过位于河南三门峡的老家,张德龙自己也不清楚老家现在还有哪些亲人。
在他眼里,第二条路更适合他。
目前,张德龙已经是太阳村中年纪比较大的孩子了,和他一块长大的“哥哥姐姐”们初中毕业后,便在太阳村相关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先后到顺义、昌平的技校去学习谋生的技能。
“这些孩子初中毕业后,我们会把他们送到职业学校学习会计、数控、酒店管理等技能。从技校毕业找到工作后,他们便能自己照顾自己了。”太阳村儿童部的苏老师表示。
从技校出来后,他们大多被分到了北京郊区的电子厂成为组装车间流水线上的操作工人,或去酒店从最底层的服务员做起。
18岁的赵磊在顺义的一家技校读了一年半了,过完年后,学校会安排他去北京郊区的一家电子厂工作。“管吃管住,每月还给1800元的工资”,赵磊兴奋地表示,这是他离开太阳村后,在社会上迈出的第一步。
比赵磊小3岁的张小森在蔬菜摊旁来来回回地转悠,这个周末他的任务就是卖菜,被问到以后想做什么时,这个男孩快速地摇了摇头说:“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菜摊上长达一米的蛇豆吸引了几个小孩子的驻足,他们是周末被父母带到太阳村来接受“教育”的,在孩子的央求下,这些父母们向张小森询问这些“蛇豆”的价格。之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临近中午,爱心人士们纷纷散去,张小森又像刚刚一样,在菜摊旁转悠,为自己寻找乐趣。“张小森,你有卖菜的样吗?”在距离菜摊四五米左右的地方,太阳村一位工作人员提醒到。听到提醒后,张小森迅速坐回摆放在菜摊后边的板凳上,神情专注,时刻准备着招呼下一位顾客。(文中服刑人员子女全部采用化名)
由于害怕孩子在太阳村以外的地方发生意外,儿童部的老师严禁任何人和团体将这些孩子带离太阳村,所以他们记忆里只有太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