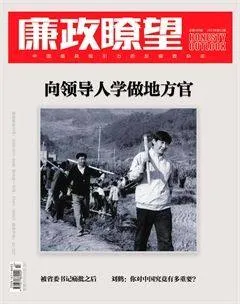于建嵘惹谁了?
相对于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这个颇为拗口的名头,于建嵘更出名的是微博名人、进京上访户的倾诉对象、“微博打拐”和“随手公益”发起人。
最近,他又添了一个新身份——“村官”。9月15日,于建嵘赴贵州省兴义市则戎乡安章村担任村主任助理,任期两年。“一间不到10平米的红砖小房、一张床、一张书桌,这算是暂时安在安章村的家”。
谁知,没多久,于建嵘就把当地给“惹毛”了,国庆期间回到北京,闲门谢客,完成了两幅大瀑布油画初稿。
有人称这是双方谈不拢的暂时搁置,10月7号晚上11点左右,于建嵘在微博中报以笑对:“虽多有无奈,但还不致于这么消沉。这次闭门画画,是因答应了一位中欧学院的同学。”《廉政瞭望》记者多次拨打于建嵘的手机,均一直处于关机状态。一名于建嵘的好友对记者表示:“在这个(敏感)时期,老于真的不好说什么。”
“他在单干”
国庆长假最后一天的下午,当不少人正在为返程拥堵焦虑时,于建嵘对外透露自己的焦虑:由于自己与则戎乡领导之间看法不一,他的纳具村发展计划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他困惑于地方政府在乡村建设规划上态度摇摆不定、前后不一。本来是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却遭遇了兜头一盆凉水。
距兴义市约20分钟车程,位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万峰林脚下的纳具村,是安章村下辖的一个自然村,也是于建嵘此次担任村主任助理期间的主要服务对象。
和大学生村官不同,进村第一天,于建嵘展现出了自己的“名人效应”,他不仅带来了他的研究团队,还有20多名从北京、上海、香港等地赶来的老板、朋友和建筑规划师。
一开始,于建嵘公开表示,本是希望这些朋友“有钱的投点资,有智慧的出主意,有技能的动手劳作”,“很多老板害怕当地取现不方便,都是直接带着现金去的。他们想为这个村庄做点事情,给这个寨子一些钱,总数大概在七八十万”。不过,于建嵘说:“我当时就拒绝了。”
当地一名官员向《廉政瞭望》记者提出自己的疑惑:“既然要拒绝,为什么又要大张旗鼓带着那些老板来?”
这名官员同时觉得于建嵘拒绝各方的支持,是在单干,有点“不能理解”,“名人到地方任职我们也见得多,牛群、王志一开始还不是都这样利用自身效应引资?”而在早些时候,于建嵘曾承认,安章村的一些干部的确希望他能引进一些项目;并且,他本人也有此考虑。
于建嵘的朋友王鹏曾表示过,挂职“村主任助理”的想法,是于建嵘提出来的。王鹏说,于建嵘觉得有这样一个“身份”,便于他帮助村子吸引投资,加快发展速度。
9月15日当天,黔西南州一名主要领导看到纳具村的沟渠凋敝得厉害,当即拍板要从财政上支援20万元,“整理一下沟渠”,于建嵘并没答应。
“我不用政府一分钱,不要政府的资源,绝不做形象工程。我的想法是,吸引社会资源到这里来,共同参与建设。”这是于建嵘的原话。
有评论认为,于建嵘作为一个关注农村问题的学者,他来挂职不会仅仅是为了发展一个地方,而是想探寻一种可以推广的经验。
但当地干部却觉得,“我们现在最缺的是发展,于教授这样的名人来了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没有钱,谈什么村民的公共意识,城市人的公共意识都不过尔尔呢?”
如此,于建嵘的雄心和当地想法从一开始便并非完全融洽。而更让他尴尬的是,尽管他已经“走马上任”了,但自己的村主任助理任命至今仍未获当地政府通过,显得有那么一点“名不副实”。
知识分子去农村
从1936年到2002年,在66年的时光中,费孝通对江村(即开弦弓村)进行了多达26次的深入访问,从《江村经济》到《乡土中国》,他通过一篇篇震撼世界的学术论文,让世界知道了江村这个地处中国江苏省东南一隅的普通江南小村,也树立了费氏社会学的国际权威地位。
2003年,温铁军也曾在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进行乡村建设试验,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但是批评声也从未间断。有的学者也怀疑温铁军所作的乡村改造是否真的有意义?一个村的试验是否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
其实,温铁军曾面临的问题,也是于建嵘正在面临的问题。
于建嵘在年轻时,曾沿着毛泽东当年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走过的路线,进行广泛的农村考察,并选择了湖南第一个农民协会发源地的村庄作为调查点。一年后,他写出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岳村政治》。
对此次挂职的村庄,于建嵘总结过3点:1.风景真美;2.村民真穷;3.村庄真衰败。他建议地方政府修复这里的原始村落,发展文化产业,让农民过上生态和富裕的生活。
正是对村里老房子的处置问题,成为于建嵘推动自己计划的最大阻碍。
9月17日下午,当于建嵘在纳具村大榕树底下和村民们座谈时,几位则戎乡政府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挂出一条写着“依法集中整治严厉打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落款为“则戎国土资源所”的横幅。后来,则戎乡政府的干部还曾对村民做工作,要他们不要把房子租给于建嵘带来的人。如果对方一定要租,就让他们直接和乡里打交道。
值得注意的是,当天上午,黔西南州州长杨永英曾赶来看望于建嵘,于建嵘和他的团队以及村支部书记查玉刚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10月8日,于建嵘在微博上回应了公众的关注:也没有太复杂的问题。分歧的关键是乡里官员要求农民把闲置废弃的房子先租给政府,再由政府转租给艺术家和作家;我的意见是,让农民自己与艺术家和作家谈,政府和村委会只是监督艺术家在帮农民修建房子时要保护环境和民族建筑风格。
政绩诉求VS学术诉求
曾有人问于建嵘,如果让你去做一个县委书记,你能干得了吗?于坦言,那不是我能做到的,话语中有几丝无奈。
这一次,按计划于建嵘的村主任助理的任期是两年。在“上任”之前,于建嵘曾为自己描绘过美好图景:“我不会一直在那个地方,必须是有限性的介入,以观察者的角色,通过和他们交谈,潜移默化地给他们提供一些规则和观念,看他们怎么变化。有时候保持一定的距离相反更能发挥作用。”
不过,一些关注此事等学者提出了忧虑:这个距离是多少,现实中并非可以准确丈量。
其实,早在于建嵘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歧暴露出来之前,就曾有媒体评论称,于建嵘到乡村挂职,只是一个开头,“乡村建设”这篇文章具体如何开展,既考验学者的坚持,也考验地方政府的宽容,更有赖于相关各方的磨合、认同程度。如何在当地政绩诉求与外来学者的乡建理念之间找到平衡,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新华网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仔细审视于建嵘的乡村计划就会发现,他的整个计划都是围绕“复兴村庄传统文化,为农民找到一条致富之路”设计的,其间丝毫没有照顾到当地政府的利益分配问题,这样的计划,自然不受当地政府的待见。
当地不少人就对记者表示,“村民是主动打扫卫生了,看似是受到了于教授的感召,但里面很大程度有新鲜劲儿的因素,劲头一过,还不知会怎样”。
据此前媒体报道,于建嵘曾拿出过2000元钱,交给村民们选出的一位村民手中,让他负责组织大家今后将村子里的卫生保持下去。
于建嵘坦言,“我不怕没有成就感,因为如果做不到重塑村民们的公共生活,让他们互助起来;做不到真正提高村民们自身的发展能力,才真正说明我的实验是失败的”。
对此,新华网观点是,于建嵘的乡村建设计划之所以停顿,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于教授对基层的了解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中国基层的复杂性,不经过深入其中的体察是难以切身感受到的。
至此,于建嵘的乡村计划宣告全面搁浅。
因王金平关说案引发的纷扰,还在台湾政坛持续。
回想事件之初,马英九亲自召开记者会,宣读了措词强硬的声明稿。他还在记者会上声色俱厉地痛批:“我们每个人可以问自己,如果这不是关说,什么才是关说?”
在台湾,“关说”一词不时见诸报端,普通民众自是熟稔。但在大陆,许多人却不明就里,对于“什么才是关说?”这一马英九之问,大多一头雾水。
关说就是说“关系”
与许多人的臆测不同,“关说”绝非台湾土话,而是语出《史记》。《史记·佞幸列传序》写道:“此两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所谓“关说”,是指用言辞打通关节、搞定某种关系。类似于大陆的“说情”、“打招呼”。
在古代,“关说”一词,经常出现在各类文章中。宋代的司马光在《上皇帝疏》中写道:“诚惧不幸有谄谀之臣,不识大体,妄有关说,自求容媚。” 明代何景明在《法行篇》中写道:“执豪侠之民,则公卿不得关说。”一个大陆已很少用的词,却在对岸被屡屡提及,可见传统文化在台湾的影响。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关说风气在台湾很是猖獗,甚至成为一种特异文化。在台湾,从乡民意代表、县市议员到“立法委员”,关说无所不在,层面从个人找工作、子女入学编班、医院门诊挂号、拆违建等,生老病死全包。
台湾关说文化盛行,也与民意代表必须下大力气做好选民服务有关。事实上,不少岛内选民认定“民代”很有能耐,早把他们当作万能的超人,什么事情都可以跟“民代”陈情反映。而“民代”们为了选举时得到选民的力挺,往往会不遗余力地帮忙。
曾有台湾民意代表感叹,临到选举,政见主张敌不过选民服务;理念比不过“够力”。的确,台湾选民的投票,其实也充满算计,张张选票都有投资报酬率的期待。那些平时能够为选民去关说,并且还能关说出成果的民意代表,选举时自然占尽先机。
还有台湾学者戏言,所谓“宗教”行为,和信仰无关,多半是有求于神,或问婚姻、或问事业、或求健康。灵验,则酬神后谢;不灵,则转台换庙,甚至砸神像泄恨。“有求必应”、“应而灵之”才是检验信仰的唯一标准。换言之,就是在请求神明为自己关说。
王金平“没有敌人”之说,乃代表了台湾政治文化最深层,但也最形于外的某些东西。他之所以基层势力稳固,和其与人为善,有求必应的处事风格不无关系。
不过,即便是在关说文化盛行的台湾,也有一条红线——那就是对司法个案不可关说,无论是“关心”还是“了解”都在严禁之列。在马英九眼中,王金平无疑触碰到了这根红线。
“君子”动口,法律就动手
在一般人的传统观念中,官员绝大多数是贪污受贿了,“做了”才会有麻烦,所以“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如果只是说说而已,似乎问题还不太严重。
但台湾对关说的查处,颠覆了我们的固有观念,原来,“君子动口不动手”,也可能违纪违法。
比如王金平关说案,当事各方并不牵涉权钱交易,只是几通电话,便引来大麻烦。王金平受民进党大佬柯建铭所托,打电话给台“法务部部长”曾勇夫和“高检署”检查长陈守煌。此后,王金平又给柯建铭回电,说“勇伯说已经OK”。表示事情已摆平,叫柯不用担心。
有台湾学者指出,关说表面看来只是人情请托,大家互相给面子,实则却是动摇法治社会的基石。在关说中,如果有人受益,那么就必然有其它人的权利遭到侵害。就如同找关系插队一样,有人排到前面去了,后面的人自然要多等一会儿。一个社会中,如果人人都想着托关系,找人请,恰恰每个人的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
还有台湾媒体的评论指出,大家都知道司法关说不对,但在这次争议,却仍有许多人因为事不关己而去同情人缘颇好的王金平。难道,真要等到因为他人关说,自己因而受到不公平对待时才会有锥心之痛?
因此,台湾关说案也是在提醒每一名官员,在现代法治社会,除了不贪以外,还需懂得谨言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