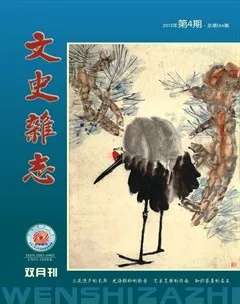论孔子的知行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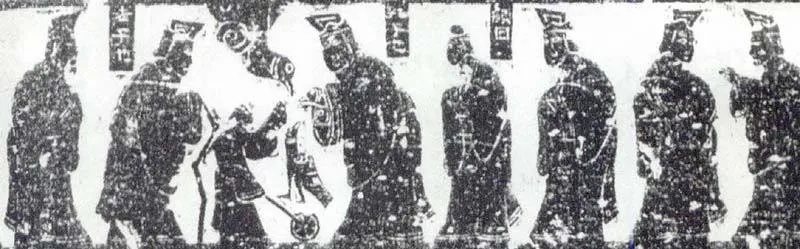

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就是对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的一种表述。宋明理学以个人为主体,围绕着知行的先后、分合、轻重、难易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先生为了鼓舞革命党人勇于投身斗争实践,亦提出和宣扬过“知难行易”的认识论学说。本文仅从认识的来源、认识过程和求知方法三方面,试析先秦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前476年)的著名学者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的知行观。
一、知识的来源——孔子强调“学而知之”
孔子在“人性论”上,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即:人性情本相近,因为习染不同,便相距悬远)然孔子又认为:“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正义》曰:“此章劝人学也。‘生而知之者上也’者,谓圣人也;‘学而知之者次也’者,言由学而知道,次于圣人,谓贤人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者,人本不好学,因其行事有所困,礼不通,发愤而学之者,复次于贤人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者,谓知困而不能学,此为下愚之民也。”困,谓有所不通。孔子所谓圣人,在《论语》中出现了四次,指尧舜禹和周公。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圣人,不能看见;能看见的,就是孔子身边的那些君子,而这些人都是“学而知之”的,实际上孔子主张“学而知之”。孔子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孙星衍《问字堂集》解释:“上知谓生而知之,下愚谓困而不学。”孔子自己以为不是圣人,当然他也不属于“民”。他是贵族子弟即君子,是属于“学而知之”的人。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论语·述而》)“好古,敏以求之者”,就是说,孔子爱好古代文化,勤奋敏捷地去学习求取。
古代文化主要指古代的文化典籍“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此外还要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些都是贵族子弟必须学习的知识和技艺,都是属于孔子所为之“学”。古代“学在官府”,知识被贵族垄断,他们的知识学问都是“官学”。春秋时代,封建领主贵族制度开始崩坏以后,有些没落的贵族和原来称为“士”的最低级的贵族才开始以私人资格传授学问,以维持生活。这才有私人讲学之事,出现了成“一家之言”的私人学派,孔子便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孔子非常好学,“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他向经典学习,向别人学习,向社会实践学习。勤敏地学习,使他成了非常博学的人。当时人说“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墨子·公孟》)。博于《诗》《书》,是从经典中获的;察于礼乐,是学习“六艺”的结果;详于万物,又是从何而来呢?虽然孔子说过,学乎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但下面这件事,便非学习经典就能解释的事情。
《春秋》记载,公元前483年“冬十二月螽”。螽,即今蝗虫为灾。《春秋》经、传记载了十次蝗灾时间多在秋天八月或九月,至迟为冬十月,无在十二月(即今农历十月)者,故季孙问孔子是什么原因?孔子说:“丘闻之,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孔子的意思,谓时已十月,天空应不见大火星(心宿二),昆虫应皆蛰伏,然大火星犹遥见于西方天空,逐渐沉没乃司历者之误,少了一个闰月,所以十二月还有虫类生出。孔子的这个天文知识从何而来?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天文》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晨’,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若历法,则古人不及近代之密。”孔子的天文知识应该来自村社共同体的农夫之辞。古代贵族子弟皆为士,士原为武士之称。古代的士要受一种严格的武士教育,其内容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而射(箭)御(驾车)在他们学习中又是主要的。孔子父亲叔梁纥是一个力大能“举国门之关”的武士,孔子在前亦是一个会射御的武士。《论语·八佾》:“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又《论语·子罕》:孔子对门弟子说:“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礼记·射义》:“孔子射于瞿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可知孔子擅长射御之事。士为统治阶级最末一等。《国语·晋语四》:“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韦昭注“士食田”曰:“受公田也。”公田,是周代村社共同体中的公有田。《孟子·滕文公上》描写的井田制就是孔氏家族曾经赖以生存的乡党村社共同体现象:“卿以下必有圭田(供士祭祀的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据徐中舒先生研究,在中国古代村社共同体中有几个公职人员,殷周叫“丘儒”,春秋战国叫“封人”,秦汉叫“三老。“丘儒”的职责相当于印度村社共同体中的婆罗门僧和司历僧,一方面司理村社里一切宗教仪式;另一方面以占星师的资格通告播种和收获的时候,通告什么时候适宜和什么时候不宜各种农业工作。要能做好这两种工作,“首先他们必须懂得四时代谢、天体运行的规律,他们要在无穷无尽的岁月里,经历一代一代的努力,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在宇宙的范围内积累资料,取得经验,虽然这些经验还是有限的,还要一代一代人随时增补,随时修订,每一个司历僧或占星师都能够贡献他们的智慧。”这就是最早的“儒”。(参见徐中舒:《论甲骨文中所见的儒》,《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下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虽然我们无史料证明“少也贱”的孔子在村社共同体中做过“丘儒”,但是有一点可相信,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一定继承了早期“丘儒”的传统,从村社共同体的社会实践中学习和掌握了丰富的天文地理知识,所以他才能从科学的角度回答季孙的问题。
这里又出现一个问题: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说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呢?我们先看《论语·微子》所记子路掉队遇见荷丈人的事: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
从前批孔断章摘句,抓住“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两句就批,甚至殃及现代广大知识分子受迫害。我们这里不分辨荷丈人那句话所指为谁?孔子听见这句话后赞之为“隐士”,使子路返回去找丈人,想同他谈谈。《论语·子罕》记载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之“鄙夫”,大概即指荷丈人这类人。尽管孔子“多能鄙事”,但他不以圣人自居。他认为在劳动人民面前,他是无知识的。樊迟请求学种庄稼,孔子说:“吾不如老农。”樊迟又请求学种菜,他说:“吾不如老圃(菜农)。”(《论语·子路》)“不如”,就是赶不上,并非一点不知。他出生于村社共同体的环境之中,怎么会“五谷不分”呢?只不过比起终年在地里躬耕的老农和老圃来说,他缺乏实践的经验。孔子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
二、认识的过程:以“行”为先,“知”“行”合一
孔子认为知识从学习得来,但学到的知识要经按时实习运用。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所讲的功课如“六艺”,实践性很强,如礼(包括各种礼节)、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书(书法)、数(算术),非反复实习演习不可。《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
孔子认为古代的典籍也必须能与现在证实才是可靠的。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文,为历史7scAcaB2yi2MrP1IBkgmt0GC/TOhis7BCS7S0ehUwNM=文件;献,即贤,指贤者。孔子认为夏的后代杞国不足以作证夏礼,殷的后代宋国不足以作证殷礼,这是因为他们的历史文件和贤者不够的缘故,若有足够的历史文件和贤者,我们就可以引来作证了。
孔子是注重实践的人,他强调以“行”为先。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意即:古时候言语不轻易出口,就是怕自己的行动赶不上。)他又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意即:君子言语要谨慎迟钝,工作要勤劳敏捷。)子贡问怎样才能做一个君子。孔子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意即:对于你要说的话,先实行了,再说出来,这就够说是一个君子了。)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意即:说得多,做得少,君子以为耻。)
孔子认为,对于从经验得来的知识,不但要加以考核,还要加以引申和类推,由已知引申到未知,“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孔子的学生子贡说,他能“闻一以知二”,另一个学生颜回能“闻一以知十”(《论语·公冶长》)。颜回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闻一以知十”,在孔子看来并不是很高的要求。他说,如果告诉一个学生,一个方的东西的一角是个什么样子,而他不能由此推知其余的三个角是甚么样子,这个学生就不必再教了,即所谓“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隅,方角。杨伯峻讲作方向,此处从冯友兰说。(参见冯友兰:《论孔子》,《三松堂全集》第十二卷第30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孔子认为对于从经验得来的东西,只引申类推,还不能达到知识的最高标准。知识的最高标准,不是仅有许多经验,而要于经验中发现可以把他们联系起来的东西。他说这是“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发现了“一”才可以把许多表面上看是不相联系的事物贯穿起来。这才成为完全的知识。这个“一”就是从经验中发现的事物的规律。(冯友兰:《论孔子》,同上)
知识从实践中学来,又回到实践中去运用和验证,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就是孔子的知行合一观。
三、求知的方法:注重学习,学思结合
孔子求知的方法,首先是学习。孔子所谓“学”包括多闻多见,向经典学习,向他人学习。“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子入太庙,每事问”,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调查研究”的方法。
向别人学习。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卫国的公孙朝问子贡:“仲尼焉学?”即是问:孔仲尼的学问是从哪里学来的?子贡回答:“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意即:我的老师何处不学,又为什么要有一定的老师,专门的传授呢?)孔子学无常师。他曾向春秋末年郯国的国君学习过少皞氏时代的职官名称,(参见《左传·昭公十七年》)向周敬王时的大夫苌弘请教过有关音乐的问题,(参见《礼记·乐记》)跟春秋末年鲁国的乐官师襄学习弹琴,(参见《史记·孔子世家》)少年时代还曾向老聃(即老子李耳)问过周礼。(参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孔子既强调学习的重要,又强调实践。《论语·子罕》记太宰问孔子的学生:“孔老先生是位圣人吗?为什么这样多才多艺呢?”子贡回答:“这本是上天让他成为圣人,又使他多才多艺。”孔子听到后,说:“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太宰知道我呀!我小时候穷苦,所以学会了不少鄙贱的技艺。真正的君子会有这样多的技巧吗?是不会的。)
孔子还认为,因为他不被国家所用,没有当什么官,使他有机会接触下层社会,所以学得一些技艺。(《论语·子罕》:“子云:吾不试,故艺。”)
学思结合。前面讲到孔子强调要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这就要靠理智的运用,即孔子所谓“思”。孔子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因为知识的最后完成,是要靠“思”。但是如果离开了“学”而专“思”,“思”又会落空。归结起来,“思”与“学”互相为用,不可偏废。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
从以上三方面的简述,我们约略可知,孔子的知行观基本是一致的,是唯物的实践论。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