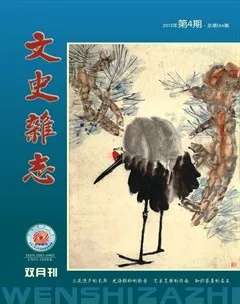李白《静夜思》别解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李白这首《静夜思》早已流传甚广 ,到了今天,就连牙牙学语的幼儿都能说“床前明月光”了。可以说,任何唐诗选本都少不得这首诗,当然也是当今语文课本的必读篇目。对这首诗歌的鉴赏,或谓赏析、欣赏、译释等文章盛行,堪称百花争艳、自由放言;只是对诗中李白的床和当时诗人情态的看法不免趋同,即稍嫌一致了。(幼儿读物的《静夜思》还画上了李白的寢室窗户、卧床等。)我以为这种时下流行、几乎一致的看法并不正确。
本文对此提出“别解”,如对“床”字就予以重新解读,对李白当时的情态予以新说。
一
当今 ,唐诗赏析文字的权威读物当数《唐诗鉴赏辞典》(本文简称《鉴赏》),其中有《静夜思》赏析一篇,兹摘录如下:
这诗的“疑是地上霜”,是叙述,……不难想象,这两句所描写的是客中深夜不能成眠、短梦初回的情景。这时庭院是寂寥的,透过窗户的皎洁月光射到床前,带来了冷森森的秋宵寒意。诗人朦胧地乍一望去,在迷离恍惚的心情中,真好像是地上铺了一层白皑皑的浓霜;可是再定神一看,四周的环境告诉他,这不是霜痕而是月色。月色不免吸引着他抬头一看,一轮娟娟素魄正挂在窗前,秋夜的太空是如此的明净!这时,他完全清醒了。……凝望着月亮,也最容易使人产生遐想,想到故乡的一切,想到家里的亲人。想着,想着,头渐渐地低了下去,完全浸入于沉思之中。
从“疑”到“举头”,从“举头”到“低头”,形象地揭示了诗人内心活动,鲜明地勾勒出一幅生动形象的月夜思乡图。[1]
这里要说的是,李白“床前明月光”中的“床”不是指睡觉的床,而是指坐的“牀”,今天叫坐椅的。(床为牀的俗字,当系后起。今天规定简体,作床。)《静夜思》诗中 ,李白没有在卧床上“深夜不能成眠、短梦初回”,如《鉴赏》所说;再说,“诗人朦胧地乍一望去”之后的描述,难以圆通。于是,本文要说明,这“牀”是坐具而不是卧具;李白此时在坐,没有卧;诗人举头、低头是在静夜中(门窗外)坐着望月思乡的情态。
二
关于《静夜思》的“床”之作卧床解,源于何时,待考。兹姑称之“卧床说”。当然,也有人提出异议,参与争论,那大约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事。(至于50年代以前,也许人们还没有想到用白话来作译释而给后来的读者留下解读的空间。)可惜,在特殊的历史年代里,连这类争论也消失了。当时,与“卧床说”不同,认为这“床”不是指卧床,而是指“井栏”。其原因在于“床”既有井栏这一义项(如《韵会》:“井干也”),而李白其它诗中就有“床”是指井栏的。“井栏说”虽言之不详,但本文认为此说至今还值得重视,便把其论据列出,大约三条。为了说明此说并不妥帖,还逐条辨析:
1.《长干行》句“绕床弄青梅”;2.《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句“梧桐落金井,一叶飞银床”;3.《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句“玉床金井冰峥嵘”。[2]这些确实不指卧床,其2、3两例之银床玉床也确指井栏。
本文认为“床”的井栏之义不宜用于《静夜思》。因为,这在李白诗中是特殊用法,具有特殊语境(况且以上第1例之床既非卧床亦非井栏)。此先说这第2、3例之银床、玉床确指井栏而确非《静夜思》中的“床”,《静夜思》不涉及井栏。
第2例(《赠别》)诗句中,金井、银床并举,梧桐、飞叶各别,意在对台卿优越位置的称美,对自身飘泊身世的感叹。诗中还有“因为洞庭叶,飘落之潇湘”等语,都有希望友人援引之意。庾肩吾早有“银床落井桐”的诗句,若李白用其典,亦只为婉转陈述己意;观其情调,可见此诗写于被罪谪之后。[3]而第3例(《答王十二》)诗句,从表达的失意之情来看,或当作于李白离开京城几年之后的浮游生活中。[4]关于“玉床金井冰峥嵘”句,有注曰“玉床金井言其美丽之饰,如金如玉”。[5]诗句以此美好意象来比况曾经有过的好日子,正映衬出诗人当下的怅惘。这与《静夜思》之“气骨甚高、神韵甚穆”(《唐宋诗醇》)相较,是大不相同的。这篇《答王十二》诗,更能看出诗人在流寓之时的自我宽解。这两首诗都多少带有为应酬而作的色彩,此所谓特殊语境吧!明乎此,可知这井栏义的银床、玉床显然不能用来指李白《静夜思》中的“床”了。
为稻粱谋而作诗而有求于人者,李杜诗章中不免有之,这是古代伟大诗人的悲哀,也是古今读书人的悲哀!说这些,也意在说明所谓特殊用法、特殊语境。
以上两例之“床”,虽指井栏却不是《静夜思》中的“床”; 而第1例“绕床弄青梅”之“床”就既不是井栏、也不是卧床,而是坐具。这恰好可作为本文坐椅之说的论据之一。
“绕床”之床非指井栏,这可以从井栏在人家住户庭院中所处的位置来说明。例如:《乐府诗集·舞曲歌辞三·淮南王篇》“后园凿井银作牀,金瓶素绠汲寒浆”,可见是后园凿井;李贺诗句“井上辘轳牀上转,水声繁,弦声浅”,即出自其《后园凿井歌》。(这两例中的“牀”也正是井栏。)如要讲个什么“井文化”,可知从古到今没有在门户近前的前园内挖凿水井的事例。这样,可知《长干行》诗中“郎骑竹马来”决不会到后园去“绕牀”弄青梅,而应当是围绕大人在门前的坐处来嬉闹玩耍。因此,这床显然不指井栏。至于井栏又何以名“牀”,窃以为当得义于“牆”,这已是题外话了。《长干行》里“绕床”不是“绕井栏”,当然更不会指寢室里绕床。“绕床”当指围绕“坐椅”。下面详细申说《静夜思》“床前”之床所指就是坐椅。
三
“床”除了卧床、井栏(引伸的)之义,还有“坐具”之义(有多种坐具也名床)。《说文》云:“牀,安身之几坐也”。再看段注:“铉本作‘安身之坐者’……《孝经》‘仲尼凥’而释之曰‘谓闲居如此’……仲尼凥者,从尸得几而止,谓坐于牀也”。这里是说,凥读为居,再看《孝经》首章第一句即“仲尼居,曾子侍”。显然,这“安身之几坐”的几正是坐具,用今天的话说当是坐椅或坐凳,“仲尼凥”是说孔子坐在这椅凳上。这几,是用来与床互训的。总之,此“几坐”即指床,段注“谓坐于牀也”。
《广韵》谓“床”:“牀俗字”(前面已提及),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的讨论。
再说孔子闲居,曾子侍,孔子言先王至德要道,当然不会躺在床上像今人那样随便扯谈什么理论。故曰孔子“坐于牀也”。至于卧具之床,固然早见于文献,如《诗·小雅·斯干》之“载寢之牀”,那是供人寢卧、形制较大的。而据《释名·释牀帐》所言“人所坐卧曰牀,牀,装也,所以自装载也。”(顺带说,古今有苗床糟床河床机床等名当是得义于装的。)更多的“牀”指坐具床,如“榻、枰”,以其形制小。“小者曰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6]今天或叫单人椅。且看《说文》谓床“安身之几坐也”后面的段注:“汉管宁常坐一木榻,积五十余年未尝箕股,其榻上当膝处皆穿”,此以榻注床,此“榻”是坐具,属床。再看《释名》谓“牀”之“小者曰独坐”,王先谦引《水经注·湘水篇》云:“‘贾谊宅有一脚石床,才容一人坐。’云谊宿所坐床,是即枰也。”[7]可知这在汉代时,一个坐的石礅子也可叫床(是即枰也)。往后的“床”其名实如何,下文交待之。
不同于贾谊、管宁所坐,形制非同一般的大坐具名床者,如曹丞相“办公厅”里的就是。《世说新语·容止》:“魏武将见匈奴使……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显然,这床就是比今天的豪华椅还大的坐具,当时毕竟叫床。同样,形制很小的也叫床。《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牀……京都贵戚竞为之。”且说这胡床,据陶穀《清异录》载:“胡牀施转关以交足,穿便条以容坐,转缩须臾,重不数斤。”是很轻便的坐具,今天的折折椅者,古已有之,其来自于胡,亦称为“床”。
单说床之为坐具者,后来名称有了衍变:即床之常用为坐具者名为“椅”了(也许相当于现在从椅中把臃肿的胖椅名为“沙发”吧)。“椅”当为借字,其本字为“倚”,故椅或当取声取义于此。“椅”本树木名(川西称“水冬瓜”),《诗·鄘风》云“树之榛粟,椅桐梓漆”。而坐具床称为椅的时间却晚于“牀前明月光”多少年了。所以,窃以为,赵宋王朝乃至五代以前,坐具无“椅”之名而泛称为牀,此后才有“椅”和原有的榻并称。
宋人欧阳修《新五代史·景延广传》载:“天福八年秋……延广所进器服、鞍马、茶床、椅榻皆裹金银”。这里,此茶床为茶具,如笔床、印床之为文具名,坐具之“床”已有新名 “椅”,“椅榻”并列。且说宋代已有“校椅”之名,宋人张瑞义《贵耳集》有云:“今之校椅者古之胡床也”。可见,皇上坐龙床(皇权制结束,此名犹存,堪称万岁校椅),臣僚坐一般校椅;梁山好汉们皆坐,晁、宋所坐即头把校椅。至于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还说到靠背椅:“如胡床之有靠背者,名东坡椅”。不管什么椅,其实从前都叫床,唐朝无椅之名当然称床,“床前明月光”, “床前”二字,后人纵然知道是“坐椅之前”,也应无法臆改了。
四
下面以诗、文材料作佐证以更加具体说明唐朝的“床”,且阐明诗人静夜思乡所坐之方位。
至今,中国院落里,屋檐下的阶沿之上,临窗之处安放坐椅,这景况还常见。李白夜思所坐之方位当如是。兹引杜甫诗《少年行》,诗云:“马上谁家白面郎?临阶下马坐人床。不通姓氏粗豪甚,指点银瓶索酒尝。”诗后原注:“床,胡床也。”[8]综观诗意,可见那“少年”是个有来头的官二代,临阶下马一屁股坐在人家的椅子上。杜诗在这里亦称椅为床,这“床”正是安放在阶沿上的,此在盛唐之时。再引中唐诗人崔护《题都城南庄》故事予以说明,人们熟习“人面桃花相映红”诗句,时人孟棨《本事诗·情感》叙述此事,说崔护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院,口渴了去敲人家的院门要水喝,院门内有姑娘应声,“女子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崔辞去,送至门……”按常理,这崔生当在院门外一饮而尽,道谢便走,谁知又进入院内,就有了“去年今日此门中”的场景:那姑娘端把椅子请崔坐,自己乃傍桃斜逸的树枝伫立,崔乃惊喜于“人面桃花相映红”了,可见二人相距不远。(按:这在唐时,算是大胆爱情的故事,但决不类今日的“时代青年”。)显然,这“设床命坐”,或许就在阶沿上,也可能将坐椅置于桃树院坝里,而不会在屋内。总之,此“床”更决非什么寢室里的睡卧之床也。例不多举,应能说明:唐代诗文皆称椅(凳)为床。
至于唐代椅(凳)的形制,即其模样如何,可参见传世文献画作——(宋·佚名所作)《十八学士图》:场景是庭院花园、苍松翠竹,唐代学士们一起研讨经义,围坐一张大桌者有杜如晦、房玄龄、陆德明等学者型高官,所坐的“床”有长方形双人坐榻、圆鼓形坐凳、正方形带扶手靠背椅等。这里没有看到那高出人头的雕花靠背椅(如当今企事业老总所坐),此椅可另见于《地藏十王图》[9]。无须赘言,这些椅凳都叫“床”。李白坐前是明月光,而诗人究竟坐的何种椅,本文从略。
五
最后,有必要谈谈与本文论题有关的《静夜思》的版本问题。我们知道,历来诸多选本中,清乾隆时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的影响很大,最为普及,其《静夜思》也是当今所遵循而通行的版本。而此版实为清初王士祯《唐人万首绝句选》所定,“疑为士祯所臆改者”[10]。其原版如宋人所编《万首唐人绝句》、清人所编《全唐诗》等,兹录其未经“臆改”的原版《静夜思》如下:
牀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
若这样,如说诗人在卧室里而言“举头望山月”,问题就更为明显;若说诗人(在室外坐椅上)静坐夜思,则顺理成章。然而,深通诗美的王士祯臆改“看”、“山”二字各作“明”,“明月”两见,今天看来亦自有妙处。对此,20世纪80年代就有“诗文欣赏”的文章说到版本问题,说到“改动”版:“是老百姓自然而然地会用自己的生活体验和语言习惯改造它”,此说值得参见;文章中另有欣赏说:“比如,我们可以设想,诗人是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梦醒过来,望着一轮明月,产生了乡思;说不定,他刚才做的正是个思乡的梦,醒来后‘思故乡’便是回味梦中之事”[11]。这和上文所引《鉴赏》之“短梦初回”说大体一致,是倾向“卧床说”的,我以为同样值得商榷。
再来看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上文已说过,他当时坐的“椅榻”,当然叫作床;而这诗句中的“床”,其音与义,只应如此。按上文所引《鉴赏》,这床是李白“朦胧”睡觉的床,然而,如果李白“迷离恍惚”地睡在床上“凝望着月亮”,而说他“举头”、“低头”,显然有问题。不过,或者(比如有其它“鉴赏”)说,李白在床上睡着,此后又翻身起来坐在床沿上(或又起身踱步)看那照射进来的床前明月光,当然可以举头、低头。可惜,这与“静夜思”那空旷寥廓的意境不合。按情理,人忧思则夜不能寐,与其睡着,不如坐着。李白诗《夜坐吟》有云:“冬夜夜寒觉夜长,沉吟久坐坐北堂”。 李白《静夜思》,无论原版还是清代才有的改动版,诗人独坐夜思于室外而不是在卧室里,方才符合情理。
结语
本文认为,关于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之床字的解析与李白坐与卧问题的探讨直接关系到《静夜思》意境的赏析。诵读《静夜思》,不禁令人想起阮籍《咏怀诗》句:“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帏鉴明月,清风吹我襟……”两者相较,一是忧生之嗟,一为怀乡之叹;山黯风清,月明夜静。伟大诗人的情韵,雋朗深沉的诗风,今日鲜见了。
本文以为《静夜思》那景况,且用今天话说:
静静的夜里,李白坐在椅上(无论坐榻、大圈椅或什么靠背椅),在檐下的廊庑上孑然一身。一望坐前,明月如霜;仰望夜空,幽寂寥落,低头黙默思念,家乡迢迢路远。
总之,拙文非难“井栏说”,不赞成通行的“卧床说”,管见一得,暂且忝称“坐椅说”。当然有不足之处,尚望请益于方家。
注释:
[1]《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9页、250页。
[2][3][5]参见瞿蜕园、朱金城:《 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版,第771页、1143页、1144页。
[4]参见王伯祥编著《增订李太白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页。
[6][7]王先谦撰集《释名疏证补》,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95页。
[8]仇兆鰲:《杜诗详注 》,中华书局1979年版。
[9]参见《中国传世人物名画全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版(据编者说,原画作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10]《全唐诗》第三函第四册《李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高步瀛选注《唐宋诗举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11]《漫说〈静夜思〉》,《文史知识》,中华书局1984年第4期,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