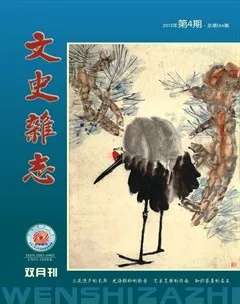陈独秀先生性格特征初考
陈独秀(1879.10——1942.5),原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属安庆)人,从小勤学好读,秉赋聪慧,习诵四书五经,有很好的国学功底。1896年,他17岁时参加科举考试中第,获秀才第一名。1901年至1914年间他先后三次东渡日本留学。他才思敏捷,学识渊博,懂日、英、法三国文字,对新学造诣尤深。他参加辛亥革命后,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倡导科学、民主,以唤醒民众而闻名于世。他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著名创建领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一大”至“五大”连任总书记,是一位富有个性魅力的政治家。本文试从陈独秀先生一个侧面,就他的个性特征作一考述。
举科学民主旗帜 刚强坚毅
《新青年》创刊号上,陈独秀开宗明义向世人宣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差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新青年》的科学、民主导向,开启了“新文化运动”序幕。接着,陈独秀频繁与远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的盟友胡适取得联系,商讨推进“新文化运动”之策,并向胡适约稿。1916年2月,胡适将新译俄国小说《决斗》寄来以表支持。陈独秀认为此小说是改良文学之先导,立刻在《新青年》刊发,反响颇佳。1917年1月,胡适第二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亦很快在《新青年》刊出。不久,在该刊当年第2期,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文章,果断言道:“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以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故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中国文学革命之气运,醖酿已非一日,其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以为吾友之声援。”此时远在美国的胡适,对国内已蓬勃兴起的文学革命,无法目睹感受。当《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他反而有点胆怯了,担心引起“保守派反对”,不愿扩大事态,来信向陈独秀建言缓慢研讨,称决不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在此关头,陈独秀态度刚强坚决,义无反顾向前精进。他在答复胡适信中明确写道:“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自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且是非甚明,必不由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已主张革命之旗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由此,新文化运动冲破重重束缚,开拓前行,修成正果。后来胡适感叹道:“陈独秀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们一年多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执行者,不久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当年如果不是陈独秀如此不容讨论之余地,文学改革、白话文,就不会有如此的效果。”[1]继后,陈独秀在参与发动领导“五四”运动、创建中国共产党活动中,“总是自觉挺身向前,像是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佛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2]正因为他具有这种刚强坚毅的性格力量,才奠定了他在那段历史时期的政坛上不可撼动的主导地位,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身陷囹圄 刚强不屈
从1919年“五四”运动至1932年,陈独秀曾五次被捕坐牢。他一以贯之坚持民主政治,反对北洋军阀,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独裁专制的政治主张,从未向敌人低头屈服过。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是1932年10月,被关在南京监狱里。蒋介石企图再次用暴力令其屈服。陈独秀刚强不屈,继续坚持自己政治主张。蒋介石遂改行软诱手段,派何应钦前去监狱“探访”,想以此软化拉拢。陈独秀义正词严对何说:“我与蒋介石不共戴天,他杀了我们许多同志,还有我的两个儿子。我和他们是有仇的。”遭陈拒绝后,何应钦因很欣赏陈独秀的书法,离开时要请陈写一条幅。陈没加思索,立刻挥笔写下“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十三个昂然不屈的大字。
1933年4月14日、4月15日,国民政府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独秀。“法官问:你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陈答:这是事实,不否认。理由很简单,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无发言权,共产党员遭屠杀,即一般国民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符合民主政治原则。”[3]最终陈独秀被国民政府南京高等法院判刑七年。在服刑中,陈独秀继续坚持反对蒋介石政府独裁专制统治,并坚持写作和研读。1935年7月,国画大师刘海粟前往狱中探望陈独秀,陈给刘写了副对联相赠。上联是“行无愧怍心常坦”,下联为“身处艰难气若虹”。其坦荡心境和政治家气节,让人钦佩。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时,陈独秀被张伯龄、胡适等人于同年8月保释出狱。
陈独秀虽被保释出狱,国民党政府仍安排军警暗中监视,并千方百计拉拢他。陈出狱时军统局处长丁默邨特意去迎接,安排他住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被陈拒绝。蒋介石又派陈立夫、陈果夫前往看访,要陈独秀出任劳动部长,与之合作反对共产党。陈明确表示拒绝诱惑,言决不反共。老朋友胡适、周佛海邀他参加国民政府国防会议;蒋介石亲信朱家骅奉命许诺提供10万元经费和五个“国民参政会议席”,要他组织一个新共产党与共产党唱对台戏,均被他一一拒绝。1937年9月,陈独秀从南京到达武汉,华中大学生联合会负责人许俊千等得知后,以学生会名义邀请陈独秀演讲抗日。他开门见山说:“全国要求的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了。为什么要抗战,一般的说法,是因为日本欺压我们太厉害。这话固然不错,可是,未免过于肤浅了,一般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应该明了更深一点的意义。这次抗战,乃六七十年来改革与革命大运动之继续,其历史意义乃是脱离帝国主义压迫与束缚,以完成中国独立与统一,由半殖民地的工业进到民族工业,使中国政治、经济获得不断的自由发展机会。”并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灭亡中国,乃是以分化手段,在南北制造各种名义的政治组织,利用亲日派做傀儡,间接来统治中国,这不是亡国是什么?”演讲结尾,陈疾声号召:“全国人民都应该拿出力量来援助抗日战争,除非甘心做汉奸!”演讲完毕,许俊千等送陈回住处时,许向陈写下“敬求大笔,赐乎俊千”的要求。陈独秀将原在狱中写给刘海粟的“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的对联,重又写给许俊千,体现了陈的人格坚守。[4]
贫病交迫 刚直不阿
陈独秀出狱后,在南京、武汉等地短住,先后寄居傅斯年、陈钟凡家(陈是北大学生),靠朋友资助度日。他刚直不阿,既拒绝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又拒绝做检讨前往延安。托派邀请他到上海也遭拒绝。胡适建议要他去美国写自传,亦不采纳。他从此踏上茫然惆怅,穷愁潦倒道路。“1938年7月,陈独秀偕夫人潘兰珍从武汉辗转长沙来到重庆,遇见同乡同学邓季宣,通过邓又认识四川江津县名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邓蟾秋仰慕陈独秀之名,邀请他到江津县。”经过一番周折,陈独秀“最后定居该县清朝拔贡杨鲁承家石墙大院。陈住在石墙大院右侧一小院,从事研究中国汉学、文字学、考古学,整理他在狱中撰写的《小学识字教本》,以度晚年。”[5]
陈独秀住石墙院期间,虽远离城市,交通不便,但前来拜访的人很多,小到县长、专员,大到国共两党要员。蒋介石派戴笠、胡宗南前往慰问,并请陈独秀好友高语罕陪同引见。戴、胡两人受命名为慰问,实则挑拨陈与中共关系,并特地带上新出版刊有康生文章的《新华日报》。康生在文章中诬蔑陈独秀是日本间谍,陈却不屑一顾,冷笑置之。“陈独秀生病卧床时,中共驻重庆国民党政府代表周恩来,在辛亥革命元老朱蕴山陪同下访问陈独秀,两人倾情交谈中,周恩来继续劝说陈独秀,希望他放弃个人成见与固执,希望他写个检查回到延安去。陈独秀还是老脾气,他直言不讳将在武汉逗留期间,董必武代表中共会见他时,他向董必武表白的话‘老干们不欢迎我的,我犯不着找他们,现在乱哄哄时代,谁有过谁没有过,还讲不清楚,我有什么过错?写什么悔过检查?’‘我这个人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去弄得大家无果而散!’”[6]又重新提起,拒绝了周恩来之劝。
1941年春,国民党要员朱家骅要张国焘转交给陈独秀一张五千元支票,这对贫病交迫中的陈独秀来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款子。但陈独秀却毫不迟疑当即将支票退给张国焘,说:“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7]这年夏,“陈独秀将原在狱中撰写的《小学识字教本》整理完稿,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出版,但在送审时,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小学’二字不妥,要请陈改书名。陈独秀说‘一字不能动’,把预支的两万元稿酬退了回去。此时,陈独秀已贫病交加,生活拮据,多么需要一笔钱治病度日,可是他就是拒收这笔稿费。”[8]这就是陈独秀的性格:刚直不阿,让人崇敬。这时,陈独秀夫人潘兰珍为贫病生活所迫,避着丈夫典当了首饰,连陈的老朋友、后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的柏文蔚赠送的一件皮袍子也当了。为补贴生活,潘兰珍还在院墙后门外空地上种上土豆等蔬菜。陈独秀夫妇清贫却不失气节的高尚风骨,赢得世人尊敬。
待人处事 坦诚爽直
陈独秀是一位个性鲜明,有棱有角,喜怒形于色的人。他待人处事,坦诚爽直,心口一致,从无遮掩。鲁迅和陈独秀两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同道,后虽各自所走人生道路不同,却彼此敬重,对对方都有较高评价。鲁迅对陈独秀的为人,作过如此比喻,说:“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9]鲁迅先生这个比喻一语道破陈独秀处事光明磊落,坦诚直爽。陈独秀不恋权,没有野心,从不耍诡计、玩权术。他尤为厌恶权术,说:“我不怕孤立,企图从阴谋诡计小把戏的基础上团结同志,做自己个人的群众,这是张国焘做过的大买卖,因而是我深恶痛绝的。”[10]
1937年12月2日,陈独秀在给陈其昌等人信中谈及中共曾向他提出去延安的三个条件写道:“我是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说不错又不对的话”;“我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以心坦然为是。”[11]张国焘在回忆他心目中的陈独秀时写道:“仲甫聪慧、果敢、爽直,富有人情味。有时喜怒于色,说一些伤人的话,但不记仇于人,争论之后,倘能认真思索问题,觉得自己有错,还敢承认,是有气魄的。建党初期,还有民主作风,让人有一种信任感。”[12]陈独秀对批评意见,有察纳雅量;对反对他的人,坦然大度不记恨。一次友人告诉他说,鲁迅批评“还有人在嚷着要求言论自由”是指陈,说陈是《红楼梦》中焦大,骂了主子王熙凤,落得吃马粪。陈独秀则说:“此言真伪无妨,别人若骂的对是应该的,若骂的不对,只好任他去骂,我一生挨人骂者多矣,我从没计较过,毁誉一个人,不是当代就能作出定论的,要看天下后世评论如何,还要看大众的看法如何。”[13]
陈独秀当然不是完人。他在刚强坚毅、不卑不亢、爽直坦诚性格的另一面,则脾气暴躁,倔强执拗,素行不检。“一旦走入歧途,他那刚强性格便一变而为刚愎自用,很难回头。他固执己见,当辩论的时候,他会声色俱厉地坚持他个人的主张,倘然有人坚决反对他,他竟会站起来拂袖离去。他疾恶如仇,却又不尽然如是,有时优柔寡断,以致姑息奸恶。”[14]正如陈独秀自己在《自传》中所说:“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疾恶如仇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性格的遗传,也有影响吧。”陈独秀对自身性格弱点及其酿成的后果是有清楚认识的。陈独秀先生当年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几次坐牢,到处奔波,生活不安定,到老心情不好,贫病交加,以致患上胃病、高血压、心脏病。1942年5月27日,他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在他客居的四川江津与世长辞,享年63岁。
注释:
[1]《胡适盖棺论定陈独秀》,《党史文苑》2010年第10期。
[2]《章士钊评说陈独秀》,《甲寅周刊》第1卷30号,1926年1月30日。
[3]《陈独秀开审记》,《国闻周刊》,1933年4月16日。
[4][5][12]《炎黄春秋》,2000年第5期、第7期,2004年第9期。
[6][7]《党史文献史料》,1996年第3期,1998年第4期。
[8]《革命史料》,1989年第2期。
[9]《鲁迅全集》第6卷第7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0][11][13][14]《陈独秀》(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