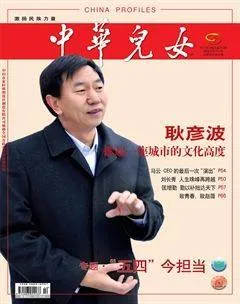莫让身份标签误了奋斗路
一部名为《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电影,勾起了人们对青春的回忆。这部略带伤感的影片,描述了一代青年人共同经历过的迷惘、追求与梦想。梦想,素来与青春如影随形,它使整个青春岁月充满奇迹、色彩斑斓,拥有未知的精彩。以一种昂扬的心态迎接生活与挑战,这正是青年人的可贵和美丽所在。
今年五四青年节,有媒体发文称,当今青年已经与过去的青年有很大不同,他们因背负太重的压力而过于“早熟”,以致丧失激情,忘记梦想、疯狂、激情,“北漂”“房奴”“月光族”等名目繁多的身份标签,使青年人只剩下焦虑、浮躁和早衰。新一代青年人在重压下求安稳,浪漫情怀过早缺失,年纪轻轻即世故老成。
现实中告别梦想
“工作之后再谈梦想,只会让人觉得是冒傻气,甚至是发疯。”
“梦想谁不曾有过,只是我觉得现在提梦想一点用都没有。”苏威今年33岁,国内名牌大学文科博士毕业,目前在北京某重点高校教书,“工作之后再谈梦想,只会让人觉得是冒傻气,甚至是发疯。”
留在象牙塔,看看书、上上课、搞搞研究,这是苏威上大学时的梦想,可如今他发现,“梦想与现实之间有着太大的差距”。
苏威每周承担14课时的教学任务,与同系教授一起做两项科研课题,他计划三年内发表6篇论文,早日拿到副高职称。为此,他把大部分的时间分给了科研,其中不少又“耗在写标书、拉关系、四处找发票报销上”。
苏威觉得,自己每天都过得“匆忙且乏味”,与以前幻想中的休闲生活完全不同,上课、查资料、带学生做调研,撰写由名教授或系主任“挂帅”的课题报告,再跑办公室和财务“贴票、签字、报销”,日复一日。
双休日除了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外,就全忙于文献翻译,为争取早日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搜集素材。
尽管高校教师这份工作稳定且“听起来还不错”,但在苏威心里,与那些在大机关当公务员或者做老板的朋友相聚,自己“从来没有什么自信”。在外人看来,大学教师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但苏威和同事们私下会自嘲为“知识工人”,或“工蜂”族。
“工蜂”族——意思是外表光鲜、业务主力、干的活多但收获有限,这群人多数忙碌于金字塔底端,仅少数人能拼到上层,才可以“有资本和人脉可以做真正感兴趣的事”。
同事“非升即走”的趋势更加剧了苏威的紧迫感。“过去,很多人把大学老师的工作视作终身的‘铁饭碗’,但如今的潜规则却是:5年内不能从讲师升到副教授,你在这个学校的教书生涯就基本结束了。”
其实,无论从哪方面条件来看,“工蜂”族都不算弱势群体,更不算什么“屌丝”:高学历,工作稳定,拥有本地城镇户口,有住房公积金和完善的保险,这些条件的具备应属“凭借学历资本而上升”的中产阶级。但“工蜂”族的自我认知令许多从业者感到压抑甚至边缘化。
一份针对大学教师的调查报告显示,这个人群的自我认知在“下行”。5138位受访高校青年教师中,84.5%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中层以下,其中,36%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13.7%认为自己处于“底层”。
众人艳羡大学教师尚且如此,普通白领更是给自己起了一堆颇显悲凉的称号。“我是一名‘蚁族’、‘啃老族’、‘矮穷矬’、‘北漂’”——这是一位IT白领在qq上的个人签名。
诸如此类的标签不断加诸在青年人身上,或主动或被动,但引起的现实效应却是:对于很多在职场摸爬滚打数年的年轻人来说,“梦想”早就成为一种奢侈品。工作仅仅是为稻粱谋,加班不过是出于无奈……
标签文化风头正劲
“新标签五花八门,公众常常对号入座,用标签解读复杂的社会现象。”
体制内、体制外、穷二代、富二代、租床族、职场便利贴……眼下,不论互联网上还是现实生活中,各种“新词”层出不穷。其中一些词汇,对某类人或某个群体进行了颇为契合的归纳,于是迅速在网络和传统媒体中传播开来,甚至成为一种风潮。接下来,人们便会自行对号入座或是将某个职业、某个群体的人对之对应,以此对周围的人和事分类、判断,进而产生社会效应。
社会学上将这类行为统一成为“贴标签”。普通人面对纷繁复杂的现象,习惯于将其化繁为简,以便清晰便捷地把握事物特征。 贴标签就是一种简单归类,人们可以借助标签对外界的人、事、物形成表面和粗浅的印象,降低行为成本。
比如年轻人开宝马、戴名表,立刻冠之“富二代”;没背景、找不到好工作的,就是“穷二代”;媒体在报道时也会大量引用这些“标签”,譬如《蚁族也想成为体制内》《穷二代,想当房奴不容易》等类似报道屡见不鲜,强化了标签的影响力和辐射面。
一些人对此持“无所谓”的态度。“就是一些新潮的词而已,大家聊天时爱说,你要是不知道,显得特out(落伍)。”媒体工作者小陈看来,有些标签简洁明了,交流中用一个词就能说明一种复杂的状况和心境,“比如‘北漂’,就很符合我们这些常年混在北京,没户口、没根基的人的状况,容易让人产生共鸣。”“比如有同事买新房了或者生孩子了,我们会说他成了‘房奴’‘孩奴’,我们没有恶意,人家也并不觉得是负担,心里美得不得了呢。”
不过,随着这些标签越来越多地融入现实生活,不少人感到了被贴标签的不适。
“自从我考上公务员后,同学们就给我贴上‘体制内’的标签,说我是吃皇粮的。”统计局的小章对此很无奈,“同学聚会,大家都说‘体制内’如何好,什么都不用愁。如果我说自己经济上有压力,立刻会被人说虚伪。如果我说工作辛苦,立刻有人说我‘别装了’。其实在同学里,我这样一个小公务员真的是收入比较低的。”
因出书而走红的城管宋志刚也曾提到,自己在执法过程中打不还口、骂不还手,即便这样,一旦有争执,人们还是会一味指责城管欺负人,而认为小贩无辜。因为“农民工”作为弱势一方和“城管”作为强势一方代表的对立形象标签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中。
为什么人们热衷于贴标签呢?
“标签化式的思维方式,有其产生的客观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教授表示。多数标签针对特定人群,是以人群归类来判定其行为,某个人群被赋予正面的标签,那么这个人群不分个体都具有正面性,反之,则不分具体情况都被打上负面烙印。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主要是由于我国群体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
“‘贴标签’也称为‘污名化’。”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强说,即一个群体将某些偏向负面的特征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将这些特征刻板印象化,掩盖其他特征,成为与之相对应的指标物。
对周围的事物贴标签,每个人几乎都在有意无意地这样做。只是,当“贴标签”随着传播方式的变化,几何级地放大其影响力和辐射面,继而成为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时,其弊端也正在引起关注。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朱力曾指出,近年来无论是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中,还是在网络的自发言论中,都存在明显的泛标签化现象。它把同一个特征归属于群体中的每一个人,而不管个体成员中的实际差异,往往会扭曲社会认知。例如,将一个偶发的、当事人无意的行为,贴上富人身份与穷人身份的标签,就使一个平常的事件变成了一个显示社会分裂的标志性公共事件。贴标签不仅不会使问题得到更好解决,反而会使人们的心理不满迅速发酵。过多的标签化式的报道,也在无形中强化了阶层意识、磨损社会和谐。这样做会加剧社会对立,也不够客观。
目前,贴标签所显现出来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是破坏性。能够流行起来的标签通常是负面的,它会导致人、事、物的正面形象遭到非理性的破坏。某类事件,可能前因后果极为复杂,但被贴上特定标签后,多数人就只会注意其标签所指的内容。其次,是快速污染性。标签所包含的负面因素,在现代发达的信息传播网络作用下,会迅速地“传染”到类似的事物或者人身上,甚至波及整个行业、产业乃至地区,忽略个体间大量存在的差异。比如前些年,“河南人”这个标签就很典型,伤了很多无辜河南人的心。第三是不易消除性。标签流行起来,会发展成一种偏见,其固化的价值观念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使被贴标签的对象很难摆脱其影响。譬如,一项调查显示,被外界认为是“屌丝”的群体,一半以上在婚恋相亲方面遇到障碍,一句“屌丝”就把再见面的希望给毁了。
这是当前中国社会生态的重要一角,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对社会背景相似,或者经济地位相近的人群进行分类,这样的动机或出于批判,或为了顾影自怜。即便这样的识别有些简单粗暴,却并不能影响其流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群的分化,标签已经超过了“标签”本身的价值,它不再只是用作对人群的属性识别,更重要的就在于,它成为人们判断社会观感,确定自身命运的重要根据。
标签阴影不利中国梦
身份标签容易传播,引起数量众多的弱势群体共鸣,反映了他们的普遍焦虑。
其实,贴标签这种行为在国外也有。只是,国外贴标签主要由强势群体针对弱势群体进行,弱势群体往往并不认可。
在我国则不同,一方面存在大量针对强势群体的标签,如官二代、富二代、公知、体制内等,另一方面弱势群体往往主动把标签贴到自己身上,如自称房奴、穷二代等。恰恰是这类标签,流传得最广也最容易被用来分析判断相应的社会现象。
无数贫穷的年轻人基于类似的背景而自嘲,深圳海事局的林嘉祥因为一句“你们算个屁!”,从而造就了“屁民”这个标签的广泛流行,无数网民自嘲为“屁民”,以此顾影自怜或自我排解。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许光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社会建设则相对落后,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尤其在社会公平方面。“按照亚当斯的公平理论,人不仅会把自己的努力程度和收入进行横向比较,也会进行大量的纵向比较。我国今天的发展格局是,不仅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很大,群体差距也非常大。”
这使得针对不同群体差异的标签很容易流行起来,弱势群体用来表达对强势群体的不满,希望引起普遍的社会关注。信息不透明,监督不到位,沟通不顺畅,又使得更多人习惯用标签思维来对事件进行判断。例如一辆豪华车发生交通事故,多数人往往立刻把关注的重点放在“豪华车”、“有钱人”等标签上,很少会去关注事故的具体原因。
“近几年贴标签的现象特别突出,因为传播方式变了。”许光建表示,弱势群体相对而言缺少话语权,在传统的传播语境中,其表达意见的渠道比较少。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这一切,使各种身份标签更容易传播,引起数量众多的弱势群体共鸣,反映他们的普遍焦虑。
有研究显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按十等分法测算,所有群体的收入状况都有明显改善,但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分配差距则不断扩大,在1988年为7倍,到2010年上升至20倍以上。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拉大,生活水平差异明显,使人们产生不平衡的心理。
分配制度不健全、向上流动的通道不够顺畅,加剧了这种不平衡。与此同时,一些个案,例如官员的子女非正常升迁等,经曝光后进一步放大了不公平的感受。
“贴标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应当避免‘标签化思维’,倡导理性、客观,不要以简单的价值判断代替基本的事实判断。”许光建说。标签思维通常是“一刀切”、“先入为主”,面对问题预设立场,以标签去思考,阻碍理性探讨。例如,飙车撞人且蛮不讲理的一定是“富二代”,在公务员考试中玩猫腻走后门的一定是“官二代”,而被“富二代”和“官二代”欺负的自然是“穷二代”。这种标签化的逻辑将当事人的身份冲突升级为阶层矛盾,很明显地预设了一个可能有失偏颇的道德和价值判断,但公众似乎对这种偏见并无太多异议。
应该看到,“标签现象”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尤其是青年人)甘于在自我贴标签中麻痹退缩,而失去了奋斗、拼搏的斗志;可怕的是,底层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少,看不到提升社会地位的希望。这不仅不利于每个个体的梦想实现,甚至会影响到“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任何一个“有梦想”的国家都会有一套精英更替与财富流转的机制,让草根青年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上流动,让每个有梦想的人尽可能追逐梦想。所谓中国梦,就是让每个人都怀有成功之心、奋斗之志,同时让他们在实现梦想时享有制度的保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五四青年节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所述,关怀青年,“为青年驰骋思想打开更浩瀚的天空,为青年实践创新搭建更广阔的舞台,为青年塑造人生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责任编辑 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