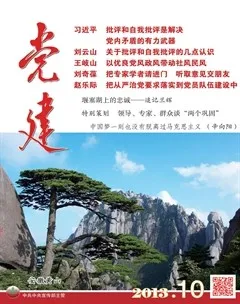赵树理:一生写农民

9 月,阵阵秋风拂帘而入,丝丝凉意不免让人伤感——“人民艺术家”赵树理的生与死都铭刻在这个月份里。
头戴厚毡帽,口噙小烟袋,身穿黑色对襟袄,吃着南瓜山药蛋,晒得黝黑的脸上淌着汗道子……即使你已经知道赵树理住在这户农民家里,也不会想到这个“乡巴佬”就是那个大作家。
对农民有着深厚感情,对农村生活有着独特感悟的赵树理,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用农民语言写农民故事的农民作家。他的价值、可贵与不朽,都与深至心髓的农民情结息息相关。
1
山一程,沟一程。我们行进在叠嶂起伏的太行山腹地,前往《小二黑结婚》故事的发生地山西省左权县芹泉乡横岭村。
灰带子般歪歪斜斜的小路淹入万山丛中,这可是真正的山大沟深啊!当年没有车坐,没有马骑的赵树理三上横岭,是怎样一步一步丈量完这崇山峻岭的呢?
低矮简陋的庄稼院散落在沟的两边,高大壮实的杨柳榆槐们投下片片绿荫。没有鸡叫狗咬,一片恬淡宁静。因为缺水和偏远,横岭已整体搬迁到山下公路旁的大南庄去了。
村里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一口百年古井还在。它仿佛在讲述着小芹、小二黑的故事,讲述着赵树理在这里创作的过程。
生活中的“小二黑”叫岳冬至,是村里的自卫队长;“小芹”叫智英贤,是村里最漂亮的姑娘。父母给岳冬至买了个不足12岁的童养媳,智英贤被父亲订了“娃娃亲”。两个都被视为已经成家的人还经常在一搭“鬼混”,这不能不引起乡人的非议和嫉恨。于是,在村里为所欲为又醋意十足的村干部将岳冬至活活打死,移尸岳家牛棚,伪造了上吊自杀的现场。事后,忍受不了可畏人言的智英贤远嫁他乡,一生再没有回过横岭。
当时,赵树理正在中共北方局党校调研室工作。听罢岳冬至叔叔的哭诉,他放下饭碗就往横岭赶,对惨案进行了详细调查,并听取了侦察员对案犯的审讯。而后,他在临街的一户干属家里住下,捻亮一盏昏昏欲睡的麻油灯,开始了《小二黑结婚》的创作。
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基本符合原型。但当他写到小二黑被活活打死时,竟无法写下去了。他觉得这样写太憋气!如果光是揭露封建传统、恶霸势力的残酷无情,不去鼓励青年们为争取婚姻自主而勇敢斗争,文学艺术怎么能起到“擂战鼓”、“吹号角”的作用呢?他抓起稿子揉成一团扔了,将结局改为小二黑没有死,他最终冲破传统和家庭束缚,与小芹幸福地结合了。这才是庄稼人喜欢的“有头有尾”的故事哩!
“小二黑”家的房子仍在。牛棚则拆掉了,只留下一面石板墙,好像仍在恪尽职守地为冤死的自卫队长遮风挡雨。据说,由于是凶死,“小二黑”被深埋在村庄下方的杂树林里。如今没有几个人知道墓中是那个曾轰动一个时代的赵树理作品中的男主人公。
拐出“小二黑”家,沿着一条石板胡同前行不远,我们看见了破败的“小芹”家。
“小芹”家的斜对面有台石磨,石磨后边的二层小楼就是原先的村公所,捆绑、吊打、致“小二黑”死地的案发处。门锁着,不知钥匙在谁手里,楼梯也坏了,根本上不去。也难怪,这事儿都过去70年了。
赵树理住过的房子已荒废,再过些年,说不定全村的房子也寻不到一点儿踪迹了。但那个“像是农民又挂着几支钢笔”的作家,永远不会在乡亲们的记忆中抹去。
2
山一程,沟一程。在左权县麻田镇交沟村村头,一座崭新的黑色墓碑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上写:“先父,李有才。……与驻李家岩村工作队成员、人民作家赵树理相识,同食宿和劳动,结为至交。一九四三年底,老赵以先父为原型创作的《李有才板话》面世。至此,先父为老赵锦笔添花,老赵为先父薄名传声……”
碑志的记载很清楚:该村的穷苦农民李有才,系赵树理《李有才板话》的创作原型。他于1991去世,生前一直任村干部。
身后尾随着一只黄狗的老汉帮我们喊来了李有才的儿子李德胜。李德胜说:“赵树理和我父亲住过的老房子在山上,离这儿还有6里地。”说着,便带我们沿羊肠小道向山中进发。丛生的荆棘荒草拦腰,凶猛的长蛇夺路而过,突然传来的采药人的吆喝声让人惊悚。后悔不该来,却没了退路。
我们气喘吁吁地攀上峭壁,终于找到了老房子。可惜面目全非,没有了院墙和房顶,屋内茂盛的杂草中长出4棵大树。赵树理描述的“前边靠门这一头,盘了个小灶,还摆着些水缸、菜瓮、锅、匙、碗、碟……”这些场景更无影无痕了。
在靠西墙正中坍塌的土炕上,赵树理曾和李有才睡了半年。听着李有才久打不衰的鼾声,赵树理觉得这位“吃饱了一家不饥,锁住门也不怕饿死小板凳”的光棍汉(后娶妻生子),俨然是一位智慧的农民政治家!尽管日子过得十分清苦,可他仍然要通过编快板,向欺侮他们的豪绅地主、官僚恶霸、狗腿子们“扔砖头”。李有才身上闪耀着中华民族不为贫穷和邪恶所屈服的伟大品质,是那样可亲可爱。“对!我要写他!要为他立传!”
到了年底,《李有才板话》就出版了。开篇道:“阎家山有个李有才,外号叫‘气不死’。这人现在有五十多岁,没有地,给村里人放牛,夏秋两季捎带看守村里的庄稼。他只是一身一口,没有家眷……”从此,爱编顺口溜的“板人”李有才名扬四海。直到今天,课本里还在讲述着他的故事。
3
山一程,沟一程。来到沁水县尉迟村我们总算见到了河,一条弯弯曲曲从村前淌过的沁河。
这里就是赵树理的故乡,也是他长篇史诗《李家庄的变迁》原型村庄。
1945年,离家8年的赵树理回乡探亲,他见到了年迈的母亲、新婚离别的妻子和长大了的儿女。可是,没有见到最牵挂的父亲。
“娘!我大呢?”
已哭干眼泪的娘告诉他:“孩儿啊!你再也见不着你大了!”
1943年11月29日,赵树理的父亲提着一罐子蜂蜜去跟别人换红薯。一出门,就碰上了“清乡”的鬼子。强盗们用枪托打,刺刀捅,把他整了个半死,然后塞进茅坑放火烧了……
从父亲的坟上回来,赵树理随即走进父老乡亲们中间,调查了解日本鬼子在村里的罪行,决心用手中的笔控诉入侵者的残暴。
恰在此时,阎锡山命令其精锐部队侵入晋东南解放区,挑起了著名的上党战役。为了形象地、系统地揭露阎锡山统治山西的罪恶,赵树理改变初衷,决定描写太行山区一个村庄从大革命失败后到抗战胜利近20年间所发生的变化。于是,他又深入到附近的李庄、端氏村和杨树庄走访调查,掌握了大量活生生的素材。
那是寒冷的冬季,因为没有桌子,高大的赵树理不得不蜷曲在小炕桌前,靠着破瓦盆里的木炭火取暖。他饱含悲愤的泪水,为苦难的李家庄人民呐喊,夜以继日地书写出了《李家庄的变迁》。
《李家庄的变迁》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又一座高峰,连同他里程碑式的另两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确立了赵树理在我国文学史中民族化、大众化的历史地位。
……
1970年9月23日,农民的忠实代言人赵树理因受“四人帮”迫害,放下手中的笔与世长辞。但小二黑与小芹的婚事、李有才的光棍日子,以及三里湾乡亲们的喜怒哀乐、尉迟村父老们的柴米油盐……一切的一切,都被他揣在心中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