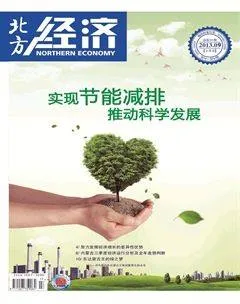国际贸易领域的劳工权益保护:多边主义的视角
国际贸易与劳工权益的关系是世界贸易体系中一个颇具争议性的问题,它既涉及对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又与贸易比较优势相关,尤其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意义重大。目前,国际上一种途径是试图用具有比较明显的“经济霸权”特点的单边主义的作法来推行劳工标准(以美国为代表),争议颇多;另一种途径是推行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公平的谈判地位和更多的谈判空间的多边主义,即通过国际组织的协调和立法来推行劳工标准,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将讨论采用多边主义保护劳工权益的现状,分析该体制的成就和缺陷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一、国际劳工标准的提出和确认:ILO的角色和作用
目前,国际上最重要的劳动者组织是国际劳工组织(ILO)。它是最重要的劳工权益保护的国际倡导者,其宗旨是在所有国家实现劳动条件和生活标准的改进,普及对工人的平等公正的待遇。ILO为国际劳工权益保护立法和监管的多边机制提供了一种典型范式。
(一)核心劳工标准的概念
ILO一直致力于建立具有国际效果的规则或者“标准”,途径是创制公约和建议书。迄今ILO已制定了189个公约和202个建议书,其内容涵盖了劳工权益的方方面面,如最长工作时间、夜班问题、最低就业年龄、工人疾病保险等。
在众多的劳工公约中,ILO确认其中八个为所有成员国都应当尊重并遵守的“核心公约”,并正式提出了“核心劳工标准”的概念。核心公约涵盖了四方面内容,即: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权(第87号和第 98号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劳动(第29号和第105号公约),废除和禁止使用童工(第 138号和第182号公约),消除在雇佣和职业方面的歧视行为(第111号和第100号公约)。核心劳工标准被认为体现了社会发展中应有的公平、正义并在维护劳工权益和基本人权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框架式要求,是经济有效运行的保证。
(二)ILO的执行和监管机制
ILO对核心劳工标准的制定和确认是一次成功的立法行为,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成员国对于劳工标准的执行和对劳工权益的保障仅依靠自觉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强大的保证执行的制度和手段,这直接决定了有关公约的有效性。
目前ILO对于其公约的执行和监管机制可以概括为两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被ILO称为“常规监管机制”,分为三步。首先,根据ILO宪章成员国有义务定期提交报告以说明对公约的执行情况,并由ILO执行专家委员会对报告进行分析和评估;第二,在检查报告的基础上,ILO将提出改进意见;第三,如成员国对公约有执行困难,ILO将进行对话和提供技术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在“常规监管机制”中,ILO专家委员会的意见是不公开的。而当该成员国不针对问题进行修正时,ILO可能会将该国列入特别名单,并在网上公布它的报告。ILO认为,一旦报告公之于众,涉及到的国家就可能受到各方的批评。为避免此情况的发生,该国将自觉对其违反公约的行为进行修正,从而解决好劳工标准的执行问题。
第二条路径被称为“特别程序”,又包含两个情况。第一,当某一成员国违反其签署的某一公约时,其他同样签署了这一公约的成员国可向管理机构提出申诉,或者由雇主/雇员联盟提起抗议。第二,如果ILO成员国违反的是有关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公约,鉴于ILO认为这两个公约尤其重要,所以无论违反这一公约的成员国是否签署了这两个公约,ILO都会启动调查程序。在特别程序中,一旦ILO发现成员国有违反公约的行为,而又未能在一定时间内给出满意的答复,管理机构将把雇主/雇员联盟提出抗议和成员国未给出满意答复等事实公之于众,或者管理机构将依据ILO宪章第33条的规定,“采取一切明智的,且有利于敦促成员国遵守公约的行为”。
(三)ILO执行监管机制的缺陷和效果
针对保障公约和劳工标准的执行,ILO已经确立了一套包含有成员国政府、雇主和雇员等三方共同参与的监管机制,但从具体操作看,最严重的缺陷在于缺乏有力措施使成员国支付违法成本,而仅试图通过“公开事实”,或 “列入特别名单”的作法向违反公约的成员国施加道德压力,迫使其发生趋善的改变。因此从根本上说,ILO的这套监管机制主要是道义性质的,不具备强制力,也就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约束。
首先,如前文所述,ILO十分重视“公开事实”的做法,从常规监管机制到特别程序,当成员国违反公约又不能修正时,ILO都将“公开事实”或列入“特别名单”做为惩戒措施,换句话说,ILO把成员国的“耻辱感”当作是其监管机制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ILO缺乏具体的惩戒措施,最终成员国是否对自己的违反公约行为做出修正,依赖的仍然是国家的自觉。
其次,从ILO对其监管机制的表述来看,其最有力的措施是上述ILO宪章第33条的规定。这一规定于2000年第一次被援引,目的是应对缅甸违反强迫劳动公约的行为。当时,ILO号召其他成员国审查同缅甸政府的关系,并对缅甸采取适当的措施。由此可见,ILO并没有能力对其成员国直接进行制裁,最有力的行为也只是号召其他成员国采取制裁等行动。ILO监管机制要发挥作用依赖的是成员国的配合,所以其效果并不明显。
总之,ILO是一个成功的立法者,帮助确立了很多在国际社会被广泛认可和接受的劳工标准。从执法的角度说,它对于违反公约的行为,除了道德劝说外,缺乏其他具体的惩罚措施,因而不能根本性地解决好公约执行的问题。学者们由此提出了很多的解决方案,其中提到最多的是让ILO和WTO合作,依靠贸易制裁来解决ILO的劳工标准执行问题。
二、WTO与ILO的合作基础及障碍
(一)WTO与ILO存在合作基础
首先,劳工权益保护问题之所以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并纳入国际贸易领域进行讨论和分析,主要在于劳工权益保护会对劳动力成本和比较优势产生重要影响,并由此作用于国家间的贸易方式和流量。这就是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连接点。而WTO是解决国家间贸易问题的最大国际组织,也就是说,WTO天然与劳工问题存在关系。
其次,GATT/WTO框架下已经有关于劳工问题的规定,在劳工问题的认识上和ILO是一致的。GATT第20条(一般例外)第e款中规定了禁止监狱劳动。虽然GATT没有明确是否允许用贸易制裁的方法来惩罚那些侵害劳工权益的成员国,但是GATT第20条a款“关于允许成员国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公共道德”的规定,被认为可能会被援引作为贸易制裁违反劳工标准问题的依据。
再次,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为国家之间的贸易纠纷提供了有效的解决途径,也为ILO成员国劳工标准执行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制度范式。WTO和ILO一样,不是超国家的组织,但是WTO却成功建立并运行着一个类似于国家司法机构的系统——争端解决机制。在这个机制下,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纠纷可以提交到争端解决机构,由专家小组予以裁决,如对裁决不服,还可以上诉到“上诉结构”。更关键的是 WTO争端解决机制确立了“授权报复”的执行机制,以确保争端解决机构裁决的有效执行,而这正是目前的ILO监管机制所缺乏的。
(二)WTO和ILO合作的障碍较大
1.GATT第20条(一般例外)的援引存在障碍
前文提到,GATT第20条可能被援引,作为使用贸易制裁的方法处理劳工问题的理由。但是GATT第20条中,除了(e)款“禁止监狱囚犯产品”直接提到了国际劳工标准的内容外,跟劳工问题有关的只有(a)款“保护公共道德”和(b)“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或健康所必需”。这里存在的最大援引障碍是,“保护”的对象是谁?从GATT的规定来看,“受保护的对象”应该是进口国的公共道德、人类和动植物。其逻辑是,出口国的某些违反国际劳工标准的作法将最终有害于进口国的利益,所以进口国提出反对才是正当的。如果将“受保护对象”扩大理解为“也包括出口国”,那么就可能引发“干预外国国内事务”的管辖权争议。
那么,利用WTO进行贸易制裁是否会出现“干预外国国内事务”的问题呢?国家之间发生贸易争端,往往有一方受损或者可能都受损,因此有动机也有资格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出申诉,也即发起申诉的一定是利益相关方。然而在劳工纠纷中,受损的直接一方往往是违反劳工标准的某国的本国劳动者。除非提起申诉的国家能够证明,他国违反劳工标准的行为有害于本国的贸易利益,否则实施制裁很有可能会被认为“干预外国国内事务”。
2.“社会倾销”概念含糊,难以判断和证明
起诉方(国)可以利用“社会倾销”的概念来说明外国的违反劳工权益的情况已经影响到了本国利益,从而在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起申诉时获得“利益相关方”的资格,然而“社会倾销”概念含糊,难以判断和证明。关于“社会倾销”目前还没有权威的定义,一般认为是指国家为降低生产成本,而执行较低的劳动标准,然后将在此恶劣环境下生产的产品销售到外国去的行为。社会倾销被认为是低标准带来了低价竞争优势,这一点和倾销类似,不同在于社会倾销强调的是这种低价竞争优势的来源是“故意被降低的劳工标准”。而事实上,由于概念模糊,定义不清,社会倾销比倾销更难判断和证明。WTO《关于实施GATT1994第六条的协定》对倾销、损害等重要概念给出了明确规定,但这些规定并不能适用于社会倾销的判定问题。因此,所谓“社会倾销”是否成立很难认定。另一方面,GATT第六条(反倾销与反补贴)着眼于讨论和消除倾销对于进口国的影响,而不是出口国的生产条件。而社会倾销的关键点在于出口国国内通过降低劳工标准而获得某种比较优势。两者的着眼点不同也导致GATT第六条和WTO反倾销规则不能适用于社会倾销。
3.ILO不具备使用WTO“授权报复”措施的前提
WTO“授权报复”实施前提是成员国通过关税减让给予了对方和其他成员国以优惠。因此,在争端解决机构裁定生效后,胜诉方可以要求败诉方修正其贸易行为或者给予补偿。同ILO一样,WTO也首先希望败诉方能自觉执行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但是,不同于ILO仅仅依靠道德劝说的方法,在败诉方不主动不自觉的情况下,WTO允许胜诉方通过“收回”关税优惠的方式来对败诉方进行“报复”。也就是说,“授权报复”的前提是双方先处于相互给惠的情况,所谓“报复”就是收回起初给予的关税优惠。然而, ILO的成员国并没有在其框架下给予对方事前优惠,因此缺乏“授权报复”的前提。WTO的“授权报复”虽好,ILO却不具备效仿的前提。
(三)WTO在劳工标准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
尽管WTO和ILO的合作存在可能性,但要在WTO加入劳工条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事实上,在东京回合和乌拉圭回合中,美国两次提出在WTO的有关规则中包括一个“社会条款”,以便惩罚那些在国际贸易中因实行低标准而赢得不公平竞争的国家。但这一提议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两方意见是如此的不能调和,以至在1996年新加坡部长会议上,WTO提出“我们再次承诺,承认并且遵守国际承认的核心劳工标准,ILO是建立和处理这些标准的机构,我们确认支持其促进这些标准的工作。我们相信,不断增加的贸易和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经济发展能促进劳工标准的提高”,并且,WTO和ILO的秘书长将“继续他们之间的合作”(Hilary Kellerson,1998)。这段话一方面对ILO提出的国际劳工标准予以了认可和接受,指出两大组织的合作关系;但另一方面,又巧妙地划出了一定的界限,说明劳工标准问题首先还是ILO的问题,所以对于合作关系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操作蓝图。
三、结论
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劳工状况与经济、贸易等的重要关系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利用劳动力供给丰富、生产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保持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还要顺应国际社会的呼吁和潮流,加强和提高对于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因此,在劳工标准的制定和推行以及劳工权益的保障方面不能做一个“旁观者”和“接受者”,而应该更加积极地投身到相关的国际立法和国际合作中去。相对单边主义所造成的被动局面,多边主义是更好的选择。比较单边主义的作法,多边主义更为公平,也给了发展中国家更多表明立场和态度的机会。对于采用多边主义来推行劳工标准的作法,发展中国家可以报以鼓励和合作的态度。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康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