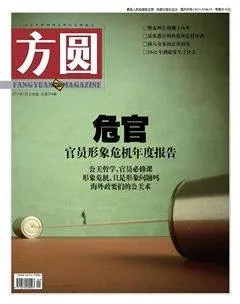1942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面对这样一场全省范围内的大饥荒,重庆乃至河南省政府所启动的救灾方案,虽可谓面面俱到,但因未能考虑到实际情况而实效惨淡
近日热映的历史灾难片《一九四二》,讲述了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这段历史,但这部广告词自诩为“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的电影,事实上,并未能够如实地还原那段历史。
河南省府当局向重庆瞒报了灾情
电影《一九四二》里的民国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为报灾去到了蒋介石跟前,结果又畏畏缩缩把话吞了回去。这一幕让人印象深刻。
但冯玉祥在1947年于美国写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蒋介石》中却不是如此表述的,冯玉祥写道:“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向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地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地骂了一个钟头。可见对于人命毫不关心。”
但是这两种表述,恐怕都不是史实。
根据史料,重庆方面收到河南省政府关于1942-1943年饥荒的报告,最早可以追溯到1942年7月。7月21日,针对此前持续数月的干旱,以省主席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决定向陕西购小麦10万大包,同时电请中央政府对1942年度本省征购粮食数目核减200万石。重庆作出反应,将河南1942年的粮食征购数额由500万石减为380万石。但遗憾的是,李培基此举虽然为河南百姓争取减少了120万石的征粮负担,但其发往重庆的电文,却远未如实反映河南的灾情情况。
河南省赈济会1942年秋推举了杨一峰、刘庄甫、任兆鲁三人,代表河南各界前往重庆报灾。据杨氏回忆,他们“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返回河南后,杨一峰等人“曾经质问李培基何以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李支吾以对”。
杨一峰一行抵达重庆时大约是9月份,据杨氏说:“抵渝后,始知中枢因受省政府谎报灾情不重之蒙蔽,即旅渝同乡亦鲜知灾情如是之严重。”此时,河南本地官绅马乘风曾向重庆上书报灾,但因河南省政府报告河南无灾,所以其报告并未产生效果。稍后,驻防河南的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珏前赴重庆面见蒋介石,也曾报告过河南的灾情,蒋介石闻知后要李速去找何应钦,何应钦回答:“灾情是不能随便报的,鄂西有灾,因为地方政府有报告,河南方面未见地方政府报告,何来的灾情?”事实上,直到1942年9月初蒋介石亲往西安王曲军校主持军事会议,以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方面对灾情程度的报告,仍然比实际灾情要轻很多,以至于在会上与以蒋鼎文为首的军方报告出现正面冲突,后者认为灾情要严重得多。
河南省政府当局向重庆瞒报灾情一事,时任河南省粮政局秘书的于镇洲晚年也有详细的回忆:“弟供职省粮政局,驻鲁山康庄,亦为灾情严重之区。弟为报灾事,屡向卢局长郁文建议,应速将真实情况转报中央,但均未被采纳。……灾区范围,以黄泛区扶沟、许昌为中心,周围数十县份,纷纷报灾,省政当局以麦苗茁壮,误认各县系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公文往返,拖延勘查,不肯据实转报中央。”于镇洲还说,洛阳军方曾将灾情实况报告给重庆,但因与省府报告相反,而遭到重庆方面的申斥:“当时驻洛阳司令长官(蒋鼎文)虽将灾情实况上报,因与省府所报不同,复蒙中央申斥,军政双方曾因此事引起极大的不快。”
李培基自己是怎么解释迟迟不向中央实情报灾的呢?1943年接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刘恩茂晚年回忆说:“当张溥泉和张厉生两位大员到河南勘察灾情时,……张厉生先生当面问李培基为何不报灾?李培基说:‘起初看到二麦麦苗丰秀,不会不下雨,谁知皇天这王八蛋刮来一阵黄风,一夜之间把麦苗刮干了。’张厉生先生又问:‘有了这样情形,为何还不报灾?’李培基说:‘我见早秋长得还好,谁知皇天这王八蛋又来个搦脖旱!’”
李氏的这种辩解很无力,金汉鼎1943年被重庆当局派往河南调查贪腐问题,据他回忆,在中央派张溥泉和张厉生前往河南调查时,“李培基主席率领有关人员在赴会途中,告知专员李杏村向代表们说:‘不要把灾情说得太严重,主席自有办法。’”
重庆国民政府不允许媒体报道灾荒吗?
重庆《大公报》1943年2月3日因刊载该报主持者王芸生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而被当局停刊三天。电影《一九四二》据此演绎,认为重庆中央政府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这其实是对史料的误解。
曾担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部长的王世杰,在其1943年2月4日的日记里披露,其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是:“《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当然,《大公报》指责政府限价不力,其实也是在指责政府救灾不力。但“指责政府救灾不力而被停刊”,并不能等同于“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
事实上,在《大公报》被停刊之前,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灾荒的报道至少已有40余篇,《大公报》遭到处罚后,到1943年6月,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饥荒的报道数量,至少也还有80余篇。重庆《新华日报》当时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其刊登的内容,和重庆《大公报》一样需接受国民政府新闻检查机关的审查。这100多篇关于河南大饥荒的报道,都没有被当局封杀。
再以当事者《大公报》为例,自1942年9月到1943年6月,其关于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记者白修德推动了政府救灾?
美国记者白修德1943年3月22日曾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报道河南饥荒。白氏晚年在其回忆录里引用一位“梅根神父”的来信,认为正是因为自己的报道,才迫使无心救灾的国民政府行动了起来:“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发挥了很大作用。”
电影《一九四二》乃至多数国内媒体均照搬了白氏晚年的这一说法,认为可信,电影还据此塑造了两位高尚而勇敢的国际友人形象。但事实并非如此。白修德在《时代》周刊报道灾荒时,中央及河南的救灾工作其实早已全面展开。
1942年9月16日,河南省救灾委员会成立;9月28日,省主席李培基正式发表讲话,高调宣布“今后本府决定将救灾一项,定为中心工作。”此后,整个河南省政府的运转,即彻底转入救灾模式。而在此前的王曲军事会议上,中央已直接减少了河南的军粮配额,并立即从陕西开始向河南运粮。
总体来说,1942年9到10月间,可视为中央及河南地方救灾工作的第一阶段。其内容主要侧重于调查灾情及救灾计划、办法的拟定。调查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查勘各县灾情实况,详细记录“充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种户口;具体的救灾计划和办法则依据上述调查制定。
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可视作救灾的第二阶段。此一时期,各项救灾工作均已分别展开。中央发放了三次急赈款;河南省政府自筹赈款500万,并在陕西购得麸皮300余万斤运回发放,地方亦筹款1000万。针对流民的各种以工代赈(主要是兴办农田水利,如疏通河道,开凿水渠等)也搞了起来。最关键的粮食问题,先是向第一战区长官部借了后方的囤粮3.5万包,又向汤恩伯部借粮160万斤,军队节食麦300万斤以及向陕西省购买的存麦2万包,都分别发放了下去;各县所存的仓谷,也勒令必须在1943年麦收之前全部散发给灾民;其他如查封大户存粮、设置粥厂、组织募捐等工作,均是在此一时期大规模展开的。对逃荒的灾民,则根据其逃荒的主要路线沿途设置救济站,供给灾民吃住。
也就是说,白修德3月22日在《时代》杂志上刊文时,上述救灾工作,均已全面展开。“粮食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不是白修德报道后的结果;“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也不是因为白修德的报道;“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的时间更远远早于白修德的报道。白氏在灾区不足20天,走马观花的报道并不可信。
当然,1943年麦收(6月份)前的四个月是灾民最困难的时期,旧储已尽,新粮未收;所以,白氏在河南看到的灾情之惨烈,确属事实;但白氏认为当局此前不救灾,自己使灾荒成为国际新闻后才开始救灾,则只是他个人的一种想当然而已。
政府采取了哪些救灾措施?
《一九四二》在描述政府救灾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但实际情况是,面对这样一场全省范围内的大饥荒,重庆乃至河南省政府所启动的救灾方案,虽可谓面面俱到,但因未能考虑到实际情况而实效惨淡。当时的救灾措施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中央允许河南在1943年麦收前不再征粮。1942年10月,中央因杨一峰等人的报灾而派张继、张厉生赴河南实地勘察,根据勘察结果,中央最终决定:将河南的征粮负担核减为280万石,合200万大包;同时准许河南在1943年4月以前先交140万包,其余60万包容后再交。这实际上等于允许河南在1943年秋收之前不再向百姓征粮——因为在1942年9月之前,河南省府已经完成的本年度征粮任务,实已超过140万包。
其二,在河南省救灾委员会主持下,对辖下68县250万户进行调查,按受灾轻重划分为充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种户口,作为救济的根据。调查结果认为:68县250万户中,不足、待救者达220万户。依据调查结果,各种救灾机构和具体救灾计划,均在此一时期设立、制定。
其三,放粮筹粮。河南省在1942-1943年曾三次开仓救灾,直至用尽各县所存历年积谷。政府还强制查封散发了大户余粮共计8.8万石。又由省政府出面,筹集资金,向邻近陕、皖、鄂各省平价购买粮食。据《河南政府救灾总报告》的不完整统计,购回配销出去的粮食,至少在3亿斤以上。
其四,移民。由官方负责遣送至陕西者30余万人,遣送至湖北者2万余人。此外,为便利灾民自发移民,蒋介石在1942年末曾亲自下达手令,命河南省救灾委员会沿陇海线,在重要地点设立粥厂,救济西去逃荒的灾民,其经费全部由中央拨付报销。自设立至结束,共耗费经费800余万元,救济灾民达55.8万余人。此外,省内各县亦普遍设立粥厂,总计4289处,收养灾民189万余人。
其他措施还有为农民筹集各种种子、强制保护牲畜以利于生产恢复,驻豫军队及公务员全体参与节粮救灾等等。
总而言之,当时的河南省政府,确如李培基自己所说,已把救灾工作变成了全省的“中心工作”,对各级官员的考核,也从灾前的征粮任务完成状况为依据,转变为完全以救灾成绩为依据。
当然,不可否认的,这些面面俱到的救灾措施,并不能彻底拯救河南1000余万灾民,首先,此灾在当时的环境下,已非人力所能拯救。河南地处抗战最前线,三面受敌,境内百姓的余粮,已被战争耗尽。本省无粮,成为制约当局救灾的最大瓶颈。而要将本省灾民运出去,或将外省粮食运进来,则又受制于交通条件。此一时期,河南唯一的现代交通枢纽,即自西安经潼关至洛阳的这一段陇海线的一部分。但就是这唯一的一段陇海线,其运输能力也相当有限。尤其是1941年中条山战役之后,黄河北岸渡口均被日军占据,潼关、会兴段其间各站,几乎无一日不受炮击。一有行车,日军就立即发炮。白天无法行车,晚上行车也只能关闭灯火,高柏至东泉店间甚至被迫停开列车,改用汽车盘运。更何况陇海线上超过四分之三的机车都处于维修或被破坏根本无法使用的状况,其运输能力可想而知。
恰如美国外交官谢伟思1942年11月在河南所调查到的那样:“粮食现在也正在运往河南省,但数量很小……潼关火车站站长说,他不知道运粮的吨数,但他对我说每晚通常有两列火车东驶,每列平均10节车皮,容量15到40吨不等。据我所见,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因此,我估计一个月至少可向河南运进1.5万吨粮食。”按照谢氏调查的数据,意味着这段陇海线即便“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一个月也只能向河南输送三千万斤粮食,而河南国统区的灾民有一千多万人,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只能从这唯一的铁路上获得三斤粮食而已。
并且,众所周知,此一时期的国民政府其中下层统治机器已经完全腐败化,这种腐败,毫无疑问会使饥荒雪上加霜。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档案中保存有一份《张光嗣关于河南省旱灾情况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1943年9月27日)》,调查者张光嗣1943年5月至9月,深入河南重灾区,调查灾情何以如此严重的原因。其中说道:“各县乡长及保甲长大多数人选极坏,关于赈款、赈粮、耕牛贷款及其他一切征物派款之营私舞弊已成最普遍之现象,甚至县长虽明弊端百出,亦故作痴聋,以致民怨沸腾,不惟影响救灾,即于政务推行亦影响甚大。”
日军用军粮救济中国灾民?
电影《一九四二》里有一个颇受争议的镜头: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在飞机上巡视河南灾情,要求日军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军官们疑惑不解:“……可是他们是中国人啊!”冈村说:“别忘了,他们首先是人!”
电影的原著,刘震云的纪实作品《温故一九四二》里更是说:“……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很多人还流传下来,繁衍生息,五十年后,俨然又是在人口上的中国第二大省。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不是。是蝗虫又自动飞走了吗?不是。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当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
无论是按照电影的表达,还是按照原著的叙述,日军用军粮救济中国灾民,都应当是一种政策性的措施。但事实是:个别日军给灾民发粮的情况未必没有(笔者并未查到相关记载,但毕竟不能逐一排查,难以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日军政策性的向灾民放粮,则肯定是子虚乌有。
刘震云纪实作品《温故一九四二》里的硬伤自不必提——这篇纪实作品,以刘氏对自己家乡河南省延津县1942至1943年饿死人的情形的调查为主轴,辅以各种历史档案文献构筑而成。刘氏在作品中引某“四九年之前的县书记”的回忆,称其家乡延津县饿死人“总有个几万人吧”。但刘氏始终没有告诉他的读者,他的家乡延津县,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他在延津县的“乡亲们”被饿死,与国民政府并无关系,他的“乡亲们”恰恰饿死在日军统治下。
而据谢伟思1942年11月在河南的观察,“在日军占领区,没有进行任何救济工作”,丁玲1944年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一文援引晋冀鲁豫边区的统计数据,称“太岳区由豫北各地逃来难民前后不下二十万”,豫北完全属于沦陷区,在日军因壮丁紧缺而严防灾民外逃的情况下,二十万灾民逃入根据地,已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沦陷区灾民死亡情形之惨烈,可参考刘子丰《1942年大旱灾纪实》一文。刘氏是濮阳人,1942年饥荒时12岁。当时濮阳已全部沦陷,刘氏该文说:“西郭村当时全村280户832人……1942年外出逃荒要饭者150户675人,占总人口的81%,卖儿卖女的50户,占总户数的20%,卖儿女54人。由夫改嫁者21人。饿死绝户的18户72人。”
如果果真如电影所叙述,日军政策性地在沦陷区给灾民发粮赈济,怎么产生如此多的流亡者和饿死者?
《一九四二》剧情简介
一九四二年,因为一场旱灾,河南地主范殿元赶着马车,马车上拉着粮食,加入往陕西逃荒的人流。
一路上历经炮火与严寒的磨难,流亡的三个月里,范殿元的车马都没了,与其同行的亲人死的死,离开的离开。其间河南省政府、中央政府使用多种措施救灾,仍未能避免大量百姓的饿死。美国记者白修德深入灾区报道了饿殍遍地、“狗吃人”的惨象。
千辛万苦到达潼关的范殿元,最终又被军队卡在了陕西边境,不许移民。最后他决定不逃荒了,开始逆着逃荒的人流往回走。“没想活着,就想死得离家近些。”
范殿元的遭遇是三百万灾民的缩影,严冬与大灾相映出当时河南的凄凉,政府救灾不力,中日战事临近,使得河南的大灾甚至差点沦为中日双方争相抛弃的负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