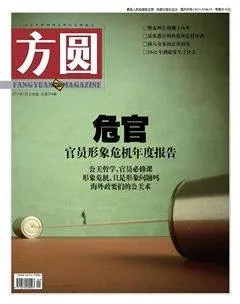国内诉讼:对日索赔的最后一种可能?

【√】中国二战受害者20年来在日本的索赔经验证明,对日诉讼不可能赢。于是,在学者的建议下,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选择了在国内诉讼这样一条新的途径
“过几天,我们就会在国内提起第二批起诉了。”12月9日,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教授潘国平告诉《方圆》记者。此前9月16日,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向重庆市高级法院提起对日索赔诉讼。至于第一批的诉讼结果,“重庆高院还在要求我们补充证据,没有正式受理。”
中国二战受害者的对日索赔诉讼战已经打了十几年,曾经轰动一时的劳工案、南京大屠杀案等,已经渐渐消失于人们视线。“因为始终没有结果,很多曾经参与其中的律师、学者觉得疲惫不堪,都不想再参与了。”潘国平说。
在这个国际法学者看来,此次重庆大轰炸在国内提起的诉讼,也许是对日索赔的最后一种可能。
山城往事
十月的山城重庆,几乎每天都在下雨,弥漫着浓重的雾气。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就隐匿在繁华的较场口商业区中间,远远看去,并不十分显眼。遗址就建立在当年的防空洞口,只有三四平方米,如果不是封锁的地下通道入口和栅栏内墙壁上悬挂的惨案照片,很像是现代城市里的一个地铁入口。
1941年6月5日,日本对重庆进行了连续五个小时的轰炸,这个当年重庆市主要的防空洞口被炸塌,洞内躲避轰炸的数以千计的市民因窒息而亡。这个事件被称为较场口惨案,它仅仅是日本从1938年到1943年持续五年时间对重庆施加轰炸袭击的其中一幕。
2012年10月7日,93岁的幸存者王树臣向《方圆》记者讲起当年,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抱起头来,浓烈的重庆口音中透出深深的恐慌。抱头是遭遇轰炸那几年养成的习惯,飞机来,有轰炸声,就往防空洞跑,跑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护住头部。
王树臣回忆,1939年5月3日,轰炸机又一次来了,他在重庆渝中区洪学巷街上朝防空洞跑时,被弹片伤了右腿,经抢救医治至今腿上仍然存有骇人的伤疤。受伤的王树臣开始到处流浪为生,乞讨打工,直到建国后才有了稳定的工作。
因为至今犹存的愤怒,9月10日,王树臣和当年的另外14名重庆大轰炸受害者一起正式向重庆市高级法院提起了对日本的诉讼。另外14名受害者大都有着与王树臣相似的经历。在当事人亲口叙述的历史中,发现这些如今幸存的受害者,在长达五年的轰炸中,或家人去世,或流离失所,都过着无比提心吊胆的生活。
对日索赔的死胡同
10月8日,这是国庆长假过后的首个工作日,因为重庆市高级法院迟迟没有对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索赔案立案,很多人都有些着急。当年受害者或者受害者家属大概有56人,参加了重庆大轰炸在国内正式起诉后的首次沟通会议。会议现场,满眼可见斑白的银发,佝偻的身躯,他们都是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原告团(以下简称原告团)的成员。
原告团办公室位于较场口惨案遗址旁的一所写字楼里。早过古稀的卢贤柏是这里的常驻值班人员,担负起了原告团的大部分联络工作。据卢贤柏介绍,2002年,一些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自发组成了这个组织,但因为无法取得正式的民间团体注册,只好在原告团的后面加个括号“筹备组”,至今如此。2004年以前,这间办公室的租金一直由一名港商赞助,这里逐渐成为许多受害者集中商讨诉讼事宜的地方。
从1988年山东茌平县张家楼村400村民集体的“第一份对日公开索赔书”开始,中国二战受害者提起对日诉讼索赔的案例越来越多,在2002年至2004年间达到一个高潮。较为社会所熟知的中国劳工对日索赔案、南京大屠杀对日索赔案、慰安妇对日索赔案等等,主要发生在这期间。这些案件无一不是选择了在日本地方法院起诉,多数经历了漫长的一审、二审,直至最高法院,然而,最好的结果也就是通过庭外和解拿到一些赔偿,大部分直接就败诉了。
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的对日索赔诉讼也是在这波高潮中开始的。诉讼从2002年开始筹备,2004年律师团组建完成。2006年3月律师团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交了起诉书,同年10月25日本案才在东京地方法院开庭审理。
卢贤柏曾作为原告团代表于2006年、2007年两次赴日本法庭作当庭陈述。他的父亲卢汉全在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中去世,“母亲在废墟里找到父亲时,他的头已经被烧焦,手上还紧紧握着家人的照片。房屋被夷为平地,从那以后,我们过的是四处流浪的痛苦生活。”过去快七十年了,向《方圆》记者叙述起当时的经历,老人还是忍不住哭了。
最开始,原告团与重庆中小企业法律服务中心签订了协议,委托其组建律师团,身为重庆中小企业法律服务中心主任的林刚,就是这时候作为律师团首席律师正式加入重庆大轰炸对日索赔工作。“根据协议,我们跟重庆市多家律师事务所进行了沟通,差不多二十家律所同意派人援助这个诉讼。”
然而,不是所有的等待都会开花结果。原告团于2004年在日本提起的诉讼,与其他中国二战受害者在日诉讼相同,没有逃掉被“拖”的宿命。
随着时间的越拖越长,很多自掏腰包前往日本支持诉讼的律所和律师都慢慢退出了。林刚是少数仅存的支持者之一,8年来,他觉得自己“筋疲力尽”。
“日本律师传来消息说,明年年底,或者后年年初,很可能会出终审判决。”卢贤柏说,但结果恐怕并不乐观。“因为前年说去年能宣判、去年说今年宣判,都没有实现。”
无论如何,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在日诉讼部分已处于收尾阶段,律师团和原告团方面不准备再增加原告人,因为在日诉讼看起来难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新的通路
2011年,当重庆大轰炸在日诉讼索赔经过7年,几乎走到末路的时候,潘国平介入了进来。
潘国平曾参加过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审判战犯的工作,此前还作为顾问参与过中国劳工对日索赔案。2011年,他受西南政法大学之邀被聘为国际法学教授,不久后,他即接触到了重庆大轰炸原告团。
在潘国平看来,“20年对日索赔诉讼的经验证明,法律有时候很冷酷,日本政府不可能让我们赢得这类官司。”
据潘国平介绍,国际上战争索赔通常使用三种途径:第一种是在侵略者所在国起诉,中国大多数二战受害者采取了此种途径。这种途径的好处是一旦胜诉,执行起来会相对容易;但诉讼中必须面临诸多实际困难,例如赴境外出庭的高额费用、聘用当地律师困难等等,而且,这样做更容易受到所在国的政治影响。“就目前来看,在日诉讼是全军覆没。很多律师、学者参与对日索赔都是公益性的,高额的费用和长时间的诉讼过程让他们苦不堪言。”潘国平说。
第二种,在第三国提起诉讼。譬如中国劳工在美国起诉日本三菱、三井公司案,就是采取了的这种途径。但这种起诉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被告在第三国有住所。
第三种是通过国际法院进行诉讼。然而,依据《国际法院规约》和《国际法院规则》,向国际法院提交的案件,原告和被告都必须是国家,我国民间的对日索赔都是个人行为,再说我国并不承认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因此,通过国际法院进行诉讼明显行不通。
其实还有一种途径:在受害者所在国提起诉讼。按照国际法的属人管辖原则,受害者所在国法院也应当拥有管辖权。潘国平认为,日本在重庆的大轰炸是对平民和军事设施的无差别打击,明显违反国际法,在重庆提起诉讼是一种值得尝试的渠道。
诉讼时效、证据收集、放弃索赔请求权和宣判后如何执行,是外界对于对日索赔案最常见的四个疑问。潘国平表示,本次在重庆提起的对日诉讼,这些都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日本能否享有国家主权豁免。”
日本能否享受国家主权豁免
国家主权豁免是国际公法中的一个概念,意指“国家的行为及其财产免受他国管辖”。简单来讲,就是说我国的法院不能受理对一个外国政府提起的诉讼,不得对外国的财产实行扣押。此次重庆大轰炸受害者以“日本国政府以及其法定代表人内阁总理大臣野田佳彦”为被告,这些被告无疑都是国家主权豁免的保护对象。
学理上,一些学者主张绝对的国家主权豁免,即享有豁免权的人无论违反了何种罪行,都不应当由他国进行司法审判。也有学者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行为都应受到这种保护。为此,国际法学者提出了规范等级理论,认为“当一个国家违反有关人权保护的国际强行法规范时,其豁免即被废除”。规范等级理论从两个方面解释了豁免的丧失:其一,当一国违反强行法规范时,它就默示放弃了主张豁免的权利。其二,违反强行法规范的国家行为被视为不受保护的国家行为,此种行为由于践踏了国际社会的意愿而丧失了合法性。
事实上,大多数国际法学者都主张对几种最严厉的反人类犯罪不适用国家主权豁免。例如国际法院法官特林达迪(Can ado Trindade)认为:对于反人类的犯罪行为不应享有豁免。在国际犯罪案件中,真正不能被忽视的是个人,作为个人应当享有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
这种理论目前在西方社会颇具影响力。希腊最高法院2000 年判决的“维奥蒂亚县居民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案”是目前为止法院采用规范等级理论审判他国政府的最重要案例。在该案中,希腊最高法院认为:“第三帝国机关在法院所在地领土上进行的恐怖谋杀,客观上并非维持该地区的军事占领或抑制地下活动之所需,是主权权力的滥用。”而且,此类行为“违反了强制国际法规则,不是公法行为”。由此,希腊法院认定德国已经默示放弃了豁免特权,对本案有管辖权。
1998 年,一个在二战中受到德国军队监禁和强制劳役的意大利公民费里尼(Ferrini)在意大利国内法院向德国提起诉讼,意大利最高法院也持类似立场否认德国享有主权豁免。
上述这些依据为潘国平设计“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在国内起诉日本”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在林刚和他共同起草的起诉书中,两人写道:“本案被告日本政府严重违反国际强行法,不应享有主权豁免。同时,鉴于目前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沉滓泛起,否认侵略历史,恢复军工,挑战中国主权,公然将中国领土钓鱼岛收归国有或者卖给其国民。对这样的国家,中国法院应该有骨气,顺应中国民意,否认日本政府的主权豁免。中国法院作为侵权行为地、损害发生地,以及受害者的国籍国法院,理应对本案拥有完全的管辖权。此外, 重庆大轰炸对日索赔案的被告系日本政府,案情特别重大,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由重庆市高级法院审理。”
困难并不只是在法律
距离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起诉日本已经过去两个月了,尽管原告团及其律师、专家已经开始策划第二批起诉,但距离法院正式受理并立案仍然遥遥无期。
原告团与律师团面临的实际困难不只是法律理论上的,还包括实践操作层面。
首要的便是原告团内部协调问题。据《方圆》记者了解,原告团的前身为2002年设立的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联谊会(筹备组),创始人为王永刚。最初这个团体并不是纯粹为诉讼而成立的,它还组织参与一些展览、义拍义卖等活动,筹集一些慈善资金。然而,随着联谊会的成员增多,对日诉讼索赔日益成为重要的活动内容,加上筹集来的慈善资金在管理方面出现了问题,相互之间的利益纠葛使得联谊会内部开始分裂。时至今日,原告团的负责人已经更换了一批。
其次,从2006年至今,原告团先后四次在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进行了四次提诉,188人成为原告,律师、部分当事人数次前往日本出庭。漫长的诉讼带来了高额的诉讼成本,而原告团并不是正式注册在案的公益组织,费用筹集相当困难。“去日本的费用都是我自己出。”林刚、卢贤柏等人对记者都是这样介绍的。
这为原告团的内部矛盾埋下了种子。10月8日的沟通会议上,内部矛盾险些导致了一场冲突。身为律师的林刚不得不面对受害者抛出的数个疑问:在日本的诉讼还没有结束,为什么还要在国内进行诉讼?诉讼为什么只挑选了15个人,别人为什么没有?是不是林刚在利用这起官司炒作?
林刚觉得委屈,他在详细叙述了第一批在国内起诉的15个人的产生过程之后,解释了加入原告团的标准:“在日本起诉过的人,不在选择范围内。这一次只是对日索赔诉讼路径上的探寻,人数太多,需要准备的材料就多,会照顾不过来,做事情就会费力不讨好。”而且,“律师代表受害者起诉,必须有亲笔签名的委托书,当时只和那些人签署了委托协议。”
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绝大多数都在七十岁以上,要想向他们讲明法律规定和诉讼程序,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另一方面,在向重庆市高院提起诉讼之后,法院对具体的材料组织提出了很多要求。首先是核实身份,按照我国现行刑诉法,这类附民事索赔要求的起诉,原告与受害人之间要具备“近亲属”的身份关系,即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这八种人才能代受害人提起诉讼。鉴于提起诉讼的很多不是受害者本人,就要一一审核这些材料。“工作非常辛苦,材料太多。”林刚说。
另外,由于第一批起诉比较匆忙,赔偿金额也是个大问题。《方圆》记者在起诉书中看到,最低的仅要求10万元赔偿,最高的则高达2亿,如此巨大的差距,令法院在受理时无所适从。对此,林刚咨询了一些学者,有人建议只请求赔礼道歉,不要求赔偿;也有人认为“财产损失的证据不太好收集,但人身伤害的证据比较好收集,可以考虑先就这一部分起诉”。有知情人士透露,重庆市高院内部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最高额为4万元,可以考虑在这个数字上对受害者的请求进行统一。
针对赔偿金额的问题,林刚解释:“我们考虑在第二批起诉的时候予以调整,但具体调整策略还没有出来。”
该怎样期待未来
当记者问到此案的诉讼前景时,潘国平并不讳言,他认为,在解决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这个问题上,政治问题甚至优先于法律问题。在他看来,打诉讼战是一个解决中日关系问题的好办法。“只要赢了一起,就可以形成示范效应,影响深远。”
林刚则显得有些悲壮,面对种种质疑,他说:“哪怕只剩下一个人委托我了,我也要把官司打下去!”
“胜诉的可能性非常渺茫,但我们还是要打!”“赢不赢不要紧,重要的是要日本道歉。”在卢贤柏、王树臣这样的受害者人看来,对日诉讼带来的一系列宣传效应,包括新闻发布会、日本媒体的报道和在日本的游行等等,已经达到了部分效果,如果能让日本道歉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事实上,这种宣传效应也正在显现。不少已经从重庆移居外地的老人,在看到新闻报道后,辗转找到原告团或者律师,要求加入到诉讼的队伍中去。林刚对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印象深刻,那位老人在外省看到新闻,“只身来重庆,先找记者,记者让他找法院,法院给了他我的电话他也没打,又走路到我兼职的西南政法大学,找了三天才找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