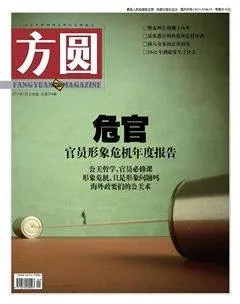活体器官移植伦理怎样审查


【√】医学讲究无害原则,所做的是对病人有帮助,但活体移植,对供者来说,没有帮助。但为什么还要做,因为不采取这个办法,另一病人生命不能延续。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无奈之举
2012年11月23日中午,在解放军309医院第二住院部肝胆外科的病房里,苏丹和她的丈夫并排着坐在两个病床中间的储物台前,喝着汤,吃着水饺。她的丈夫表现得很平静,苏丹边吃边不时对着丈夫讲话,偶尔望向病房门口,看着门口因为她的“回头望”变得激动起来的摄影记者们。
手术结束已是第23天,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面。因为术后有点小感染,医生禁止任何人探望,在场的记者们只能隔窗相望。
3个月前,苏丹得知与自己离婚两个月的前夫身患癌症,毅然决定复婚为其捐肝。从那时起,为爱捐肝的苏丹便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随后,人们也发现,原来她这样一份真情实现的背后,离不开一个特殊组织——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伦理委员会)的成全。
从被质疑、被否决,再到二轮审查,最终审查通过,用309医院全军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石炳毅的话说,苏丹吃了很多苦才成功为爱人捐肝。人们不禁好奇,这真情奉献背后有怎样的情理法的纠葛,伦理委员会究竟承载着怎样的角色呢?
两轮审查为苏丹开先例
8月31日,32岁的苏丹为丈夫田新丙捐肝申请进入伦理审查阶段。在此之前,苏丹已经背着田新丙去医院做了体检,体检报告显示她符合捐献条件。
出席审查会的12名专家,面对这份申请,有人犹豫了。12人无记名投票,8人支持,4人投了反对票。
这个结果出来后,主持伦理审查委员会的石炳毅就不断被媒体追问着一个问题: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同意一个为了爱人而作出如此牺牲的申请者?
石炳毅说,这是他最难回答的问题。“我是一直支持苏丹的。”但就连苏丹本人,也曾对石炳毅有过误解,认为是他这个主持大局的医生在阻拦。
“这个女人为了她爱的人,已经受了很多的苦,而我能帮的,就是成全她。”石炳毅对《方圆》记者说,因为是无记名投票,他也不知道那次审查是谁在投反对票。
苏丹是内蒙古人,田新丙来自河南。两人恋爱、结婚,相伴近10载,直到今年6月,二人因为对公司规范产生分歧,大吵一架,之后离婚。婚后两人暂时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为合开的公司继续奋斗。
2012年8月份,39岁的田新丙被查出肝硬化中晚期,并伴有新生小肝癌,需进行肝移植。此时,他与苏丹离婚两个月。
苏丹从医生那里得知,解放军309医院已有多名患者在等待肝源,肝源十分紧缺。可田新丙的病情等不起,于是苏丹决定自己为其捐肝。
根据国务院批准颁发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
苏丹和田新丙已经离婚。苏丹要想捐肝给田新丙,还缺少一个合法的身份。
苏丹想到复婚。她背着田新丙做了体检,并说服了父母支持自己的决定。“就算只有两三成的希望,她也要陪我来闯一下。我真的很感动。”被苏丹的父母和苏丹劝说了两个星期后,田新丙最终接受了苏丹的提议。
石炳毅告诉记者,这个过程对苏丹来说,无疑走得很艰难。有很多次,苏丹跑到他的面前哭,试图从医生这里得到帮助。
据了解,在见到苏丹和田新丙之前,伦理委员会的专家们看着资料都在琢磨,“是夫家有钱,背后存在金钱交易?还是别的原因,让这个离婚了的女人坚持复婚捐肝?”
因为这些质疑,还考虑到供体的风险,直接导致第一次审查失败。
审查失败并没有让苏丹放弃。她后来给医院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信,信中她表示,“因为我爱他”,所以一定要给田新丙捐肝。
这封信感动了很多人,包括石炳毅。他向总参卫生部打了报告,申请为苏丹进行第二轮审查。第二轮审查中,15名伦理委员会成员全部参与,全票通过。
“为供受体双方组织二轮伦理审查,这在我的执业生涯中从未听说过,可以说开了一个先例。”石炳毅说。
“审查的过程就像预审”
像供受体的苏丹和田新丙所经历的一样,活体器官移植手术前要通过两部分的审查:身体检查和伦理审查。
不难理解,所谓身体检查是通过医学检查,确定捐献器官的人是否适合移植手术,例如,供者有没有重要脏器疾病、血液疾病、待移植器官是否健康等等。
但身体检查通过还不够。荧幕上常常出现这样的情景:女一号双眼失明,悲痛欲绝,对她爱得死去活来的男三号想把自己的眼角膜换给她,无奈医生告知“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你们非亲属关系,不能进行活体移植”,男三号为了成全女主人公,开车自杀,留下捐献角膜给她的遗愿。
这样的剧情却也符合法律规范逻辑。即使活体器官捐献者身体允许,但《条例》规定了活体捐赠者的范围,不在此范围,算作违法,医院也不得施行手术。判断是否符合捐献条件,则是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的范围。
石炳毅表示,所有的器官移植都要经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不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器官捐献者,在未进入伦理委员会审查之前就已经被刷掉。以苏丹为例。苏丹申请活体器官捐献,首先要递交申请,在申请中表明与田新丙的夫妻关系,同时要附上经过公证的结婚证和户口本。
“像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可以从户口本中体现出来,但其他关系,就比较难以判断。”石炳毅介绍说,如果有人称是捐献给舅舅,那需要让其出示足够的证据,我们还要进行多方面调查,“但通常这种情况属于亲戚造假,没等上伦理委员会就被我们识破”。
除了提交关系证明,接下来最重要的审查重点便是“捐献者是否自愿”。
“主观意愿的判断很重要,这对伦理委员会成员的素质要求比较高,必须通过问话发现是否是本人真实意愿,所以我常常说,伦理委员会更像是预审科,审查的过程就像预审。”石炳毅说。
石炳毅回忆说,他接待过一位女性病人,经夫妇双方研究决定由其女儿捐献肾脏为母亲进行肾脏移植。当石炳毅与这个年仅8岁的孩子初次沟通交流时,发现女孩为脑瘫患者,不具有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且未满18周岁,显然不符合伦理学原则,家属提出的活体供肾的要求在经伦理委员会审查前被否定。
这样的例子,石炳毅每年遇到几十例。让他记忆深刻的还有一位年轻帅气的青年男子,当时,男子的母亲带着姐姐来到医院,要求为其弟弟活体捐肾进行肾脏移植。在调查中,石炳毅发现该病人对其姐活体捐肾有一定程度的强迫性。
“他们姐弟俩从小关系好,弟弟病了后,认为姐姐的肾质量高,不愿意要别人的肾源,就希望姐姐为其捐献,姐姐碍于亲情,便也同意了。”石炳毅表示,这种情况是不属于其本人真实意愿的表达。
石炳毅后来得知,该女子捐献的事情并未得到丈夫的同意,其丈夫表示如果她坚持捐献就不要再回到家里。“女子丈夫是其第一法定监护人,伦理委员会审查时他必须到场,且如果捐献,需要其同意才行。”最终,在伦理听证会前,石炳毅说服病人放弃接受活体捐肾移植。
除了对动机和直接意愿的考虑,专家们更多地还要考虑活体捐献器官手术的风险。石炳毅举例介绍,活体捐肝手术,比活体捐肾手术风险更大,存在术后出血、肝功能不全、胆漏、感染等多种可能性。国内外都曾出现过严重并发症导致供者死亡的案例。所以,伦理委员会的审查会更加严格。
器官移植的最后一道关口
现实中,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在人体器官移植活动中把握着最后一道关口。那么伦理委员会究竟是怎样一个特殊组织呢?
据石炳毅介绍,2006年以前,我国医学界还没有伦理委员会的概念。我国器官移植工作者遵守的是世界卫生组织(WHO)1991年《人体器官移植指导原则》开展人体器官移植工作。
《人体器官移植指导原则》是国际上的通法通则,其基本“原则”就是:严禁器官买卖,人体器官捐赠必须取得捐赠者本人的书面同意。
2006年3月,国家卫生部制定下发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并于2006年7月1日起施行。《暂行规定》重申了人体器官不得买卖,医疗机构用于移植的人体器官必须经捐赠者书面同意,要求开展器官移植的医院具有相应资质,确保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
《暂行规定》还规定了申请办理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必须具备的条件,其中一条是要有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要求每例人体器官移植术前均应得到医疗机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应用与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方能实施。
据了解,按照《暂行规定》的要求,伦理委员会由管理、医疗、护理、药学、法律、伦理等方面的专家组成,其中,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务人员人数不超过委员会委员总人数的1/4。
石炳毅介绍说,解放军309医院于2006年7月成立“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并于2007年7月进行了一次调整。伦理委员会由15人组成,其中器官移植医生3人,由主管医疗的副院长任伦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现在的伦理审查十分严格,需要全部委员一致同意并签名确认后,伦理委员会方可出具同意摘取活体器官的书面意见,2009年以前则相对宽松一些。”石炳毅解释说,2007年5月1日起实施的经国务院批准颁发的《条例》规定,经2/3以上委员同意,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方可出具同意摘取人体器官的书面意见。但2009年12月,卫生部发布了关于规范活体器官移植若干规定的通知,其中规定伦理委员会全体委员一致同意并签名确认后,方可出具书面意见。
“上述规定的改变,带来了一个明显变化。”石炳毅介绍说,2009年全国活体器官移植总数2720例,占全国全年器官移植总数的40.2%,2009年12月卫生部发布通知有了明文新规后,2010年,全国活体器官移植总数降为976例,占全国全年器官移植总数的17.6%。
“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更严格了,活体器官移植数量下降明显。由此可见,伦理委员会在器官移植活动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明显。”石炳毅说。
活体器官移植标准还应“往回收”
《方圆》:网上公开资料显示,以肝移植为例,截至2007年,活体肝移植的总数仅100余例。但在2009年,全年活体器官移植总数近3000例。这是否说明人们对活体器官移植接受度高了?
石炳毅:的确,人们对活体器官移植的认识更深,更愿意接受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活体器官移植成功,人们感觉到活体移植并非那么可怕。也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肝肾源等紧缺,活体移植需求大。现在大约有120万病人等待器官移植,这个数量还在以每年十几万递增,但全国每年只能做五六千例。仅以解放军309医院为例,目前有4000多个病人需要器官移植,我们每年只能做200多个,每个月新增加几十例患者,而每月得到移植的只有一二十例,肝肾源等永远满足不了。
《方圆》:您上述提到的,卫生部在2009年末发通知后,第二年的活体器官移植数量就下来了。那这几年情况又如何?国家为什么要控制活体器官移植数量?
石炳毅:这两年,在供求矛盾的影响下,活体器官移植的数量又呈现上升趋势。例如,2011年,全国活体器官移植总数1325例,占全国器官移植总数的25.2%,2012年是28%。不能说是控制,是对活体器官移植的规范更严格了。不可否认,现在有的医院在活体器官移植方面打“擦边球”。就像对于非父母子女、非夫妻关系的其他亲属关系认定上,申请者说是病人的侄子,但实际不是,或者主观意愿不是很明显,有些模糊不好界定的,伦理委员会审查的时候会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方圆》:是否可以认为,这个空间极可能存在器官买卖?
石炳毅:正规的医院的伦理审查还是很严格的,都是按照《暂行规定》和《条例》的相关规定执行。争取活体移植诊疗项目很困难,对于有资质的医院,器官移植的伦理审查是否规范,对医院的发展影响很大,如果伦理审查出问题,将对医院资质起一票否决的作用,国家卫生部和医疗服务管理司,会吊销医疗机构执照,并将其进行查处。
《方圆》:您个人对活体器官移植怎么看?
石炳毅:我们是中国最大的器官移植医院,器官移植总数是全国最多的,活体数却是最少的。从2006年我们院成立伦理委员会以来,总共通过伦理审查250例,2012年到目前只做了36例,有的医院一年就做200多例。从内心来讲,我不主张做活体器官移植,这与我个人的理念有关,比较保守。
《方圆》:亲属供肾现已被医学界和社会广泛接受,非亲属关系如家庭之间的交换捐献也可能为供体短缺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而且现在活体器官移植的成功率较尸体移植更高,为什么您持保守态度?
石炳毅:有人也曾问,有的人出于活体供肾的安全性和自身的乐于助人的精神,在没有感情关系的情况下自觉自愿捐献,可以吗。这种情况在国外已很常见,但目前国内法律不允许。不仅这种情况不允许,我认为现有的活体器官移植的标准还应“往回收”。我是医生,医学讲究无害原则,所做的是对病人有帮助,但活体移植,对供者来说,没有帮助。但为什么还要做,因为不采取这个办法,另一病人生命不能延续。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无奈之举。
《方圆》:活体器官移植的伤害到底有多大?
石炳毅:以活体供肾移植为例,其伦理学所涉及的主体是供体和受体,而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关注供者的利益。应该讲清,活体供肾切取术是对供肾者没有任何益处的手术,术后供者在外伤、感染、肿瘤侵袭时,将面临肾功能不全或变成“无肾人”的危险,而且在供肾的摘取前后也有发生各种并发症的可能性。1987年报道全世界至少有20例供体死亡。在美国活体供肾围手术期死亡率约为0.03%,最常见的死亡原因是肺栓塞。
《方圆》:未来,关于活体器官移植活动方面,您有什么期望?
石炳毅:目前,我国尚缺乏一部适合中国国情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操作规范和指南。在临床实践中,多数医院参照《阿姆斯特丹评估细则》和《英国活体供肾移植指南》的标准指导工作。希望《中国活体供肾移植指南》尽快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