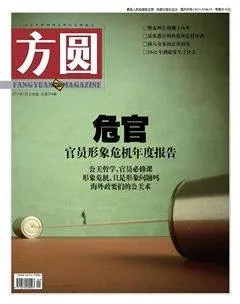公关哲学,官员必修课

【√】危机事件发生后,应该有相应部门去评价事件的处理情况,看其应对方式是否有普适价值。评价结束后,相关部门还应根据评价的情况进行改进
《我是城管》一书出版后不久,作者周亚鹰、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城管局局长就感觉到了来自外界的漫骂和质疑。中国江苏网一名时政评论员撰文评论说:“周亚鹰局长的文章,急于证明‘城管并不是这样的’,其实质就是无视自身问题的存在,只是利用自己的生花妙笔来为城管撇清责任、鸣冤叫屈,显然不是真正想‘挽回城管形象’,反倒是‘掩耳盗铃’、欲盖弥彰,让人更加反感。”
更让周亚鹰困惑的是,“我发现官员形象面临着易‘破’难‘立’的困局,一旦公众对我们失去信心,我们很难再去扭转局面。”
什么是好的官员形象
“形象危机的出现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官员自身有了诸多弊病。”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告诉记者,“性丑闻”、“露巨富”等首先是由于官员在德行方面有所欠缺造成的,虽然社会公众不能对公务员的道德水平太过苛求,但总体上还是应该高于或等于社会平均水平。在他看来,解决官员形象危机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提高公务员的自身修养,让他们尽可能多地向老百姓心中的“官员形象”靠近。
好的官员形象应该是怎样的?
“我前段时间又看了一次电影《焦裕禄》,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干部形象、官员形象。在他身上我们能明白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他身上我们能看到什么是兼济天下的情怀。然而,我们现在的官员,却很难达到这样的境界。”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告诉记者,现在许多官员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对待群众的诚恳度越来越低,滥用手中职权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因而他们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也越来越差。而官员们若想要洗牌重新来过的话,首先必须把这三个方面的“坏账”解决好。
在林喆看来,一方面官员需要严于律己,另一方面政府在选任官员时也必须以德为先,诚实的状况、爱民的情况以及责任意识的强弱都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然而,对道德的评价始终不是一个事实判断,它无法用量化的标准去衡量。
“对于公务员,我认为他们只要做到忠于职守、勤勉尽责就足够了。对于如何保持道德水平,我认为很有必要去建立相应的制度来充分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认为,官员要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广开言路、虚心接受公众批评是个不错的选择。
在他看来,“广开言路”也许会出现侵害官员名誉权的情况,但不能因此而因噎废食。也许这种方式会导致各类不和谐之声不绝于耳,有时甚至会有一些冒犯性的言论,但是这些仅仅只是副作用罢了。官员形象需要在官员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中走向完美。
不能被社会心态牵着走
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公众参与社会公共管理的热情也在极度高涨,同时他们参与社会监督、表达自己意愿的方式也在逐步增多。“网络反腐”就是其中一种。2012年11月23日,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因被爆出不雅视频而被司法部门调查,他的落马也让“公众如何参与社会监督”这一话题成为热议的焦点。
“我们看到,网络反腐这个过程中存在着许多违反法律、违反程序的情况,然而现在许多人对‘网络反腐’这种方式持宽容态度,他们认为只要能达到反腐的目的,即使手段有些瑕疵也可以包容。社会公众对贪腐现象的痛恨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对公平正义的期待,这从侧面说明了官员形象所面临的危机,它体现了社会对官员形象存在的普遍焦虑。”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兰荣杰认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社会管理的方式方法中势必会有一些不合乎法律的方式,他们的热情可以理解,但始终目的不能证明手段的合法性,参与社会监督不能以牺牲官员个人的合法权利为代价。
在这个问题上,唐钧也提出了同样的忧虑。他告诉记者,媒体和群众在揭露官员问题时存在夸大事件、造谣、传播谣言等行为,甚至涉嫌网络暴力,存在误伤的风险。这些虽与官员自身没有过多联系,但却在客观上加重了官员的形象危机,滋生了信任危机。
他认为,官员对待来自民间的声音时必须要有所选择。
“官员形象有时会受到社会心态的影响,因此政府部门不能完全被民意所牵制。”唐钧告诉记者,官员在应对形象风险时,的确需要考虑社会评价这个参数,但却不能过分依赖,以至“丧失自主性”。
“每个政府部门都有自己的职能,每个部门也都应当恪守自己的职能,不能因为想要获取一些好的社会评价就去做一些职责之外的事情,而将本末倒置。”
唐钧告诉记者,在他这些年来的研究中,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那就是:社会服务部门的形象远远好于执法部门。“这很正常,因为每个部门的职责权限都不一样,而且有些东西是人之常情。你比方说,交警开了一张罚单,既要罚款又要扣分,有几个人会在心里觉得这张罚单开得好?所以,维护形象、应对形象危机不能一味地去迎合。”
一位在某城管局任职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讲述了他的困惑:“我们现在执行任务时会特别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做。城管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和管理城市秩序,所以我们不可避免地会与小商、小贩发生冲突。然而,由于过去曾经发生过一些恶性事件,在普通老百姓心里我们的形象很负面,所以我们现在为了避免发生冲突,就在执行工作时采用‘只赶不抓’的方式,但事实上这样根本起不到威慑的作用。但我们只要一‘追逃’,就听到周围老百姓喊‘城管打人了’。”如何正确处理舆论与职权之间的关系,这让他非常苦恼。
事实上,这个问题也让司法机关头疼不已。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罗猛告诉记者,海淀检察院已经开始了对网络舆情监控机制的探索,但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
“我们现在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在做工作。一方面,对于网络上的一些言论、一些举报我们都会及时跟进,及时地与当事人接洽、沟通,给他们以正面回复而不是推诿、视而不见。另一方面,我们也正在探索建立相应的线索评价机制,因为的确有一些虚假造谣情况的存在,我们不能不加分辨地、盲目地去跟进,否则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在罗猛看来,工作还是应当掌握主动性,不能被其他的因素牵制。
政府形象不能“躲猫猫”
罗猛的说法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在采访中,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认为,应对官员形象危机的主动权掌握在官员手中,而他们在应对形象风险时需要更加积极、主动。
“其实有时候,老百姓要的只是政府的一种态度。”在兰荣杰看来,“敢于面对”是应对官员形象危机的重要手段。“有时候突发事件发生了,政府不能去躲、去推诿,不能用一种错误去掩盖另一种错误,否则会带来更大的形象危机。”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官员有这样一种姿态,不是遮遮掩掩,不是故意地隐瞒,不是故意地去压制相关信息的传播,即使之前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最后是能够得到公众的理解的。”杨建顺告诉记者,要求政府积极、主动、及时去应对危机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这样做可以减少突发事件发生后的谣言。
2009年,北京市政府应对禽流感危机的做法便可圈点。当时,市政府在报告禽流感病例后,立即启动应急机制,让公众详细了解禽流感的最新情况和应对措施。同时迅速采取措施应对禽流感,加强禽流感预防知识的宣传,加强养殖环节防疫管理和检疫监督,减少人禽接触,加强对重点地区的免疫和检测。
正是因为信息的公开透明,采取的措施及时有效,在防禽流感的过程中,谣言及负面消息较少,公众情绪较为平稳。
而2012年3月在周口兴起的“平坟复耕”工作恰恰相反。当时200多万个坟头被当地基层政府先后平掉,其间采取的对普通百姓的祖坟进行强制平毁的做法饱受争议。网络质疑声四起,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等学者以及一批豫籍媒体人纷纷提出抗议。而周口市当地政府不仅不作任何回应,反而不遗余力宣传动员平坟工作,相关“成果”报告屡见报端。这种应对无疑激起了了舆论对平坟工作的更大抵触。根据有关舆情报告,反对平坟的博客在半年时间里达到了3万多篇,微博达到了70万余条。舆论无可收拾之余,周口市也于11月终于暂停平坟,并承认平坟“是有点快了”。
唐钧把形象危机产生的根源分为三类:形象偏差度、形象解释度和形象落差度。
偏差度,即看官员形象的问题是否来自于部门职能设定和社会心态的偏差和误解;落差度,即看官员形象的问题与公众的预期差距多大;解释度,即看官员对于危机事件的责任、处理经过和结果的解释能否获得公众理解。
事实上,形象落差度和形象解释度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形象落差度的形成直接来自于主体对形象危机的消极回应,形象解释度的形成则来源于主体的回应,兰荣杰、杨建顺所说的这种危机应对方法其实就是在“减少形象落差度,提高形象解释度”。
唐钧告诉记者,近几年来许多政府官员都已经意识到了“形象解释度”mky6hhp6161jNwoTiVz7OVKWYKKIeHCCNLApvvOymaQ=的重要性,事故发生后鲜有“不说话、不作为”的情况,但其在解释方面的工作仍然有所欠缺。
“一方面,解释项的发布时间多为危机事件爆发后,缺乏持续的发布规划;另一方面,解释项发布的内容多针对具体事件中的问题,呈现碎片化的特点,因而有时会显得‘难以自圆其说’。”唐钧认为,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官员需要针对形象危机的具体问题主动部署、积极推进。既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也要多方沟通,听取群众意见,针对群众需求不断改进政府工作,消除误解和质疑。
由“因”去及“果”
“我们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生活也都富裕了,按理说,我们的官员形象应该不会有危机,但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在杨建顺看来,官员形象危机的出现不是偶然现象,它说明官员平时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常规工作没有做好,也没有做到位。
“政府要应对形象危机,同样也应该从自身着手。既然是日常工作没有做到位,那么就需要从这个问题去着手,建立相应的机制。”杨建顺告诉记者,“官员”是“形象危机”这个结果的因,只有把“因”的问题解决好了,才能把“果”正了。
那么,“因”的问题在哪里?
杨建顺把“因”分为“不作为”和“不知悉”两类。“不作为”主要指某些官员没有很好地履行法定的义务,承担法定的职责,所以公众对其不满意,贪污腐败即是典型例子;而“不知悉”则由公众对信息了解得不充分、对官员产生误解而导致,事实上这就是唐钧所谓的“形象偏差”。
“不论是解决‘不作为’还是‘不知悉’,核心都在于建构起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公开机制,让官员的工作真正在老百姓的监督之下进行。”杨建顺认为,许多贪腐、渎职行为频发的原因主要在于监管体制没有在阳光下运转起来,因而许多行为人怀有侥幸心理,铤而走险。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目前信息公开体制的不健全,政府的一些具体工作并不为公众所知晓,而公众对政府形象的理解又与他们的知悉程度息息相关,危机便由此而来。
“要求信息公开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即在于纠正形象偏差度,这种偏差是由于公众对相关政府部门的不了解、有误解而引起。一般而言,产生形象偏差的原因有这样几个:一是多元管理主体造成的职能分割不清;二是法规不健全造成的职能定位不明;三是权责不对称造成的履职尽责不力;四是受社会心态影响的管理服务职能错位。”唐钧说。
在这一点上,周亚鹰深有体会。“同样是执法人员,警察抓罪犯就会得到民众的欢呼,而我们‘清理’小商贩就会被许多人诟病。许多人都认为,为了生计而在街边摆个小摊情有可原,我们的执法行为太过不近人情。事实上,这种行为违反城市管理规定,如若不治理、任其发展,最后对大家都不好,但许多人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在唐钧看来,要纠正形象偏差,政府机构改革还应“深入人心”,使群众对具体部门的职能配置有基本的了解。对于社会对职能定位存在误解的,还需要政府主动推进社会预期的调整和修正。
“针对官员形象危机而言,我们还需要建立综合评价机制,这个机制包括两个方面,形象危机的改良机制和改革机制。”杨建顺认为,危机事件发生后,应该有相应的部门去评价该事件的处理情况,看其应对方式是否对其他类似事件有普适价值。同时,评价结束后,相关部门还应根据评价的情况进行改进,根据评价数据对现象机制进行修正,让工作转入正轨。
“唯有这样,官员形象、政府形象才能不断地走向正效应,相关工作才能不断地产生正能量。”杨建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