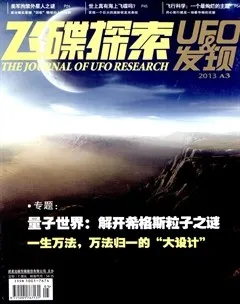活生生的量子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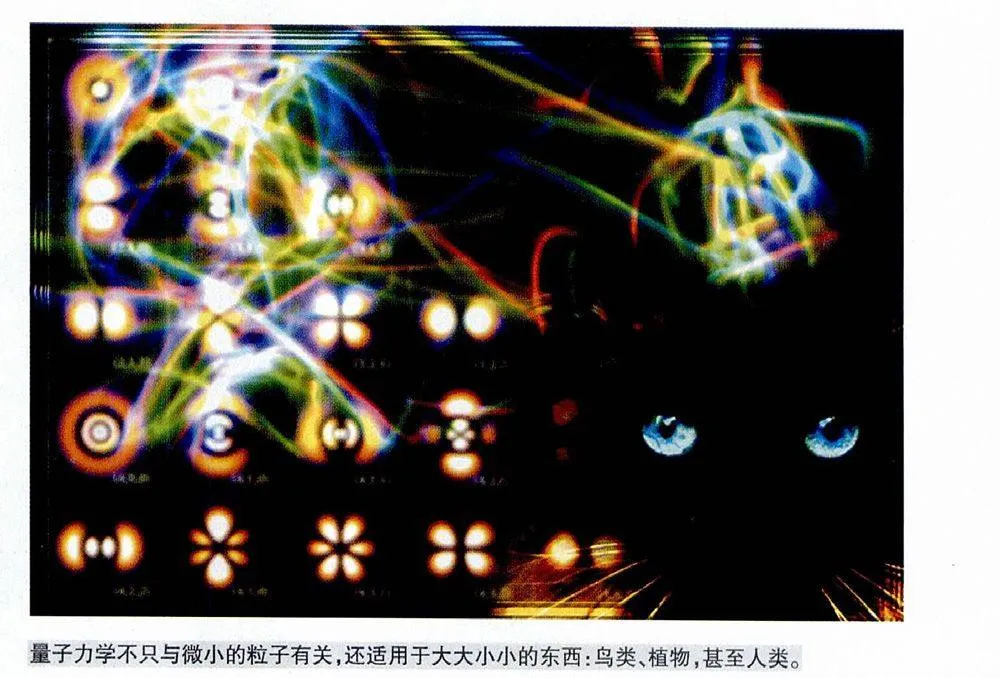
根据标准的物理教科书,量子力学是微观世界的理论,用来描述粒子、原子和分子;而描述宏观尺度的梨子、人和植物时,就得改用一般的古典物理。
分子与梨子间有个边界,在那儿量子力学的奇特行为消失,出现我们熟悉的古典物理行为。量子力学只适用于微小世界的这种印象,普遍存在于人们的科学知识里。例如,在畅销名著《优雅的宇宙》的第一页,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学家布赖恩·格林提到,量子力学“提供一个理论架构,让我们理解最小尺度下的宇宙”。古典物理(涵盖量子以外的所有理论,包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负责最大尺度的世界。
然而,对世界做这种方便的切割,其实是种迷思。很少有现代物理学家会认为古典物理和量子力学具有同等的地位,古典物理应该只是具有量子本质的世界(不论大小)的一种有用近似。虽然在宏观世界可能比较难看到量子效应,但原因基本上跟大小无关,而是跟量子系统彼此作用的方式有关。
一直到十几年前,实验学者仍未证实量子行为可以出现在大尺度系统,如今这已是家常便饭。这些效应比任何人所想的都还要普遍,甚至可能出现在我们身体的细胞里。
即使是我们这些靠研究这类效应吃饭的人,也还没完全理解它所教给我们的、关于自然运作的方式。量子行为很难可视化,也不容易以常识理解。它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观察这宇宙的方式,并接受一个新颖又陌生的世界图像。
缠结难解的故事
对量子物理学家而言,古典物理是全彩世界的一个黑白影像,无法完整呈现这个丰富的世界。在旧教科书的观点里,当尺度一变大,色调就不再丰富。个别粒子具量子性质,一堆粒子则变为古典。
然而,关于尺寸并非决定性因素的第一个线索,可以追溯到物理学历史上最有名的思想实验之一:薛定谔的猫。
1935年,薛定谔想出一个病态的情节来说明微观与宏观世界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无法画出界线。量子力学说,放射性原子可以同时处于衰变及未衰变的状态;若将原子与一瓶可以杀死猫的毒药扯上关系,使得原子衰变会导致猫死亡,则猫会如同原子般处于模棱两可的量子态。怪异性质由一个感染到另一个,大小在此并不重要,问题是为何猫的主人都只会看到他们的宠物非死即活?
以现代的观点,世界看起来像古典的,是因为物体与环境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将量子效应掩藏了起来。例如,猫的生死信息通过光子和热交换,迅速渗漏到环境里。量子现象会牵涉到不同古典状态的组合(例如同时死与活),而这种组合会很快散逸掉。这种信息的渗漏便是“去同调”过程的基础。
大的东西比小的容易去同调,这就是为什么物理学家通常可以只把量子力学当成微观世界的理论。但在许多例子里,这种信息渗漏可被减缓或停止,如此一来,量子世界就会全然显露。
缠结是典型的量子现象,是薛定谔于1935年在那篇将他的猫介绍给全世界的论文里发明的名词。缠结将几个独立粒子捆绑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个古典系统总是可被分割的,至少原则上是如此;由个别组件集合而得的性质,在个别组件里也会有。但是缠结的系统无法如此分割,并且会导致奇怪的结果:缠结的粒子即使互相远离,仍会表现为单一整体,这就是爱因斯坦所称的、著名的“幽灵般的超距作用”。
物理学家通常讲的是电子等基本粒子的缠结。这些粒子可粗略想象为旋转的小陀螺,以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旋转,转轴指向任意给定的方向:水平、垂直、45°角等。测量其自旋时,必须选定一个方向,观测粒子是否沿着那个方向转动。
为了方便说明,假设粒子表现的是古典行为。你可以让一个粒子沿水平轴顺时针方向旋转,另一个沿水平轴逆时针方向旋转;如此一来,二者的总自旋为零。它们的转动轴在空间中是固定的,测量结果取决于你选的方向是否沿着粒子的转动轴。如果对二者都做水平轴的测量,则会看到两个粒子的转动方向相反;如果都做垂直轴的测量,则完全不会侦测到这两个粒子的转动。
然而,如果是具有量子性质的电子,则情况会惊人的不同。你可以让粒子的总自旋为零,即使你没有给定个别粒子的转动方向。测量其中一个粒子时,你会看到它随机以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转动,就好像粒子是自己决定要朝哪个方向转。而且,不管你选择测量哪个方向,只要对这两个粒子测量同一方向,则测得的转动方向永远相反,一个顺时针,一个逆时针。它们怎么知道要这样做?这仍然是个极其神秘的性质。不仅如此,如果你对一个粒子做水平轴测量,对另一个做垂直轴测量,则仍可测量到部分自旋,这就好像粒子没有固定的转动轴。因此,测量结果是古典物理无法解释的。
谁在帮助原子排列?
大部分的缠结实验都只用到几个粒子,因为一大群粒子不容易隔绝环境的影响,其中的粒子很容易跟无关的粒子缠结,破坏原始的内在联结。以去同调的说法,就是有太多信息渗漏到环境里,造成系统有古典的行为。对我们这些寻找缠结的实际用途(例如量子计算机)的研究人员来说,保持缠结是一项重要的挑战。
2003年,有一个巧妙的实验证实,如果能够减少渗漏或加以抵消,则大的系统也可以保持缠结。
英国伦敦大学的加布里埃尔·阿普尔等人将一块氟化锂盐放在外加的磁场里,盐里的原子就像旋转的小磁棒,会尽量与外加磁场同向,这种反应表现为磁化率。原子间的作用力就像同侪压力般,会让它们更快排列整齐。研究人员改变磁场强度,然后测量原子排得多快。他们发现,原子的反应速度比彼此作用力的强度所能提供的还快。很显然,在这个实验中有额外的效应帮助原子排列整齐,而研究人员认为这是缠结造成的。若真如此,则盐块里的1020个原子形成了巨大的缠结态。
为了避免热能所造成的无序运动,阿普尔的团队是在极低的温度下做实验(仅千分之几K)。不过,在那之后,巴西物理研究中心的亚历山大·马丁斯·德·苏萨等人以室温或更高的温度,在铜羧酸盐之类的材料里发现了宏观缠结,自旋粒子间的交互作用强到可以抗拒热能所造成的无序。在其他例子里,则必须用外力抵挡热效应。物理学家在越来越大、越来越高温的系统里看到缠结:从以电磁场捕获的离子到晶格里的超冷原子,再到超导量子位。
这些系统就像薛定谔的猫。考虑一个原子或离子,其电子可能靠近或远离原子核(或是既靠近又远离)。这种电子就像薛定谔思想实验里可能衰变、也可能没衰变的原子。不管电子在哪儿,这整个原子是可以向左或向右移动的,运动方向是左或右就像猫是死的或活的。物理学家以激光操控原子;可以将这两种性质扯上关系。如果电子靠近原子核,就让原子向左移动;如果电子远离原子核,就让原子向右移动。如此一来,电子的状态就跟原子的移动缠结起来,如同原子衰变跟猫的状态缠结起来一样,同时既向左又向右移动的原子,可以模拟既死又活的猫。
许多其他的实验也扩展这种基本概念,使大量的原子也可以缠结,从而进入古典物理不可能说明的状态。如果大体积且高温的固体可以缠结,我们只要稍用想象力就可以问:又大又暖和的特殊系统——生命,也是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