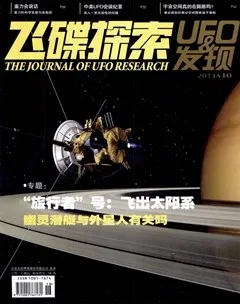先天还是后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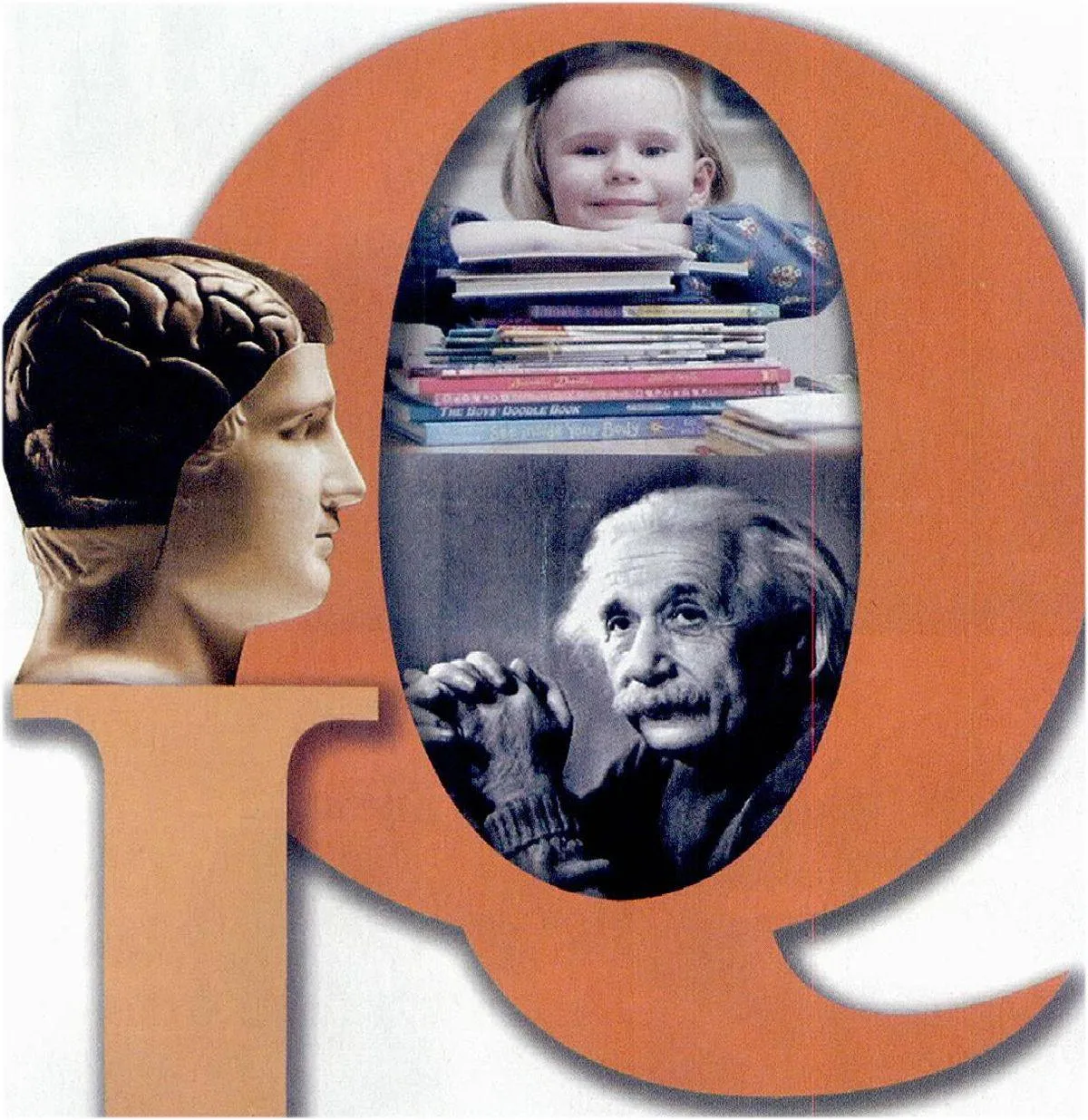
我们现在的模样和性格是先天就设定好的,还是后天教养所形成的?“研究发现政治立场与基因有关”,这种故事媒体最爱了。大大的头条写着“左翼自由主义者是天生而非后天养成”,报道中引用美国科学家的研究,指出具有某些基因的人比较容易抱持自由派的政治立场。
表面看来,指出发现不过是为“先天与后天”的辩论(我们的特性究竟是基因决定还是后来养成)增添一笔罢了。过去几年来,这类报道不胜枚举,它们通常宣称基因是决定一个人是否有冒险、无神论,甚至精神异常等许多行为的关键。这些报道背后隐含的信息令人无力:正如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眼睛颜色一样,DNA也决定了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
武断取巧的媒体
但是“自由派基因”这个故事背后的真相有点不太一样。近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打破了原本先天/后天的二分法,这项研究也是其中之一。它提出一个更微妙的新观点,认为人类特性多半是先天与后天综合的产物。
领导这项研究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医学院教授詹姆士·福勒解释道,他们发现只有在社交生活活跃的人身上,才能看得到基因DRD4和自由派立场之间的关联。福勒希望能把这点说清楚:“一个人必须遗传到这个基因,并且在青春期时拥有众多朋友,先天和后天这两项因素交互作用,才会显现自由派的倾向。”
但是这样做还是不管用。许多媒体直接把这项研究贴上“先天派”的标签,然后就置之不理,等着下一个“天生就如此”的故事。这项争论引起的反应不但惊人,还令人不安。因为这种“把基因摆在第一位”的信念,曾导致20世纪30年代美国强行禁止“低能者”生育,以及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半岛的种族净化暴行。
另一方面,反对基因决定论的论述也走向极端。这一派人士相信,人们生来是“一块白板”,生命未来的发展只靠成长环境来决定,这衍生出许多奇怪的儿童教养理论,还让父母对于自己子女的不成材感到内疚不已。
“生而平等”对上“优生筛选”,讽刺的是,争论先天与后天的先驱们都认为他们的观点是在为这个社会追求最佳福祉。
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在1690年出版的名著《人类悟性论》一书中,阐述了“天生是白板”的人类行为观点,他自认给了“原罪与君权神授”这类观念一记重击。他主张,如果人人生而平等,那么每个人都能够(并且应该)享有相同的生存、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就深受这个观念的影响。同样,当维多利亚时期的知识分子赫伯特·斯宾塞和弗朗西斯·高尔顿将达尔文的演化论和人类社会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时,他们自认这么做能够增进大众的福祉。
不过,即使基因在达尔文时代尚未被证实,他的遗传观点就已经比许多他的追随者所倡导的还要复杂。事实上,他认为某些本能是用来“学会某项技艺”,比如人类的说话能力可能就是一例。
斯宾塞针对演化论下了著名的结语“适者生存”,高尔顿则提倡通过选择性繁殖(即“人择”)将人种系统化“改良”的优生概念,一些同时期的人都看出这些论述潜藏的危险。即便如此,许多知识分子仍将这些疑虑扔到一旁,认为事实不辩自明。
早在1865年,高尔顿就发表了一篇有关名人家庭杰出儿童的研究,推论出这些儿童的成功概率是一般家庭子女的240倍。10年后,高尔顿延续先前的研究,率先比较同卵双胞胎的发展,此后这种方式就成为先天与后天之争的主要研究方法。由于在同卵双胞胎的人生中发现许多相似之处,高尔顿便认定先天的力量显然凌驾于后天之上,因此选择性繁殖才是促进社会进步的良方。
许多参加了1912年伦敦“第一届国际优生学研讨会”的人也都认同这一看法,其中包括达尔文的儿子,里欧纳德·达尔文。时任优生学学会主席的里欧纳德警告说,如果让人类中的“不适者”继续繁衍,将会对我们的后代子孙造成威胁。不过,这场会议中也不乏反对声浪,前任英国首相阿瑟·贝尔福就在该会议的演说中表示担忧,认为整个遗传性的议题远比科学家所想的还要复杂,并警告狂热分子会挟着优生学的名义偷偷散布自己的意识形态。
行为学先驱的怪异实验
为了探寻环境在人类行为上扮演何种角色,早期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些很不寻常的实验。1931年,美国心理学家温思罗普·凯洛格和他的太太决定研究父母教养方法如何影响幼儿发展,于是他们让自己10个月大的儿子唐诺和一只黑猩猩宝宝一起接受教养。他们发现在很多测验中,黑猩猩宝宝的能力和他们的儿子不相上下(意味着这些能力受到环境的影响),但是黑猩猩没学会讲话。当他们的儿子开始发出黑猩猩般的叫声时,凯洛格才放弃这项实验。
最具争议性的实验或许是美国心理学家华生对一个被称为“小艾伯特”的8个月大婴儿所进行的实验了。华生将小艾伯特原本不害怕的东西与巨大的恼人声响联结,证明这样能够诱发不合常理的恐惧。经过数个月的实验,小艾伯特对兔子和狗产生强烈恐惧。
教养方针走火入魔
在美国,优生学观念的传播速度有如野火燎原。在里欧纳德发表演说后1年,美国许多州就立法允许强制禁止“低能者”生育。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在短短数个月内便推行优生政策。他们起初是强行禁止数千名有精神分裂情况的人生育,最后演变成像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那样的百万人大屠杀。
随着纳粹于1945年战败,以及后来人们对其政策的强烈憎恶,使得先天与后天之争很快再度倒向“天生是白板”的人类行为观点。这派拥护者再次以看似可靠的科学研究来为他们的观点护航,他们的结论也再次漠视了实际状况的复杂性。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约翰·华生表示,所有探究人类特质与本能之间关联的说法都无法量化,所以毫无意义可言。他主张应该着眼于人们如何响应周遭的世界,并且认为这样就能证明所有人类都有能力完成任何事。
华生和他的助手搜集了许多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其中有些显然偏离常轨。更奇怪的是,尽管这些行为主义者的研究显示出后天教养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试着排除例如遗传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且竟然无视于这些研究缺陷就全盘接受。
20世纪50年代晚期,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进行了颇具争议的实验,通过图像清楚呈现出这些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心理学家哈利·哈洛把小猴子和它们的母亲分开,并将它们放入有两个人造假妈妈的笼子里。其中一个假妈妈只是个装上奶瓶与牛奶的铁丝框架模型;另一个则比较像猴妈妈,可以让小猴子抱抱,但是无法提供乳汁。根据行为主义者的理论,这些小猴子应该很快就学会忽略铁丝妈妈的冷酷并把吸奶视为第一要务。然而实验发现,这些小猴子大半时间都在温暖但没有奶喝的妈妈身边,只有肚子饿的时候才暂时跑去铁丝妈妈那里。
哈洛证明了大部分人(除了行为主义者之外)视为理所当然的看法:行为不只是由环境所塑造。这些猴子出自本能,渴望获得母亲身上的温暖抚慰,还会主动找出这样的特征。
哈洛发现的证据支持某些行为特质是天生而来的时候,先天与后天之争的双方论证都正深刻影响着父母和子女。行为主义者所写的育儿手册坚称,若是太常亲吻或拥抱小孩,小孩就会变得软弱。同时,支持遗传作用的证据也正左右着教育方式。先天派认为同卵双胞胎的研究证实了智力主要是遗传而来,因此有人主张教育资源应集中在早期显现聪明倾向的儿童身上。
伯特的丑闻
先天与后天之争曾经引发许多激烈的争议,其中最甚者莫过于当时著名的英国教育心理学家西里尔·伯特爵士所引发的风暴。
20世纪40年代,伯特提出证据认为智能几乎全由基因决定,环境(尤其是教育)只扮演了次要角色。这项证据来自伯特进行的同卵双胞胎研究。他让一些同卵双胞胎分别处于不同的成长环境,结果显示即使教养方式截然不同,双胞胎的智商仍不相上下。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伯特获得更多数据支持他的主张,这样的看法也促成了英国的教育制度,特别是英国实行的“11+考试”,目的是找出哪些儿童可能拥有高智商基因,好让教育资源能够集中在这些儿童身上。
然而,后来伯特的证据开始出现问题。他声称追踪了53对适合研究的双胞胎,而研究结果的一致性却高得出奇。到了1976年,也就是伯特死后5年,《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项调查显示伯特的研究涉嫌造假,不久伯特的传记作者也出面证实这一说法。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只是伯特的疏忽而非造假,也有人坚信伯特认为智商可以遗传的基本主张是正确的。然而对大部分科学家来说,伯特的丑闻俨然在警示我们,这场先天与后天的争论可能发挥多大的影响力。
几年之后,双胞胎研究开始受人质疑,不过此时“基因就是天命”的主张已经失去了大半影响力(至少在学术圈以外如此)。父母们早就发现不管他们多么努力,子女们的个性通常还是有极大的差异,这表示个性并非全然由先天或后天所决定。
然而在学术界,这项争议仍然沸沸扬扬。1975年,哈佛大学的蚁类专家爱德华·威尔森出版了《社会生物学》,并在书中提到单靠基因就能产生非常复杂的行为。他也试图把他的论点延伸到人类行为上,而这掀起了激烈的争辩。主要原因在于,这样的观点似乎想让基因决定论死灰复燃,带有优生学的弦外之音。而这个时候,科学家也不断提出证据,显示从性倾向到职业选择,基因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界似乎终于取得和大众一样的结论,那就是人类行为是先天、后天与机运综合而成的结果。
1998年,美国心理学家茱蒂·哈里斯出版《教养的迷思》,这本畅销书为父母们长久以来的怀疑提供了科学支持:父母的教养技巧对子女发展的影响其实相对不大。此时,遗传研究也找到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基因和环境如何相互影响,这也使先天/后天之间的标准二分法显得相当可笑。
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重点不只是有没有某个相关的基因,还包括这个基因如何表现,而这可是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科学家发现草原田鼠的一夫一妻制和某种基因“开关”有关,启动这个开关会使它们的大脑对于血管加压素变得敏感。似乎就是因为这个基因的表现,使它们迷上释放的血管加压素,所以才和性伴侣长相厮守。
基因的表现方式也会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老鼠实验中发现,比起被母亲忽视的幼鼠,从母亲身上获得许多关注的幼鼠的荷尔蒙浓度,比较不会受到压力的影响。换言之,相同的荷尔蒙相关基因,它的表现会因养育方式的不同而改变。
该研究团队接着通过生化方式改变那个基因的表现,成功地让原本安适的老鼠变得紧张,也让原本神经质的老鼠变得泰然自若。这不禁让人期待不良教养对子女造成的影响在子女长大后也有办法消除。
“同性恋基因”是否存在?
1993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中心的狄恩·汉默发表了一项震惊全球的证据,显示在同性恋兄弟的研究中,发现某些基因和同性恋有关。大约3/4的同性恋兄弟在性染色体上有某组相同的DNA序列,代表他们基因体中的这些区段内至少有一个同性恋基因。其他研究人员则发现,同卵双胞胎都是男同性恋的机会比异卵双胞胎高出许多,这个结果也符合同性恋基因的概念。
然而在1999年,由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研究者进行的史上最大规模的双胞胎基因研究,却无法重现汉默当初发表的结果,这使得人们开始怀疑汉默的主张。无论如何,汉默强调即使这样的基因确实存在,它也不会决定性向,因为正如双胞胎研究所揭露的,非遗传的因素也很重要。
应验达尔文的预测
科学家发现,人类的许多特质也有这种所谓的“外遗传联结”,包含忧郁、精神分裂和政治倾向,甚至性倾向。如今,科学家已经找到证据支持达尔文对口说能力所提出的看法。研究人员发现,一个名为FOXP2的基因和语言学习能力有关。但只有这个基因是不够的,它必须是正确的变异体,还得以正确的方式表现。
先天与后天之争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但是到最后我们可能只会得到这样的真相:这不过是个错误的二分法罢了。我们从这个辩论中得到的最大收获或许是:我们明确意识到了,若科学争议中的任一方垄断信息后,将会酿成多大的灾难。(盛文娟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