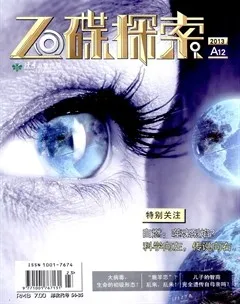“鹿羊恋”?乱来,乱来!



要说最近国内动物界最热门的八卦,莫过于云南野生动物园的绵羊长毛和梅花鹿纯子的不伦恋了。一头从小生活在鹿群里的公绵羊,居然赢得了雌鹿的芳心,平日里卿卿我我也就罢了,居然真刀真枪地操练起来了。
这种咸湿劲爆的消息历来最满足成为一个热门八卦的充分条件。其实,以我儿童时期的农村生活经验来看,这类超越物种的“恋情”并不罕见。谁家的公鸭骑了谁家的母鸡,还把人家母鸡给啄死了(鸭子的交配远比鸡的激烈,公鸭会死死啄住母鸭的颈部,而鸡的脖子没有鸭子的那么强悍);或者谁家发情的母马没拴好,让别村的驴给占了便宜。这些事儿都会在茶余饭后不断被人提起。
乱来的动物们
如果从动物行为学的角度入手,不难发现这些乱来行为的始作俑者往往都是雄性动物,特别是那些一夫多妻或者多夫多妻制的雄性动物。对它们来说,反正有的是储备,而且中奖了也不用自己负责,有枣没枣打一竿子再说。这些雄性动物不太挑剔,很多东西都会挑起它们的“性趣”。比如,一只公绿头鸭对一具同性同类的尸体“性”趣盎然,一些雄甲虫只因为啤酒瓶跟雌甲虫的颜色质感比较相近就纠缠不休。
另一些动物则似乎对性事发展出除了传宗接代之外的功能,比如玩乐。此中高手是各种鲸类,这些普遍被认为智力发达的动物与人类一样热衷于乱来。比如有记录说瓶鼻海豚把性器官插进海龟龟壳缝隙的软肉里,或者用其末cNJUR0w98fa5U1kR+Ahg6w==端的钩状物挑起一条滑溜溜的鳗鱼。跟已经寻不到踪迹的白鳍豚长得很像的亚马孙河豚更会玩,早在1985年,就有科学家发现雄亚马孙河豚有种特别的爱好,那就是把自己的性器官插进同伴头顶的喷水孔(也就是鼻孔)里。有时候人类也会成为这些永远面带微笑的家伙的调戏对象。一项关于南半球与野生鲸类伴游观光活动的调查,记录了至少13起海豚试图将与之伴游的人类当成泄欲工具的报道。
其实你大可不必去海里找这种体验,那些家里养着公狗的朋友想必都经历过自家的宠物抱着客人的腿做猥琐之事的尴尬。
与这些花花大少比起来,有些乱来的家伙实在是很严肃的,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鸟类。稍微熟悉动物学的朋友可能都听说过动物行为学的开山祖师之一康拉德·洛伦兹曾经做过的一个实验,他亲自孵化了一批灰雁的蛋,从小雁破壳的那一刻开始便与之形影不离。结果这些小雁后来就紧紧跟随洛伦兹的靴子,就像跟着自己的父母一样。这种现象叫作“印记”,在所有动物里,鸟类的印记行为最为明显,也被研究得最为透彻。
有趣的是,印记不但会让鸟认贼作父,还直接影响了它们的择偶标准。比如小雪雁有两种色型———白色和蓝色。1972年,鸟类学家库克发现,在野外,小雪雁总是倾向于寻找与自己相同色型的伴侣,而如果让它们从小被相反色型的养父母收养,它长大后就会倾向于寻找与自己相反色型的伴侣。如果让它们从小被一白一蓝的混合家庭收养,它的口味就不再偏向任何一个色型。类似的结论在鸽子、鸡和斑胸草雀(也就是珍珠鸟)身上都得到了验证。科学家甚至成功地让斑胸草雀“爱”上了人类的手指,对其大献殷勤。
此类事件大部分都能用以下几点来解释———它们大多生活在圈养条件下,从小跟其他动物生活在一起,“人生观”出现了很大问题。等它们长大了,被限制了自由的春情又无处释放,于是就悲剧了。
不伦恋为何悲情?
按理说,不伦恋说起来应该是,也的确是悲剧的,然而上面这些事儿怎么看怎么充满喜感,但接下来说的这个就绝对悲情。1993年,科学家在危地马拉附近的大西洋3000多米深的深海中看到了两只正在缠绵的章鱼,奇怪的是,这两条章鱼根本不是一个种类,更诡异的是,它们都是雄性。性对于章鱼的意义除了繁衍还有死亡。因为它们一生只会交配一次,然后雌雄双方都会在小章鱼孵化前后死去。既然一生只为这一次,这类动物理应严肃起来才是,可为何这两只还要乱来一气呢?研究人员对此的解释是,在深海,这些独行的家伙可能很难遇到配偶甚至同类,当性成熟来临,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它们会抓住一切机会拼死一搏———真是太悲惨了。
很久以来,主流科学家一直认为,跨物种杂交这种事,在动物界(之所以强调动物界,是因为在植物界杂交现象非常普遍)即便偶有发生,也绝对是非主流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没有结果,或者只是个坏结果。所谓没结果就是两种动物亲缘关系相隔太远,根本无法产生后代,比如长毛和纯子虽然都是偶蹄目的动物,可一个是牛科,一个是鹿科,它们的祖先分家至少已经2000多万年了,实在是八竿子打不着。而所谓的坏结果是,两种动物的祖先分家时间不算久,结合能产生后代,但是基本上不可能有杂二代,因为由于染色体错配等原因,杂一代有生育能力的可能性极小,比如马和驴的后代骡子。
不过,现实中还真的有例外。
1985年5月15日,夏威夷的海洋世界公园里,雌性瓶鼻海豚帕娜荷丽生下了一个雌性幼崽,这个小“姑娘”的父亲,却是与帕娜荷丽共享一个水池的一头名叫Tanui Hahai的雄性伪虎鲸。伪虎鲸虽然比瓶鼻海豚大三四倍,而且叫“鲸”,但它跟宽吻海豚一样属于鲸目海豚科,所以亲缘关系并不远。这只“鲸豚兽”被取名为Kekai malu。
Kekai malu在很小的时候就生过一个幼崽,但是早夭了,1991年又生下一个雌性幼崽,在9岁的时候死去。2004年12月23日,她生下第三个孩子Kawili Kai,它的父亲是一头宽吻海豚。如果你去夏威夷旅行,可以去拜访一下它俩,这是已知仅存的两头“鲸豚兽”。2011年7月,在沈阳的一家海洋馆里也曾产下过一头“鲸豚兽”,出生后不久便夭折了。
新“物种”是如何诞生的?
这些异种杂交并产下可育后代的例子着实挑战了经典的物种定义。物种是生物分类里面最基本的单位,我们说一只鸟科动物是鸡而不是鸭子,就是通过形态进行定种。这看上去好像并不难,但在生物界,怎样定义一个物种一直是一件很让人挠头的事,因为有数不清的生物,而我们熟悉的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
在动物界,最常用也最有效的定义方式是生殖隔离。
生殖隔离是20世纪最伟大的进化生物学家之一恩斯特·迈尔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到60年代正式完善。简而言之,那些在自然条件下无法交配,或者交配后无法产下后代,或者后代不育的两群动物,就可以视作两个物种。当然,这个概念存在很多疏漏,比如大量并非两性生殖的动物被无视了,而且我们也不太可能将任意两个动物杂交一下以验证其是否有生殖隔离。尽管如此,生殖隔离仍然很有意义,因为它昭示了物种的内涵,那就是相对独立的一套基因组。
传统的进化生物学家认为,野生条件下的种间杂交十分罕见,除了后代很难生育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杂种”们将面临父母两个物种的竞争。即便它们侥幸杀出一条生路,活到了性成熟的年纪,可满眼的异性大部分还是爷爷家或者姥姥家的人,会重新掉进祖先物种基因组的汪洋大海中。所以,由一个物种由于后代产生变异,逐渐分化成两群,或者由于地理阻隔分成独立演化的群体才是新物种出现的方式。
种间杂交,1+1=3?
随着新的野外和实验室研究,一些不寻常的例子逐渐被人们发现。2006年,美国史密森尼热带研究所的耶稣·马瓦雷兹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个小组在位于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交界处的山区中发现了一种杂交蝴蝶Heliconius heurippa,这种蝴蝶翅膀上的红色和黄色分别遗传自另外两种蝴蝶。新蝴蝶在选择配偶时十分挑剔,只跟同时拥有红黄色斑翅膀的“同类”交配,对或红或黄的亲戚蝴蝶不感兴趣。同时,新蝴蝶的栖息地海拔比父母种蝴蝶都高,幼虫钟爱的食物也与父母不同。这就既保证了新的杂交基因组的“纯净”,又避免了同室操戈的情况发生。
于是,这又成了新物种诞生的另一方式,也就是1+1=3。马瓦雷兹以及其他科学家的发现鼓舞了很多“不走寻常路”的进化生物学家,比如英国伦敦大学的生物学家詹姆斯·马莱特。在他看来,至少有10%的动物物种是由种间杂交产生的。
虽然科学界对10%这个数量还有诸多争论,但是种间杂交产生新物种这一理论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毕竟在大部分时候,演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造成种群隔离的地理隔离并非总是不可逾越的。
比如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证实北极熊是由棕熊演化而来的,两者大约在15万年前分道扬镳。而牙齿化石证据则显示,北极熊在2万年至10万年前才从棕熊的杂食变成几乎单一的肉食。不管是15万年还是2万年,其实都只是生物演化史上的一瞬,只是由于第四纪冰期的来临,两群动物才被分开,然后独自演化至今,并从外形到行为上产生了巨大的不同。然而,由于全球气候变暖等因素,原本生活在北极圈以南的棕熊分布范围越来越北,并逐渐跟自己“失散多年”的亲人北极熊亲密接触。结果就是近几年“棕白熊”不断被人发现———地理隔离被打破了,是否会出现新种的熊,或者失散多年的棕熊和北极熊会否破镜重圆,这都值得期待。
实际上,更有科学家大胆推测,我们每个人都是种间杂交的产物———我们的祖先跟现代黑猩猩的祖先曾经有过一腿。来自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在对照人类与黑猩猩的基因组时发现,虽然大约60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和现代黑猩猩的祖先已经分家了,但是人类和现代黑猩猩X染色体上的很多基因只有大约400万年的差距。如何解释这近200万年的差距?研究人员推测,在两个物种已经分离200万年之后,我们的祖先和黑猩猩的祖先又短暂地重归于好过。你可别怪我们的祖先口味太重,因为400万年前的人类和400万年前的黑猩猩看上去并不像现代人类和现代黑猩猩那样差异巨大。
即便种间杂交在自然界并非那么禁忌,不过,回头来看云南野生动物园长毛和纯子的结合,它们终究不会有“幸福的果实”。至于在情人节为“鹿羊恋”举行婚礼,把它俩拧在一起当成浪漫的典范,唉,真是有点不足为外人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