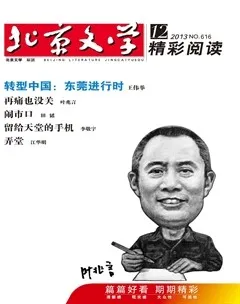绵延的山脉
转眼间,我到贵阳已十年有余。杜牧诗云,十年一觉扬州梦。十年一梦,百年又未尝不是一梦。我之所以来到贵阳,缘于一个人,而这个人却在不久前离开了,离开了他曾经生活的这座名叫贵阳的城市,这个称作人间的世界。
这个人就是我始终称之为老师的王鸿儒先生。
一次偶然,我看到一份关于家乡福泉的知识竞赛题,题目有关家乡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方方面面。譬如一道题问的是福泉最高的楼是什么楼,有多少层?紧接着一道,福泉籍历史小说作家王鸿儒的主要作品是什么?等等。对于自幼执迷于文学的我来说,不觉眼前一亮,家乡还出了一个作家?当时觉得作家是一个遥远的概念,只存在于书本上,怎么会与我家乡小城联系上呢?那时我正在重庆读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手机、网络远未流行,传统的书信还是一种主要的联络交流方式。当时除了读书做作业,总有大把的时间是闲置的,因此,写信成了学生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那时,我给王鸿儒先生写了一封信,写这封信正如我给众多文学杂志编辑的投稿信一样,一方面是满腔热忱,一方面也知道可能泥牛入海,有去无回。可想不到的是,先生竟给我回信了,信写得谦逊、热忱,且多鼓励。从此,我开始了与先生的交往。
放暑假后,我便按着先生写给我的地址前去拜访。其时,我脚蹬一双崭新的皮鞋,脸上带着崭新的伤痕——一次意外,在校园里和我一起行走的女生被一群酒鬼调戏,我为了尊严,一人独斗群氓,遍体鳞伤——诚如我母亲所言,好打的牯牛没有一张好皮。后来校方给予了我一笔“见义勇为”奖金,我便用这钱买了平生最昂贵的一双皮鞋。乘了一夜的火车,到了贵阳,正是清晨,重庆的燠热一下抛诸脑后,好像从炼狱脱身出来。迎面而来的是如水的阳光,天青云白,清新的天气和景物。我搭乘中巴前往花溪,在车上,见着一个美貌娴静的女子,我不由多看了她几X17HM5MTRXtkd6rZfcPQibXLaeT0Llu1ZPb3jyWUGp8=眼。在我的遐想中,她小家碧玉一般,似乎成了山清水秀、云遮雾罩而有几分神秘的花溪的化身。这让我觉得,花溪是美丽的,值得向往。下车前行,越过花溪河上的石拱桥,往左转,进清华中学,在靠山一栋简朴的教师宿舍楼的三楼,我敲开了先生的家门。门打开,迎面而来的是两张盈盈笑脸,先生和他的夫人正站在门边。先生个子不高,相貌端正,言谈举止温文尔雅,平和之中饱含激情。而其夫人,非常地勤劳,贤惠。后来听说,她年轻时非常地美丽。在她身上,秉承着中国传统女性的诸多美德,相夫教子,任劳任怨。先生用电脑前,大多手稿都是她誊写的,而且她带的三个孩子个个都有出息。先生的家坐落在清澈的花溪河畔,依山傍水,一个远离尘嚣的所在,若是盛夏,凉风习习;窗外是峻峭的山脉,山上林木葱郁,偶有白鹭飞越,若是夕光映照,便罩上一层淡淡的黄金。这里自然是一个读书写作的清静之地,虽适于隐逸,但先生于此并不是过闲适的日子,他在这里著书立说,从不消停。
正值假期,我请先生帮我找一份事做。先生欣然应允,他托朋友安排我到了一家文学杂志做编辑。编辑部堆放着凌乱的书籍和稿件,桌椅也很陈旧。尽管如此,我却怡然自得——这就是我投稿要投的地方啊,这就是决定稿件是否刊发,决定一个人是否成为作家的地方啊。下班了,我还是久久不愿离去,尽情体味着近似于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那种喜悦。
先生安排我住在他的朋友家,他的朋友也是这家杂志的编辑,一位诗人。诗人有万丈豪情,夜晚拿出他的长诗朗诵给我听。开始我出于礼貌,做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后来撑不住,便有些昏昏欲睡了。诗人知道我喜欢喝酒,见状便取出他收藏多年的老酒,给我斟上一杯,好像是给我的奖励。喝上一杯,我又精神一会,而后随着诗人催眠般的朗诵,我又昏昏欲睡,这时他又让我喝一杯。当他声情并茂地朗诵完,一瓶酒喝去了大半,我已酩酊大醉。我是被酒灌醉了,还是被诗歌陶醉了?有时诗人会打开一口陈旧的木箱,翻找出曾经名不见经传而今已赫赫有名的诗人的书信和照片,向我展示和阅读,其中便有顾城和北岛的。此后他似乎忘了给我看过,又一次翻找出来,于是我又一次装作没见过似的兴致盎然地观看和倾听。但不管怎样,我要感谢这位可爱的诗人,是他不嫌麻烦收留了我,让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有了一个容身之处。
我在编辑部里没什么稿件可看,主编就叫我编读者来信,我说,没有读者来信怎么编啊!主编说,没有你就自己编吧,于是我就编了一堆“读者来信”,“读者”来自四面八方,不同职业,对杂志刊登的作品有着各种各样的评论。这些“读者来信”刊出后,好多人还以为是真的读者来信。杜撰这些来信,近乎于创作,为此我还得了一笔稿费,得意了好一阵。这就是我最早的编辑生涯。
暑假结束后,我又回到了学校,研究生三年级已没什么课了,主要是写毕业论文,呆在校园,犹如困兽,时光更显荒芜,而且得开始找工作了。于是,我给先生打电话,他说刚好贵州另一家有名的文学杂志需要进人,你不妨来一试。这样,我又到了贵阳。先生在甲秀楼等我,见了面,他将一份准备好的礼物交给我,说你见了主编就说是你买的,一点心意。先生想得真周到,还为我准备礼物。后来,我就到了这家杂志实习,并且毕业后分到了这家杂志,一直到现在,而且,从一个编辑变作了主编。
刚到贵阳,几乎是举目无亲,下了班我便呆在宿舍里。没有电视机,看不了电视;白天看了那么多的文字,晚上便不想看书,而且读了几年的研究生,对于书籍有些厌倦,只想融入鲜活的现实,而现实的大门紧闭。尤其到了周末,更觉百无聊赖。于是,那几年,我常常往花溪跑,去先生家。先生于我,是师长,也是朋友,我对他几乎是无话不说,推心置腹。我的抑郁,我的愿望统统向他倾诉,先生对我多是开导、安慰和鼓励。先生夫人许阿姨饭菜做得很好,每到先生家,总要做上一顿丰盛的晚餐。她说,平时他们吃饭都很简单。他们对我的盛情,以及我无端的打扰,很让我感到不安。若是冬天,围着铁炉子,吃着热气腾腾的火锅,喝着陈年老酒,更觉惬意。因为先生不爱饮酒,所以家里存有好些年的酒,不少都被我喝掉了。
饭后,往往已是暮色四合。先生总要送我到车站,即便是寒冬腊月也是如此。直到车开动了,他还站在原地。从河谷吹来的风拂动着他前额有些卷曲的头发,车站昏黄的灯光映照着他的微笑,这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回贵阳市区的中巴车,如离弦之箭,开得飞快。车上充斥着烟味、酒味,酒后亢奋的喧哗和粗鲁的话。我觉得城乡接合部的人有些是不让人喜欢的,不伦不类,既失去了乡下人的质朴,又没有城里人的文明,同时秉承了乡下人的粗鄙和城里人的狡黠。但我必须要和他们同行,这就是怨憎会。
时间久了,我对于这座城市慢慢地熟悉起来,慢慢有了一些朋友,逐步营造起自己的生活,交往了女友,以致最终结婚。常去打扰先生,我也觉得不好意思。而且,先生的三个子女都在沿海城市,每到冬天,他和夫人都要飞到那边去,以回避贵州冬天的阴霾寒冷,直到春暖花开才回到贵阳,这无疑是一种候鸟似的生活——利用空间的跨越避开了季节更替带来的苦楚。我去往花溪的次数是越来越少了,再后来更少与先生见面,因为打他家电话,要么没人接,要么是一个陌生女孩的声音,告知先生不在。原来他生病了,辗转南北住院治疗——这个情况是后来才清楚的,他怕给别人带来麻烦,一直没说。当我到花溪再见到病后的先生时,不禁吓了一跳,他可谓是形销骨立,瘦得皮包骨头了,但先生精神还好,有说有笑,心态平和,乐观。见面依旧聊聊生活和文学方面的事情。但交谈已无过去的激烈,像拉家常似的平淡。走时他再没有像以往那样送我到车站了。又一次见到先生时,是在中医附院的病房,先生比以前更削瘦了,手臂上吊着液水。他说,你不要耽误工作啊,快回吧。病房里还有其他的病人和家属,我们不便多聊,匆匆作别。而最后一次见着先生时,他已躺在重症监护室,鼻孔插着呼吸管,手上吊着液水,脸庞灰暗浮肿。他睡着了,发出被阻滞的粗重的呼吸声。我没有唤醒先生,甚至没有去握他的手,我默默地伫立着,心底知道,这或许就是与先生的永别。而这样的永别,竟无任何的言语。此后,每天我的心总是忐忑的,害怕那在预料中的消息传来。但那消息在一周后还是传来了。
那一周,我父亲因高血压也住进了中医附院。从父亲病房窗户便可看见对面大楼一楼的重症监护室,那里面就躺着先生。我站到窗户边,心里颇为感慨,对面的一楼躺着的是弥留之际的老师,而我的身后躺着的是我耄耋之年的父亲。傍晚,我给父亲送饭后,总要走到重症监护室的窗外。窗前一丛夹竹桃正在盛开,如火如荼。因过了探视时间,监护室门户紧闭,我只有敲门询问医生了解先生的状况。在窗外伫立良久,我不知先生是否感知,我现在就在他身边,相隔很近,但我又感到我们相隔很远,甚至是越来越远,以致迢遥无边的距离。一墙之隔,咫尺之遥,可能就是阴阳两界。室内死神盘桓,先生随时都有可能随着死神远游。我默默祈祷,希冀奇迹发生,先生康复,从病榻上起身,笑盈盈地走出来。
我赶到景云山殡仪馆,先生已静静地安躺在玻璃棺里,脸上扑了很不自然的红白的粉,身子显得那样地瘦小。我感到死神的凶残,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生命终将在其面前妥协。厅堂过于阔大,躺着的先生显得形单影只。遗体告别式上,不少人失声痛哭,而我,不知为何始终未流一滴眼泪,或许我内心里已接受冰冷的现实。
先生安葬的陵园靠近一个叫红枫湖的湖畔,很大,放眼望去,满山遍野的墓碑,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这是另一座城。先生墓地周围的陵墓,我仔细地阅读碑上的文字,以及逝者的照片,觉得都与先生不是同路人。有的笑容可掬,和蔼可亲,就像邻里大妈,喜欢打麻将。我不知道先生会不会和他们和得来,如果和不来,仍热衷于著书立说,在这荒郊野外,夜夜听着湖水拍岸,该是很寂寞吧。
先生享年六十九,虽算不上英年早逝,但现在的老人一般都是要活到八十多岁,相比起来,先生还是走得过早了。我觉得先生的早逝与其生命的透支有关。生活中他没多少嗜好,不打麻将,不抽烟喝酒,虽有几个好友,但相聚甚少,长年累月就呆在书房里,看书写作,现实生活相对单一(而其沉浸其间的精神世界无疑是绚烂的)。对于时间,他容不得半点浪费,争分夺秒。写作消耗了他太多的精力,这种消耗成就了一部部小说和史学的著作,于社会有益,于他自己和他的家人却有损,甚至是伤害,巨大的伤害。
先生大学毕业,本来是要留省城的,但遭逢“运动”,下放到黔南的一个叫茂兰的小镇中学教书。那里森林茂密,溪流纵横,是一个风光秀丽的地方——现已成为著名的风景区。要知道,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凤毛麟角,乃天之骄子,况且先生在大学时代已崭露头角,在一个文学处于社会意识形态核心地位的时代,先生无疑是骄中之骄,有着很大的抱负,正想大展宏图之际却被“发配”到偏远的地方,可想其心中是有很大的怨愤的。然而这样的际遇也不是一无是处。正是在那里,先生邂逅了后来成为他夫人的许女士,许女士美丽贤淑,给予先生无尽的幸福和襄助。这样的遭遇,对于他来说,有所耽误,但也更激发他进取的意志。正是在那儿,他考取了贵州社科院的研究生。也正是这种遭际,使他深深体味了一介书生,一个知识分子在历史潮流中对自己命运无力的抗争,而这种体认深深融入了他的历史小说。
据说,先生祖上是清代被贬入黔的一位高官,入黔后耕读传家。或许先生身上便因流淌着“士大夫”的血液,博览群书,勤于笔耕,张扬士的精神。先生年轻时很早就发表了文学作品,后来或许是读研究生而且在社科院工作的缘故,转向了研究,撰写了大量文学研究方面的文章与著作。再后来,可能是不甘于仅限于文学的评说,或者是看不惯那些毫无才情而又洋洋自得、自诩为作家的写作者的无知无畏,于是便想证明给他们看看,搞学术的我一样也能创作,而且可能写得更好,当然也是他长期压抑的创作激情和梦想的迸发。他转向了小说的创作,而且成绩斐然,可谓是从学者转变为作家;而到了晚年他又转向了研究,不过,这时他的研究已不是文学的研究,而是文化的研究,准确地说,是地域文化的研究,结果同样令人称赞。先生晚年可以说是从作家又转变为学者了。像这样既在学术研究领域又在文学创作领域双向修远、著述丰厚者是不多见的。
与先生相比,我很惭愧。我曾经也是非常的勤奋,读书到深夜,天未明即起。可后来我可能是失望了,变得散漫起来。日复一日地酗酒,中午喝,晚上喝,仿佛不是我在喝酒,而是酒在喝我,不知不觉就喝掉了我一大截光阴。是不是想以酒精驱逐那幽灵般如影随形的虚无呢?先生曾委婉地批评过我,要我少喝酒,多读书多写东西,不要浪费自己的才情。现在,我很少喝酒了,我过得异常忙碌,忙于做好一本文学杂志。在这点上,我可能没有辜负先生的期许:来贵州吧,为家乡做点事,为文学做点事。但在写作上,我还是辜负了先生,甚为歉疚。
每次我去拜访先生,在从花溪返回市区的车上,我总凝视着窗外,黑黢黢的山峦默默地向后移动。黑暗中的山脉仿佛生命,亘古千年,而又绵延无尽,历尽沧桑,却从无言语,该有着怎样深邃博大的内心世界?在高原,山脉就是天,就是大地,就是沧海,就是桑田。坚硬,屹立,不崩毁。宛如先生的灵魂。
责任编辑 张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