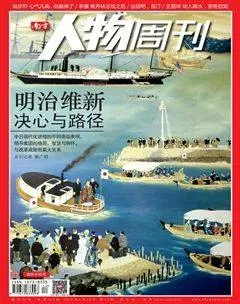战后影响最深远的英国首相
英国战后哪位首相影响最深远?不是丘吉尔,他虽屡屡在“20世纪最伟大的英国首相”之类民调中占先,且在1951-1955年再次拜相,但当时他的政绩乏善可陈,他对英国的贡献,主要是在二战中带领国家民族奋勇抗敌,在国运最风雨飘摇时,让社稷不落入纳粹魔掌。换句话说,这不能算进战后那一本账。
过去一个多星期,撒切尔夫人逝世,人们忙不迭悼念这位铁娘子,缅怀时,不少人都把她封作英国战后影响最深远的首相。但我想提醒大家别忘了另一位,英国战后首位首相,工党的艾德礼。在2010年University of Leeds访问106位英国政治和历史学者的调查中,艾德礼与撒切尔夫人分占第一、二位;而在2004年同样由University of Leeds所作的类似调查中,艾德礼同样压过铁娘子,更是第一与第四之比。这两位风云人物的功过,要拿来一并讨论才好理解。
英国战后百废待兴,选民在1945年大选放弃了虽是战争英雄、却刚愎自用的丘吉尔。在艰苦的战争中,每个人都为国家民族作出无私奉献,于是在战后重建和休养生息时,讲求的理应是和衷共济,让每个人都能分享成果,而工党那套权利义务共享共扛、同志间互信互爱的伦理,恰巧最能迎合时代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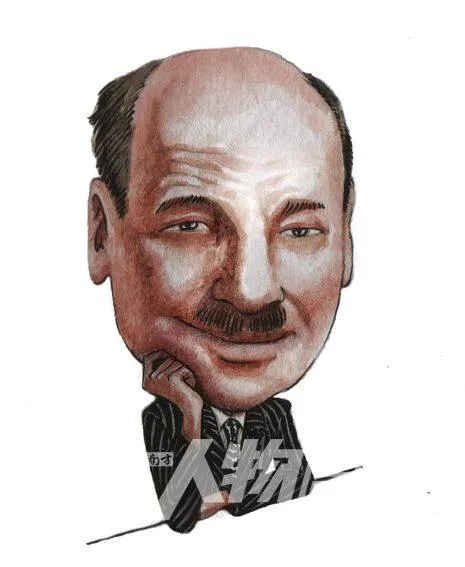
在艾德礼的带领下,社会建立了3点的共识,并进行了相关的改革,包括:
一、维持稳定以及高水平的就业;
二、福利主义国家,例如政府向失业和贫穷人士提供社会救济,以及以政府补贴的全民保险为基础,向全民提供免费医疗照顾;
三、混合式经济,在市场经济之上,把大量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企业国有化,如煤炭、石油、电力、铁路、航空和钢铁。这三项可谓环环相扣,例如国企提供“铁饭碗”,这是稳定和高水平就业的一大支柱,而除了高税率以外,把大量企业和其盈利国有化,也是提供福利的一大财政来源。
在这样的变革下,正如一位矿工领袖在1950年工党大会上欣喜和乐观的发言:“贫穷已经消灭,饥饿已经无所闻,病人都获得照顾,老人都得到奉养。我们的下一代是在希望的土地上成长。”在艾德礼的领导下,社会贫富悬殊大幅改善,英国60kl5EeouyBbT+A7lhTd8IeU4K3RlHwf0L9p0QlRfDg=迈向一个更为平等、和谐的社会。
虽然1951后进行了政党轮替,但正如曾在艾德礼任上担任财相的Hugh Dalton于1954年所说:“人民十分满意保守党,因为充分就业、福利国家等等社会立义者的特性,保守党都窃为私有了。”
这就是艾德礼的影响,也是所谓“战后共识”,或称“社会民主共识”。此共识在战后获两大党广泛认同近三十载。
但凡事有始必有终,有利必有弊,“战后共识”的巨大代价,30年后暴露无遗。国营让企业失去效率和竞争力,福利主义让政府负担沉重,工会过分坐大让政府和企业缚手缚脚。这些症候都在1978至1979年的所谓“不满之冬季”,来个总爆发。
为避免进一步刺激己十分严重的通胀,执政的工党政府不得不把公营部门加薪率控制在5%以下,这被工会视为破坏彼此间一直存在的“社会契约”,因而发动大规模罢工抗议,政府被此起彼伏的罢工行动弄得疲于奔命、晕头转向。罢工引发停电、交通瘫痪、街道上垃圾堆积如山,甚至出现棺材无人落葬、医院减收急症病人等场面,再加上那是16年来最冷的冬天,不只让这个冬天变得格外凄凉,亦令经济进一步雪上加霜、奄奄一息。
时势造英雄,就在“不满之冬”后人心思变的时刻,撒切尔夫人乘时而起,带领保守党在1979年大选胜出。上台后,她紧抱“小政府”的方针,推行国企私有化、减税以刺激投资、让市场主导经济、收紧货币供应、削减社会福利、把公共房屋出售给原先的租户、打击工会势力,悍然结束实行了30年的“战后共识”。
史家和学者把这套管治哲学称为“撒切尔主义”,她是20世纪惟一一个名字被冠上“主义”的首相,即使丘吉尔也没这样的殊荣。其管治哲学影响深远,之后的首相梅杰、布莱尔、布朗和卡梅伦,没有一个敢明显反其道而行。2002年,布莱尔的左右手,执政工党政府重臣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毫不忌讳地公然宣称:“到了今天我们每一个都是撒切尔主义者。”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艾德礼和戴卓尔夫人就是如此各领风骚,不但改造了自己的政党,也影响了对手的政党。
2012年,当铁娘子在汉普郡出席一个晚宴时,被同场嘉宾问到什么是她从政的最大成就,她不无傲慢地说:“布莱尔和新工党。我们迫使对手改变了思维。”这与前面提到的半个世纪之前Hugh Dalton所说的一番话,不是相映成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