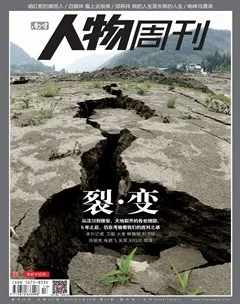茵莱 直上天堂,往返人间





普鲁斯特曾经写道,地名是人们思绪中“地表上一些特定地点”的具体化。比如巴黎是“一个堆满镀金边框的镜子、刻意安排的店面和大量博物馆的地方”、仰光是“大佛塔、昂山素季和穿笼基的男人”,至于茵莱(不是莱茵),它是东南亚最大的高山湖泊的名字。“这是一个由漂浮在水上的花园、棚屋村庄和摇摇欲坠的佛塔组成的水汪汪美妙的世界。”《孤独星球》如此描述这里,“很多旅行者把这里当成缅甸的桃花源,群山倒映在湖水里,模糊了天与地的界限。”
当我在蒲甘的佛塔上蹿下跳到精疲力竭,被热带平原的风吹得昏昏欲睡之后, 决定前往茵莱为旅途画上句点。
破旧的班车在凌晨从蒲甘驶出,穿过山区,向着少有游人惊扰的掸邦高原扬长而去。公路渐渐变成乡间马路,周围是绿色稻田。“男人女人坐在小屋外纺纱或绕丝线, 孩子们在大人周围玩耍,野犬睡在道路中央”,毛姆(Maugham W.S.)在《客厅里的绅士》中写道。这本小册子记录了他上世纪20年代从仰光到海防,穿越缅甸、掸邦、暹罗与印度支那的旅行,“这些人至少找到了解答生存之谜的一种方法。”
8小时后,到达水鸟(Shwenyaung),这是在茵莱湖的一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缅甸村庄。它与外界的接触不多,依旧保留着传统东南亚民俗。整个小镇只有3间旅馆,Mingalar inn就藏在 Southern Shan State路上(靠近邮局),这家由一对夫妻经营的客栈有十余间用竹子装饰的惬意房间,园子里的主角,是一颗开满鸡蛋花的大树。
在凉爽的天气、连绵群山包围的优美湖区景色和友善好客的氛围里,数个美好的日子转瞬即逝。
好几天的清晨,我都会在客栈门口等候着一列穿着红色袈裟的僧侣在柔和的晨光里缓缓走来,他们拿出僧钵,我和任何一个当地人一样放入一些米饭、水果或其他食物,相视一笑也无言语,完成一项静默的仪式。
然后步行穿过小镇,在渡口的小桥上看着它渐渐苏醒。渡口处的水面并不宽广,水色有着粉笔画温和疲惫的柔弱,这些颜色带着油彩的半透明,但少了那份执着的明确性。衣着明亮的当地人开始从四面汇聚,农夫把湖区采摘的蔬果运到码头,穿着笼裙的妇人缓步而来,三三两两的孩子提着装有饭盒的编织篮朝学校走去。
我搭上一艘船朝向湖区深处,嘟嘟的马达划破热闹,驶入彻底的静谧中。颜色鲜艳的小木屋零星散落湖边,湖面上的光游戏般地涂抹着刚刚调好的颜料,我屏住呼吸,因为相信它会转瞬即逝,然后心怀期待地等着,就像吟诵一首有点复杂的格律诗,倾耳等候姗姗迟来的韵脚。
湖上有人家正在打渔,用一条腿缠住木桨踩水前进,双手撒网捕鱼。木船走走停停,拜访湖上的村庄:有人家在打铁,有人家用湖藕制成的丝线纺成布匹,造船的、卷烟的、加工首饰的,都是古老手工作坊。人们集体工作,做他们想做的事,没有表演欲,眼光柔软而单纯。
茵莱湖像两条茄瓜,狭长且窄,五六个小时之后,抵达“茄瓜”的另一头——湖区的另外一个小镇。带着玫红色头巾的当地少数民族农民带着各种颜色艳丽的生鲜食物、手工制造的器物来到码头交易,佛寺掩映在不远处的树林中, 鸟在树间鸣叫,蟋蟀唧唧,在少年简陋的笛子里堆积成忧伤的曲调。
在茵莱,彼此矛盾的事物混杂于和谐,却有一种古老的安全感。
茵莱湖区旅游TIPS:
- 每年9、10月,雨季的最高峰,缅甸各地的江河湖泊一片欢腾,人们举行划船比赛(Boat races),茵莱此时是全国当仁不让的沸点。紧随其后的是点灯节(Festival of light或Thadingyut),人们在3天的节日期间点亮所有的油灯、火气灯、电灯甚至蜡烛。
- 晚上最惬意的时光大概就是找一家运河边的酒吧小酌一杯。VIEW POINTE是个不错的去处,这间镶嵌着碎玻璃的红顶白墙法式建筑就座落在桥头,这里有精心烹制的掸族食物。
- 如果有更多的时间,建议在格劳下车,加入45公里徒步之旅。行走在清凉的掸邦高原大山中,可到达部波朗、欧泊、茵达等最原始的掸族人的村落。